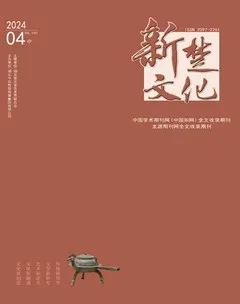丁戊奇荒中陜西的災害應對
【摘要】丁戊奇荒是光緒初年的一場嚴重災害,發生于清政府著力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時刻,妥善應對這場災害成為陜西省的重要任務。清代完備的荒政體系再次發揮作用,通過整頓官僚體系、依靠基層士紳力量積極救災、維護基層社會秩序等手段,陜西大體平穩度過災年,也保障了新疆戰事的順利結束。
【關鍵詞】丁戊奇荒;陜西;災害應對
【中圖分類號】K252;D691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4)11-0011-04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11.003
丁戊奇荒是光緒初年發生的一場重大災害,具有波及范圍廣、持續時間長、破壞力巨大的特點,對當時陜西影響劇烈。目前丁戊奇荒的相關研究區域集中在當時的山西、河南、直隸等省,關于陜西的研究,僅有張銀娜從渭北諸縣地方政府角度探討了丁戊奇荒發生后的各種應對措施[1],未能著眼陜西省政府層面談這一問題,也未涉及中央政府的應對問題。本文嘗試將陜西省與州縣地方政府的災害應對措施相結合,兼顧中央層面的救災舉措,系統梳理陜西省在丁戊奇荒中的應對特點,總結其中的歷史經驗。
一、丁戊奇荒與陜西災情
(一)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是1875-1878年旱災引發的特大災荒,1877、1878兩年最為嚴重,按干支紀年,1877年為丁丑年,1878年為戊寅年,因此稱為“丁戊奇荒”。這場災難主要波及晉、冀、魯、豫、陜五省,并殃及隴東、川北、蘇北等地,被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荃稱作“二百余年未有之災”[2]33,學者估計1.6~2億人受災、死亡高達900~1300萬人[3]272。其根本原因,夏明方總結為“近代以來國內封建主義日益腐敗的政治制度和殘酷的經濟剝削、國外資本主義日趨加深的經濟侵略”[4],氣候原因是1873-1878年的厄爾尼諾現象較強,東亞季風減弱[5]。此外,倉儲制度衰敗、農民負擔過重、吏治腐敗、戰亂和生態惡化,都是這場慘劇的成因。
(二)時代背景
光緒初年的關中地區殘破不堪。1862年以來關中戰亂頻仍,回民起義、捻軍入陜造成人口銳減,土地成片拋荒,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1869年以后,戰亂告一段落,但陜西地處戰爭物資供應前線,征派苛繁,使剛剛遭受戰爭創傷的關中人民更加貧困[6]353。在陜甘總督左宗棠看來,陜甘地區“頻年被賊蹂躪,農業舊荒,積欠錢糧無從征解”[7]6。
時值朝廷命左宗棠收復新疆,陜西承擔了后勤任務。1875年3月,朝廷任命譚鐘麟接替曾國荃出任巡撫[8]133下,丁戊奇荒就發生在他的任內。清廷任命左宗棠的同月,上諭說“西征糧臺,已諭左宗棠責成陜西藩司經理,應行奏催及咨行各省事件,呈由陜西巡撫核”[8]56下,即陜西省分擔了西征大軍的部分后勤工作。糧臺不僅負責轉運糧食,還要保障餉銀和軍械、火器等后勤物資的運輸[9]100。
(三)陜西省受災概況
1877年之前,陜西災情尚不嚴重,1877年旱災波及全省。這年陜西全境有80多廳州縣因災緩征錢糧,全省幾無幸免,九月朝廷下令緩征陜西受災49廳州縣錢糧[8]806,農歷十二月初七(1878年1月9日)上諭又說,“緩征陜西……三十九廳州縣被災地方新舊額賦有差”[8]872上。《申報》記載了各縣受災慘狀,“秦中自去年立夏節后,數月不雨,秋苗顆粒無收,至今歲五月,為收割夏糧之期,僅十成之一,至六七月,又旱,赤野千里,幾不知禾稼為何物矣……同州府所轄……及近各州縣,民有菜色,俱不聊生”[10]。醴泉東門外挖掘兩個“萬人坑”掩埋尸首,城中水井被小兒尸體填滿,吃石粉致死、在粥廠擁擠致死者不計其數[11]卷14,4。1878年仍有55個廳州縣受災嚴重,朝廷“蠲緩陜西大荔……五十五廳州縣被災村莊額賦有差”[12]203下。同年年底,巡撫譚鐘麟上奏稱“賑務告竣”[12]259下,標志著災情高峰終于過去。
這場特大災害中,關中是陜西主要受災區域,而渭北甚于渭南,又以關中東部同州府最為嚴重。關中在1877-1878年各廳州縣連續兩年都有蠲免、緩征錢糧的記錄,說明普遍受災。從記載看,“(饑民)扶老攜幼百十成群,紛向渭河南各州縣轉徙流離”[13]510-511,渭北饑民大量涌向渭河以南地區,渭南情況稍好于渭北,“陜西兇荒自道光二十六年以來最重者莫如光緒三年,雨則稀少禾苗枯萎,平原之地與南北山相同,而渭北各州縣苦旱尤甚”[14]卷127,23。渭北諸縣受災程度也有區別,關中東部的同州府情況更為嚴重,這里農田水利不發達,“惟仰澤于天,不為灌溉計”[15]卷14,24,一遇旱災則損失慘重,1881年同州知府稱“光緒丁丑陜西歲大旱,同災尤棘”[15]卷14,23,下轄的澄城“光緒三年,大饑,人相食……死者十之六七”[16]卷11,6,蒲城“至四年夏,餓斃者三分之二”[17]卷13,6,韓城光緒三四年間“野無青草,道饉相望,盜賊蜂起,弱肉強食”[18]卷4,11。
旱災除直接引起饑荒外,還間接引發其他次生災害。比如1878年,澄城“狼復熾,傷人甚眾”[16]卷11,6,“秋大疫,死者無算”[16]卷11,6。
人在極端情況下容易鋌而走險,即天災導致人禍。1877年,大荔、蒲城發生了饑民攔路搶糧事件,韓城白馬川有“土匪”聚集,“……據稱近聞陜西同州府屬之大荔、朝邑、郃陽、澄城、韓城、白水、各縣,因旱歉收,麥田不過十之一二。華陰、華州、潼關等屬,秋苗盡為田鼠蝗蟲所害,糧價驟增。大荔、蒲城等處,搶糧傷人之案遞出。韓城之白馬川,聚人數千,游勇土匪,互相煽亂,并有軍械旗幟”[8]762,蒲城“刀匪”入縣城劫獄擊殺知縣,“……刀匪乘機蠢動,七月間突有已革武生屈繼仁,糾眾擁至蒲城縣,爬城劫獄,焚燒衙署,該縣知縣黃傳紳率勇圍拏,旋即被戕”[8]775上,足見這里災情嚴重,社會秩序已經動蕩。
二、陜西省的應對舉措
民國《澄城縣志》提及丁戊奇荒時說,“時朝廷有事回疆,未暇賑救,死者十之六七”[16]卷11,6,將澄城縣損失慘重的原因與用兵新疆聯系起來,這是有道理的。當時陜西既要全力保障西征大軍后勤,又要應對此次天災,那么可能面對的局面有這樣幾個:一是處置得力,陜西平穩度過災年;二是陜西在災情中損失慘重,但未影響稅賦的征收和西征大軍后勤供應;三是陜西損失慘重,西征大軍后勤供應不足,使得收復新疆行動失敗;四是陜西損失慘重,爆發大規模動亂,西征大軍慘敗,動搖統治。因此,陜西此次災情應對的底線是,全力保障左宗棠在新疆的軍事行動順利,防止受災地區發生大規模民變。
本次災情中,陜西省的應對舉措主要有三:整頓吏治、采取賑災措施、維護基層社會秩序。
(一)整頓吏治
督、撫有監察下屬州縣官員的職責,在此次災情中,清廷曾屢次下令各地督撫加強監管,譚鐘麟多次奏請懲處災情中不稱職的陜西官員。1877年譚鐘麟奏報,富平知縣劉志同不遵指示、設立粥廠不公導致災民紛紛到省城控訴,署理高陵知縣陳衍昌上報的災民戶口存糧數字含糊、且放任士紳舞弊,候補知縣何廉等管理省城南關粥廠不利,候補知縣汪鳳澐在富平縣協助賑災辦理不善,幾人都被革職嚴懲[8]872。次年五月,清廷一次將他參奏的五名官員革職[12]130。
(二)賑災措施
1.與致仕官員協作,處理賑災事務
1877年,清廷委任前陜西布政使張瀛在陜西稽查災情,幫辦賑災事務。張瀛是陜西蒲城人,此前一年因病從山西布政使任上解職,為官經驗豐富,又熟悉本地情況,在當年“刀匪”劫獄殺死縣令前后,他寫信給譚鐘麟告知災情,譚鐘麟方才奏請蠲緩蒲城錢糧,旋即被任命幫辦陜西賑務。朝廷特派官員到各地幫辦賑務,從形式上彰顯了中央的重視,從作用上看,一方面分擔督撫布政使的工作量,一方面也起到了監督作用。
2.官方求神祈雨活動穩定人心
丁戊奇荒中,上至皇帝,下至各級官員,求神祈雨活動的記載不絕如縷。根據《清實錄》記載,僅光緒二年(1876年)前五個月,光緒皇帝就親自前往大高殿祈雨達13次之多,此外在光緒元年至五年,還多次派遣皇室宗親前往祠壇神廟祈雨、各省督撫前往名山大川和神廟祭祀,并表彰“禱雨靈應”的廟宇,華岳廟、太白廟在1878年得到了表彰匾額[12]288上。陜西省的各級官員求神祈雨活動也屢見不鮮,如1878年春天,韓城知縣甫一上任便在韓城境內的九龍山進行祈雨活動,并親筆寫下《九龍山祈雨記》,立碑為記[18]卷4,8-9;同州知府不僅求神祈雨,還會同大荔知縣和鄉紳,專門在城東北建龍神廟供奉神明[15]卷14,23-24。
中國古代有天人感應的理論,若發生自然災害,則是“天象示警”,系上天降下的懲戒,只有誠心侍奉神明,才能免于災禍,這種思想在民間十分盛行,官方順應這種思想,在災害發生時進行求神祈禱活動,并大加宣揚,引導民眾視線,一定程度上轉移了百姓對官府的不滿情緒,起到安撫民心、防止民變的作用,因此也是應對災荒的重要措施。
3.減免、緩征受災地區賦役,穩定局勢
減免、緩征災區賦役,是應對災情的通例,清代蠲免、緩征是寫入《大清會典》的救荒措施。蠲免即將應征收的稅賦減少或免除,有明確的步驟,需要由州縣查明數目后上報布政使核實,再張貼告示公布[19]30。若受災程度稍輕,則會緩征災區稅賦。
前文已述,陜西大規模緩征、減免錢糧發生在災情最重的1877-1878年,此項舉措實際作用不是直接救助災民。1877年,同州府發生嚴重民變,先是韓城、郃陽有“匪徒”聚集,之后蒲城知縣在圍捕“刀匪”過程中被殺,于是九月上諭指示巡撫譚鐘麟“至所稱渭南、臨潼、富平等縣,催科甚急,小民無計謀生,恐致激成事端”,命令他“即行查明災區輕重,奏請蠲緩錢糧,以示體恤”[8]791下,說明初衷是防止激起民變。
4.賑濟災民,降低災害損失
丁戊奇荒中,各省賑濟活動包括官方主導的官賑、民間組織的義賑和外國人組織的洋賑,陜西主要實施的是官賑。
官賑是傳統賑濟的主要方式,具體有直接發放錢糧給災民和粥賑兩種。直接發放錢糧,需要按照受災程度確定發放的時間長短,一般持續數月,直到災情過去,根據實際情況,對于有償還能力或受災較輕的災民實行有償賑貸和賑糶,對于不具備以上條件的災民,則發放少量錢糧保證活命。根據譚鐘麟的奏報,從1877年九月初一到次年六月底,陜西省“統計各屬賑過極、次貧男女大小口三百一十四萬口有奇”[20]374。粥賑則是在受災地區和災區人口聚集的聚落設立粥廠,通過施粥保障災民基本的食物,陜西在省城西安和各受災州縣都設有粥廠,盡量確保災民不致餓死。粥廠的位置、數量會根據災情變化而調整,如富平知縣革職后,繼任者遵照譚鐘麟指示救災,因城北流民眾多且沒有有效的組織管理,“特于北關外太元廟內設立粥廠一處”[21]卷10,7。
5.籌措錢糧,保障賑濟
因陜西缺糧,需從外省購入大量賑災糧食。1877年8月,譚鐘麟上奏折請求挪用各省所欠陜西協濟專餉,以及閩粵海關、江漢關應運往陜西的餉銀賑濟[8]775-776,解除陜西無錢買糧的窘境。自鎮壓太平軍開始,清朝陸續在全國設置厘卡,向坐商收交易稅“坐厘”,向行商收流通稅“行厘”,厘卡數量眾多,統屬復雜,嚴重影響商業流通,會降低糧食的運輸效率。譚鐘麟無權命令河南、湖南、湖北的厘卡,于是上奏清廷,由清廷統籌數省,為陜西賑災糧食提供便利。1878年春,編修崔志道上奏,“陜省賑務需款尚多,西征現已報捷,兵餉如有可以酌裁之處,請飭左宗棠騰挪撥濟”[12]71上,清廷于是令左宗棠酌情辦理,與前述取消厘金征收的舉措相同,陜西省無權調用西征餉銀,須清廷居中協調。
1877年9月上諭稱,購買運輸糧食所需費用為數不少,要求左宗棠、譚鐘麟盡力動員陜甘士紳、商人捐銀[8]793下。以涇陽為例,丁戊奇荒中,官員、有功名者、商人紛紛捐錢捐糧助力,有兩人除各捐銀數千兩外,還直接襄助賑災事務[22]卷14,10-13。他們的事跡被記入官方編纂的縣志中,是一種精神褒獎,此外還有許多受到物質褒獎的鄉紳,如賜予出身等。
另外本次賑災中,組織中國近代第一次義賑的東南沿海地區士紳也捐助了銀兩。自光緒三年八月至光緒五年二月,上海的各省士紳商人為直隸、山西、河南、陜西四省賑災籌集規銀27萬余兩,其中分兩批運往陜西共13000兩[23]5285,5287。
6.任用士紳,協助賑濟
清代的官僚隊伍總規模不大,胡恒認為文官規模基本維持在14000人上下,晚清文官數量稍有擴充,也不超過兩萬人[24],清代內地縣級單位有一千多個,平均到每縣,正式的官員數量屈指可數,于是常設各種無品吏員協助處理日常工作,當遇到天災類突發事件時,縣城以外的廣大鄉村地區人手仍不足,必須另尋合作勢力。各州縣的賑災,依賴士紳等地方基層勢力,他們在縣下有較大影響力,又較為富足,受災情影響較小,既能為賑濟提供物資保障,又可以協助官府組織賑災活動。在救災過程中,韓城、大荔、富平、蒲城等受災嚴重的縣,也普遍依靠地方基層勢力協助組織救災。最具代表性的是韓城,知縣在《光緒三年賑務碑記》中寫道,他上任之初“無從措手”,后來縣中“賢士大夫”協助賑災,“或專司賑務,或專勸捐輸,均能任怨任勞,即采買轉運查災,各紳商亦多晝夜奔馳,不辭勞瘁”[18]卷4,11,在本地鄉紳商人的幫助下,韓城賑務才得以正常運轉。
7.推行區田、代田法抗旱減災
1877年冬,官員上奏請求在受災嚴重的晉、豫、陜三省推行區田法,清廷即令三省巡撫按實際情況予以辦理[8]860上。區田法始見于西漢《氾勝之書》[25]38,是一種用于抗旱的耕作方法,將不常耕作的荒地劃為許多有間隔的矩形區域,在這些小區域內精耕細作,以求高產,被歷代視作應對旱災的重要手段。區田法往往與代田法并稱,代田法最早由漢代趙過推行,“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26]1138,即在一畝田地上縱向挖出三條溝,溝壟隔開,每年輪換耕種,這樣能恢復土地肥力,抵御風災。
當時同州大荔縣在知縣主持下,大力推行區田、代田法。知縣親自在城東關租地數畝耕種,為民眾做示范,并刊刻圖示,推廣到全縣,兩名生員帶頭施行,“歲旱減收,尚每畝得谷兩石余”[23]5844,得到左宗棠贊賞。知縣還在親自實踐后總結了兩種方法優劣,認為代田法適合容易灌溉的土地,如果取水困難,則適合區田法。
8.興工代賑,安置災民
興工代賑是應對災害的慣常做法。1878年春,有御史上奏清廷稱“陜西省城至臨潼五十里間,水失故道,請疏治灞浐,俾達渭河”[12]31下,請求以工代賑,得到批準,遂下令由巡撫負責辦理,陜西省遂開始施行。大荔縣知縣周銘旂興修水利,他計口分工,安排災民在平地上開鑿水井,新開三千多口,按照工程難易程度,每口井發放小麥一到兩斗,同時還疏浚鐵鐮山下干涸的泉水,在膠泥溝等處開鑿水渠,在河濱架設水車灌溉農田,這些工程也都需要大量人力投入,起到了安置災民、興修水利抗旱的效果。
(三)維護基層秩序
陜西省官府對民變與叛亂采取了堅決鎮壓的措施。1877年,陜西一隊士兵行至涇陽縣嘩變,攻入城中搶奪財物,殺人放火,譚鐘麟立刻派出總兵姚文廣等追擊,“本月(十月)初三日至子午峪口,將潰勇四面兜圍”[8]818上,將其一舉消滅;差不多同時,譚鐘麟還派兵鎮壓了同州的幾股民變。
在基層,各項賑災活動仍然依靠平時的基層組織方式進行。例如蒲城縣當時依靠“聯”這一組織:“……縣地方遼闊,所管民戶一百零八聯……卑職會同委員及紳耆公同酌議章程,除富聯自捐自散外,所有極貧、災種之區,一面清查戶口一面散發賑糧……”[17]卷3,20-21大荔縣則依托縣內四十二保賑災,又設置路、團等組織,“統計荔邑四十二保,分為十二方……鄉間村各為團,各以路總統之”,“荔邑四十二保,向分四十二團……惟各保散處各方,地勢參錯,頭緒較繁。茲擬按十二支分為十二路”,用以維持基層治安[15]卷14,25。
在這次災難中,陜西特別是關中東部地區損失慘重,但仍在可承受范圍,未出現社會秩序崩潰和大規模民變,西征大軍沒有后顧之憂,新疆戰事在災情最重的1877-1878年基本結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方政府處置災情得力,保障了國家重要戰略的推進。
三、歷史經驗
統一領導是應對重大災害的前提。在應對丁戊奇荒過程中,陜西省政府發揮了協調各方力量的作用,受災各州縣政府則是救災措施的直接領導者。陜西省政府與中央通力協作,保證省內災情及時上報、受災地區獲得蠲免、叛亂從速平息、賑災錢糧源源不斷、不合格官員適時裁撤,在省府監督管理下,受災各州縣基本盡到賑災職責,維持了荒政體系的正常運作,發揮出了應對災害的正向作用。
建立完善的救災系統是應對災害的有力保障。陜西省為救災而采取的各項舉措,基本屬于既有荒政體系內容。表明清朝建立并維持的災害應對系統是成熟有效的,對處理各類災害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生產水平低下、缺乏現代防災減災技術的中國古代社會,正是依靠不斷完善的荒政系統,才能抵御各種天災的侵襲。
掌握基層是應對災害的必要條件。整個賑災過程中,陜西各級官府盡力維持著對基層的掌控力,以保證基層社會秩序的穩定,這是中國歷代政府救災留下的具有普適性的經驗。為了維持這種掌控力,州縣官員選擇依賴地方士紳的力量,反映出清政府基層治理能力的不足,造成這種局面,表面上看是政府官員數量嚴重不足,其實質是古代社會基層勢力強大,國家力量無法伸入鄉村,只有地方士紳配合,國家政令才能通達。時至今日,“皇權不下縣”早已成為歷史,但政府對基層的掌控不能放松。
參考文獻:
[1]張銀娜.光緒“丁戊奇荒”與地方政府應對[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1.
[2]曾國荃.曾忠襄公奏議[M].木刻本.[出版者不詳],1903(清光緒二十九年).
[3]何炳棣,葛劍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4]夏明方.也談“丁戊奇荒”[J].清史研究,1992(04):83-91.
[5]滿志敏.光緒三年北方大旱的氣候背景[J].復旦學報,2000(06):28-35.
[6]秦暉,韓敏,邵宏謨.陜西通史·明清卷[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
[7]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6冊[M].上海:上海書店,1986.
[8]德宗景皇帝朝實錄(一)[M]//清實錄:第5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9]羅爾綱.湘軍兵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4.
[10]秦饑[N].申報,1877-10-03(3).
[11]曹驥觀.續修醴泉縣志稿[M].鉛印本.西安:酉山書局,1935(民國二十四年).
[12]德宗景皇帝朝實錄(二)[M]//清實錄:第5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13]柏景偉.灃西草堂集[M]//清代詩文集匯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4]楊虎域,邵力子,督修.宋伯魯,吳廷錫,纂.續修陜西通志稿[M].鉛印本.陜西省政府通志館,1934(民國二十三年).
[15]馮譽驥.同州府續志[M].刻本.[出版者不詳],1881(清光緒七年).
[16]王懷斌.澄城附志:卷11[M].石印本.[出版者不詳],1926(民國十五年).
[17]李體仁.蒲城縣新志[M].刻本.[出版者不詳],1905(光緒乙巳年).
[18]趙本蔭.韓城縣續志[M].[出版者不詳],1924(民國十三年).
[19]李向軍.清代荒政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
[20]李文海,周源,等.近代中國災荒紀年[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21]樊增祥.富平縣志稿[M].刻本.[出版者不詳],1891(清光緒十七年).
[22]劉懋官,周斯億.宣統重修涇陽縣志[M].刻本.[出版者不詳],1911(清宣統三年).
[23]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中國荒政書集成[G].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24]胡恒.清朝的政區分等與國家治理[N].中華讀書報,2018-07-11(13).
[25]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初稿)[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26]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作者簡介:
王開明,男,山東淄博人,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中國史專業博士生,研究方向:區域歷史地理、歷史農業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