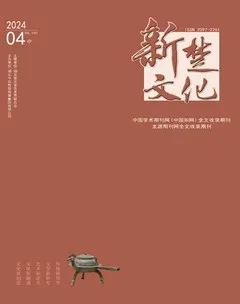從生子到遇合:唐前異類關系小說母題變遷
【摘要】異類生子母題源自上古時期的感生神話,具有通聯上天、與天攀附的神圣意義。戰國時期,感生夢形式的帝系神話雛形出現,異類生子母題的政治目的逐漸取代了宗教意義。到了兩漢時期,異類生子母題分成三個不同的發展方向,感生神話徹底轉變成了以感生夢為形式的政治神話,動物生子則趨向于獵奇。其中,“異類生子”中的根本文化因子進一步催動了“異類遇合”的產生,包括人神遇合、人妖遇合和人獸遇合這三種類型。在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遇合代替生子成為人與異類相關題材的創作核心,體現了時人從宗教、政教到追求生命體驗的價值觀轉變。該時期的主題發展,為后世同類小說創作提供了母題和樣式的雙重典范。
【關鍵詞】異類生子;感生神話;與天攀附;人神遇合
【中圖分類號】I242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4)11-0025-04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11.007
異類生子母題即指人與異類結合并生子,異類包括神仙、動物、精怪。此外,人鬼遇合、生子等母題與異類母題發展源頭不同,神仙、動物在早期異類生子母題中屬于同質生物,只是后期才有明顯界限。因此,本文所指的鬼是人死后的靈魂狀態即人鬼,仍歸為人的延伸,不屬于異類范圍。早期異類生子有著非凡地位,但在魏晉南北朝,此類母題開始不再突出,相應的異類遇合主題卻漸漸發展起來。因此,本文主要就異類生子與后期延伸出的異類遇合這兩者間的消長和流變原因做出梳理與探討。
一、上古感生神話:原始崇拜和宗教信仰
最早的異類生子母題即上古感生神話。
上古時期最早的關于人類起源神話應是女媧神話。最早可見《山海經》: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1]515
僅從字面來看,這則傳說并沒有直接提出女媧之腸化人這一說法。很多學者認為所謂“化神”亦應為“化人”。無論造人還是造神,這無疑關于繁衍,應為后代女媧造人的最早記錄。
根據“女性單獨化為十人”這一生殖崇拜推測,該神話應是源自原始社會母權制時期,其呈現了初民對女性孕子的解讀:人的降生是自然造化而成,女性僅為載體。出于對自然的畏懼以及有限的認知,初民基于原始崇拜和宗教信仰解釋自然現象如交配生育等,神化了視野所見的自然物以及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當然這也與母權制有關系,知母不知父的日常隱去了生育主體的一方,“無父感天而生”順應產生。
類似“上天為父,后土為母”等思想成為原始宗教信仰,使人們堅信自己的出生與所敬畏的自然有著緊密聯系。《易傳》中就記錄下了這種思想: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易·咸》彖)
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易·序卦》)[2]28
后世對各類古帝的降生都賦予了天子的神話色彩,目前文獻可考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感生神話即為《詩經》中記載的商、周兩族的始祖神話。
《詩經·商頌》中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3]647以及“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3]649講述了簡狄吞玄鳥卵生商契的感生神話。周代始祖棄的感生神話則見于《詩經·大雅·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3]503
這兩則神話都突出了同樣的元素:帝王為天子。比之母系氏族的眾生均為自然之子,這個時期的人民認為只有英雄人物才是上天之子。母系社會逐漸向父系社會過渡,父親角色的出現讓初民開始意識到生育可能是男女交配的結果。這點與眾生皆源自上天相悖,因此初民將與天攀附的心理寄托到了古帝傳說中——始祖為上天之子,身為后代也有榮與焉。
但這仍是原始崇拜和宗教信仰的反映。即使具備了解釋一些自然現象的能力,為了滿足信仰層面的與天攀附愿望,初民仍以天為尊,表達了原始人民對認識、征服自然的樸素情感和美好期待。這種期待下的異類生子母題均帶有神圣色彩,但并非迷信色彩,而是源自原始宗教的質樸幻想。
二、春秋戰國:宗教意義向政治目的過渡
這時的異類生子基本仍以感生神話為主,不過其自身發生了重要變化。
一是感生形式發生了本質變化,異于實際行為,首次出現了感生夢,即帝系感生神話的雛形。也就是在知父知母的情況下,以夢的形式將出身假托于天。《左傳》中記載了鄭穆公的感生神話: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鰷。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4]4075
感天而生不再是女性感外物而孕的實際行為,而是在夢中受“天使”指點之后孕育而生。早期以動物、人武等出現的神跡,開始以類人形象出現。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神的形象和內涵也一起發生了變化。不過并非神的自然屬性消失了,而是記載材料的史官更側重表現神對現實的實際表現和影響。至少在這則傳說中,政治目的超過了宗教意義。
鄭穆公之母《左傳》記載為“賤妾”,而“賤妾之子”卻登上了皇位,為了證明其皇位的正統性,成為上天之子是最好的選擇,畢竟上天的身份在鄭文公之上,上天之子比鄭文公嫡子的身份更為尊貴,也更有資格登上皇位。
這是感生神話第二個變化——創作目的的轉變。過去的感生神話并無政治目的,正是這一改變使其開始具備迷信色彩。這點還體現在《國語·鄭語》中的褒姒感生神話: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王使婦人不幃而噪之,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5]519
這則神話特殊在褒姒其人。以往感生神話中的主角一般都是正面的英雄人物,且均為男性。該傳說的背景為西周末年史伯與鄭桓公的一次對話,由于周幽王不顧諸侯意愿,倒行逆施,造成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鄭桓公問史伯:“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6]史伯正是在回答這個事關國家興亡以及個人安危的重大問題時講了這則故事。特別指出的是,此時下距西周滅亡還有三年,正是褒姒受寵之時[6]。此處引出褒姒感生神話是為了證明周幽王不配為王,于是上天派褒姒這位人獸結合生下的妖女來結束周政權。
該神話的政治目的更為明顯,聯合當時的天命觀,將周政權的覆滅歸為上天意志,諸侯吞并等行為不是禮崩樂壞、僭越之罪,乃是順應天命、替天行道。而且從中可以看出一個觀念變化:隨著解釋自然的能力增強,人們意識到了生子是男女結合的結果,實際人獸結合而生的變為了妖人,這也為后世異類生子提供了另一條敘事路徑。但由于時代限制,自然神還占據一定的地位,這還只是一種趨勢。
這兩個變化意味著在春秋戰國時期,異類生子母題中的感生神話已有向政治目的過渡的傾向,其變化的本身都在服務政治目的。
上博簡《子羔》中也能看出這個傾向。子羔問三王的父親是因地位低賤而被隱去姓名還是確實為天子,孔子回答三王是上天之子,與確為人子的舜以德受禪有所不同。孔子相信鬼神之說,認為三王無父感生是真實的,但其表達核心在于舜以德受禪,與天子無異,進一步鞏固“德治”的思想觀點,強調了人的道德主體性,認為德治才是獲取政權最合情合理的方式。
三、兩漢時期:政治神話和天人和諧
兩漢時,異類生子母題出現了三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從感生神話中誕生的帝系感生神話占了主導地位;人神結合,也就是人神戀的雛形作為政治神話的伴生產物出現;人獸結合生子趨向獵奇怪異。
帝系感生神話在漢代得到了充分發展。后世感生神話皆以感生夢作為主要形式,不再是人與異類實際的產子行為,且對象一般為帝王將相。在知其父母的情況下,這樣的神話明顯是出自政治目的的編造,可見其與天攀附的意圖,目的為教化、統攝百姓。《史記·高祖本紀》中記載了劉邦感生神話: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7]341
由于漢代盛行大宇宙論、萬物感生以及讖緯思想等,漢代感生神話將上天表述為一位干涉人間政權建構的至高神,同時將感生的帝王描述為天子[8]。古人普遍認為,政治和諧是靠“天人合一”來實現的,在這基礎上,政治神話開始興盛,感生神話徹底完成了政治化轉變。
這與武帝時期改先秦神系為以太一為中心的神系有關。此舉最重要的是重新定位了神的地位,改變了神、人等之前涇渭分明的局面,神的實用性超越了其本身的宗教信仰,人完全可以招徠其為現實生活服務。這也為異類遇合題材中人神遇合題材提供了基礎。
異類生子應是異類遇合題材的源頭之一。此時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僅為雛形的人神結合,應是政治神話的伴生產物。最早的人神戀題材約始于《高唐賦》《神女賦》,不過因賦體的浪漫傳統以及文人寄托情懷的可能,且其中人神相遇均是縹縹緲緲、似是而非,并不能和人神戀敘事中的實際行為相提并論。兩漢時期《孝子傳》的董永故事、《列仙傳》中園客、江妃二女故事也不能歸入其范圍。
繼承上古“和諧”的生命觀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兩漢結合儒家“天人感應”以及“大一統”思想,發展成了特殊的大生命觀。大生命觀強調總體性和統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個體生命的獨特性和自由性,在此觀念下產生的人神結合必定不會以個體間的情感為主線。《孝子傳》中董永和織女兩人并未相戀,而是“天令”織女為董永妻,重點在于表現孝心感天,而非人神結合。
董永者,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于富公以供喪事……女出門謂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耳。”[9]
《列仙傳》中的園客“姿貌好而性良”,與天女并未相戀結合;江妃二女與鄭交甫江上對話,雖頗有情趣,但也只是一場空歡喜。這三個故事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天人和諧的局面。因此可說,這類人神結合題材應是政治伴生的產物。
另一方面,由于人們的認識進步,神的形象已經和人十分相似,如從《山海經》中“豹尾虎齒而善嘯”轉變為《列仙傳》中雍容華貴的王母娘娘等。獸和神的含義徹底分開,人獸結合生子不再意味著傳遞神圣和與天攀附,而偏向怪異、獵奇。《博物志》卷三《異獸》“猴玃”最具代表:
蜀中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獼猴……名曰猴玃,一名馬化,或曰猳玃。伺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故取女也。取去為室家……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無異,皆以楊為姓。[10]25
另有《博物志》卷七所引《徐偃王志》的“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10]55等篇同可為證,這里的不祥也可理解為背離了天人和諧。
四、魏晉南北朝:個人生命意識的凸顯
魏晉南北朝時期異類生子母題已經逐漸不再是異類關系故事的主要元素。相對的,異類遇合得到了充分發展,數量眾多。在魏晉南北朝這個特殊時代,遇合這一元素明顯比生子更受青睞,這里遇合包括從戀愛到婚姻這一完整過程。
整個魏晉南北朝儼然就是一個亂世,除去戰亂天災,還有無止休的政治斗爭。生命的短促無常,以及個體的無可奈何等悲劇意識都充分展現在了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新的社會狀況改變了這一時期的人生追求和價值觀念,符合自由之美的思潮和審美開始興起。
此時正是玄學和佛教興盛之際。在玄學的影響下,人們更加在意自身處境、情感和人格。另一方面,佛教的傳入和佛經的翻譯使得想象世界愈加豐富,中國文學故事性空前進步。當生死問題變得常見時,面臨死無可避、生也短促的困境,人的個體生命意識凸顯出來,人們開始在幻想中思考如何逃避這種痛苦。
當人力難以改變現狀,人們自然而然將希望寄托于天,希望“天帝”哀憐人類,這種心理的內核是一種在無可奈何中求助上天的行為,仍屬與天攀附范圍。最早異類生子母題中最為突出的文化因子即為與天攀附,這時的感生神話雖然數量眾多,但總體沒有大突破,已與異類生子關聯不大,而且魏晉南北朝之后的感生夢神話很少。因此這一因子逐漸被異類遇合所繼承。
并且這一因子的含義和形式也隨著題材變化發生了相應的異化——人與異類的關系不再是上下的親子關系,而轉變成一種同級關系。由于感生神話的性質問題,普通人有類似感生夢的遭遇并不恰當,況且上天之子也沒能真正做到性命無憂。只有成為神仙,才能真正擺脫易死之局。修道成仙的傳說比比皆是,實施起來卻是辛苦萬分、難見曙光。之于普通人,有一種方法可以快速比肩神仙,那就成為神仙的配偶。此處的配偶比兩漢更多了情感色彩,即存在情感結合。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類人神遇合題材逐漸成熟,并占了主導地位,發展出了多種樣式,如“仙女下凡型”和“仙窟艷遇型”等。
張敏的《神女傳》應該是第一篇人神遇合的小說[11]。成為神的配偶,人具備了一定知曉“天機”的機會,相當于半人半神的存在,有了長壽的機遇。
兼注《易》七卷,有卦有象,以象為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兇,優揚子之《太玄》、擇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11]。
弦超與神女結合后能夠領會神女對卜筮之書的注釋,并據此觀天象預測吉兇——這樣的弦超已不再是凡人,他能夠為自己規避命運中的不祥,輕松延長自己的壽命。
同時期另一部典型人神遇合作品《杜蘭香傳》中也出現了神女贈送仙丹的情節。此題材另一類型“仙窟遇艷”型就更能體現出這種期望,這類小說中經常出現人從仙境返回人間后發現過去幾百年余的情節(或是沒有回去,直接留在了仙境),反映出仙境和人間的時間差距。這正寄托了此時人們對于長生的渴望。目前可見最早的“仙窟艷遇型”故事見于《拾遺記》卷十“洞庭山”條。
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采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12]444
純粹人獸結合生子的故事已經很少了,且一般被視為妖兆。《搜神記》中記載了一篇《馬生人》: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劉向以為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13]126
這里的解釋為妖異之事,雖不知這則故事究竟是傳自先秦,還是源自后世杜撰,但可察時人態度一二。在卷十二《五氣變化論》中提出“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13]214,也能反映視該現象為不祥之兆的態度。
而另一類異類遇合——人妖遇合則是繼承了異類生子母題中萬物有靈的文化因子。不過其中人的態度大多也是負面的,如驚異、厭惡等(也存在比較中性和積極的態度)。妖怪的性質與動物并無二致,而且比動物更加妖異。妖怪一般是自然物變化成人的,性質已與神截然不同。這種態度是隨著理性精神發展沿襲下來的,只是前朝此類故事較少而不顯突出。
《搜神后記》中記載了《老黃狗》《猴私宮妓》等故事,《三吳記》中的《白魚江郎》更能體現人類對妖怪的深惡痛絕,其中不僅包含遇合生子,還有對妖怪的處置方式。面對已經相愛并結合的異類,岳父可以直接開膛破肚,全家人可以面不改色吃下魚肉,妻子能夠無動于衷再嫁他人。無論如何,這樣的反應都顯得過于絕情。
異類生子中的“生子”元素意味著生命的進一步延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個人意識的激發使得人們更加在乎自身的生命體驗,及時行樂是這一時期最關鍵、灑脫的生活方式,直接的感情之樂更能刺激感官和生活,而遇合中或是獵奇或是艷遇等特征也更符合時人對于物欲或情欲的追求。畢竟遇合中與異類的關系處于主體,而在生子故事中的身份一般在于客體。后世一般也是遇合后再生子,生子只是遇合后的結果,可有可無,保存了其主體關系而略去客體關系。因此這一時期的生子元素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不會成為故事的核心。異類生子母題雖仍存在,但其原本含義已漸被異類遇合題材代替。
五、結語
異類生子母題從最初的感生神話,隨著人們認識的進步漸漸走向另一主題。其中最為突出的與天攀附文化因子被魏晉南北朝開始興盛的異類遇合主題所繼承,并為后世的小說奉獻了眾多題材,如其中的人神戀、人妖遇合等題材啟發刺激了唐傳奇,對后世明清小說也起到積極作用。唐傳奇中《補江總白猿傳》等小說還保留了一定的異類生子元素,如《游仙窟》《柳毅傳》等小說中人神遇合的故事寫得極為出彩,往后的清代小說《紅樓夢》中仍能見出人神遇合的元素。此外,狐妖、蛇妖等多種妖精形象也多次在作品中出現,吳承恩的《西游記》也多次采用人妖遇合元素。
參考文獻:
[1]郭璞.山海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程憬.中國古代神話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3]方玉潤.詩經原始[M].北京:中華書局,1986.
[4]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9.
[5]左丘明.國語[M].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組,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趙沛霖.褒姒的神話傳說及其文化思想價值[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04):50-56.
[7]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8]王倩.感生、異相與異象:“天命”神話建構王權敘事的路徑[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4(01):45-54.
[9]張乘健.敦煌發見的《董永變文》淺探[J].文學遺產,1988(03):26-36.
[10]張華,等.博物志(外七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李劍國.《神女傳》《杜蘭香傳》《曹著傳》考論[J].明清小說研究,1998(04):153-170.
[12]王嘉.拾遺記[M].北京:中華書局,2021.
[13]干寶.搜神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沈葉婷(2003-),女,漢族,湖南衡陽人,湘潭大學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