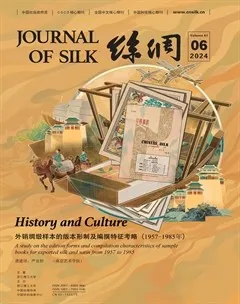“西化”與“化西”:近代中國女性婚禮頭飾變遷
梁惠娥 付雅雯 邢樂



Westerniz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Woman's wedding headdress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收稿日期:2024-01-02 ;修回日期:2024-04-3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一般項目(21BG142)
作者簡介:梁惠娥(1967—),女,教授,博導,主要從事服飾文化與服
裝設計的研究。
摘要:在西化思潮影響下,中國近代女性婚禮頭飾經歷了鳳冠蓋頭的落幕、花冠披巾的演變、西式頭紗的流行三個階段。本文通過對近代報刊雜志上刊登的結婚照與史料進行互證,重點探討了中國近代女性婚禮頭飾時尚化變遷過程中的“被動化西”和“主動化西”現象,進而探究變遷過程中所具有的開放性、簡潔性和自由性,并挖掘其對近代女性婚戀自由思想的影響。關鍵詞:鳳冠蓋頭;花冠披巾;頭紗;文明婚禮;近代服飾
中圖分類號:TS941.12; K892.9?????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001-7003(2024)06-0129-09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4.06.014
晚清時期婦女刊物《女子世界》于1904年第11期刊登了一則“創新婚禮”,關于從日本西京大學留學歸來的新郎廉某在無錫同新娘姚女士成婚的報道,被稱之為“文明婚禮的先導”。1905年該刊又報道了發生在上海、鎮江、長沙三地的“文明結婚三則”,被稱之為“改革的先聲”。這兩則新聞可以說是近代中國婚禮西化的初次實踐。其中,女性婚禮服飾在西化過程中具有時代性、變遷性和代表性[3]。目前學術界關于近代女性婚禮服飾的研究略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對于具有地域辨識度的文化區域[3]或城市[4-5]的女性婚禮服形制特征、變革成因等的研究,但此議題的具體細節仍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地方。例如,女性婚禮頭飾在近代西化思潮影響下經歷了怎樣的變遷過程?在整個變遷過程中,女性對于婚禮頭飾的使用是其自我意識覺醒后的主動接受,還是國家政策推動下的被動選擇?以及女性婚禮頭飾的變遷是否影響了女性身體自決、精神獨立的進步?基于此,本文選取近代女性婚禮頭飾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近代婚紗照的整理與剖析進而探討以上問題,以期更加全面系統地了解近代婚禮服飾時尚變遷的風格特征。
1 近代女性婚禮頭飾的時尚化變遷
南宋至晚清時期,受到傳統禮教影響,古代婦女婚禮頭飾使用鳳冠蓋頭以遮羞、避邪。到了近代,西化思潮帶來的西式頭飾進入中國,在與本土傳統頭飾融合后,衍生出改良后的半
傳統頭飾——花冠披巾[6],鳳冠蓋頭隨之退出歷史舞臺。
1.1 鳳冠蓋頭:傳統女性婚禮頭飾的落幕與閃現
中國“蓋頭”婚俗較早在南宋吳自牧的《夢粱錄》嫁娶卷中有所記載,新娘戴蓋頭于婚儀的“牽巾”之后,“交拜”之前,“并立堂前,遂請男家雙全女親,以秤或用機杼挑蓋頭,方露花容”[7]。從“方露花容”可知,蓋頭必須將新娘的頭臉遮掩嚴實,不允許有絲毫顯露。1975年,江西鄱陽縣磨刀石公社殷家大隊發掘的南宋洪子成夫婦合葬墓[8]中出土了一件戲瓷俑(圖1)。此女瓷俑頭戴“蓋頭”,在宋代南戲表演中扮演結婚女子的角色,這也印證了蓋頭在南宋時期用于婚俗[9]。宋代以后,女子出嫁戴“蓋頭”的風俗一直延續不衰,有清一代,更是上升為禮制規范。日本江戶時代曾任長崎地方長官的中川忠英,主持調查并出版了一本題為《清俗紀聞》的調查記錄,該書描繪了清代乾隆年間中國東南沿線一帶(江蘇、浙江、福建)的民間習俗、傳統習慣、社會情況等。書中對于“蓋頭”有這樣的記載:“新娘衣裳,內穿名為披風袂衣之平常衣服,外穿名為大紅圓領之上衣。頭上批蓋名為頭面覆之紅色披巾。”這個紅色披巾一直要到合巹酒后才能被揭下:“合巹完畢后,方可取下新娘頭面覆之披巾,脫下大紅圓領之上衣,換上天青色上衣。” [10]
與蓋頭搭配使用的為鳳冠。鳳冠是古代貴婦所戴的一種禮冠,因冠上飾有鳳凰而得名。其制初見于晉代,至宋代被確定為禮服。宋代后妃在受冊、謁廟等隆重場合,俱戴鳳冠。到了明清時期,鳳冠的形制更為考究,不僅裝飾珠花,而且還以金龍相伴。同時,明令規定除皇后、妃嬪之外,其余人未經允許一律不得私戴鳳冠。但是,由于明代民間奢靡之風盛行,普通民眾開始模仿貴族的裝扮,挑戰傳統的服飾等級制度。清末舉人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記載了民間婚禮使用鳳冠的情況:“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鳳冠者。”從中可以看出,民間婚禮鳳冠只是假借“鳳冠”之名,增添喜慶之色,其造型簡單,一般不綴龍鳳,僅綴珠玉、花釵等物,與明清時期皇后鳳冠相差甚遠,因此也稱之為彩冠[11]。
圖2[12]是1929年《良友》上刊登的倪逢吉女士與燕京大學教授梅貽寶博士的婚禮照。照片中倪逢吉女士佩戴鳳冠,其造型為從前額至肩綴有垂珠,遮擋面部,以此代替了蓋頭的作用。《良友》雜志對此評論道:“新人物行古裝婚禮。”同一期《良友》雜志的同一版面刊登了文學家冰心(謝婉瑩女士)與吳文藻博士的結婚照(圖3[12]),兩人皆穿著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新式婚禮服。兩對新人的兩幅婚紗照一左一右、一新
一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反襯出倪逢吉女士和梅貽寶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
1.2 花冠披巾:改良女性婚禮頭飾的誕生與演變
民國初期,隨著西式觀念的介入和近代社會的開放,政府極力倡導“文明婚禮”。“文明婚禮”是指借鑒或采用西方的婚禮儀式而有選擇性地摒棄瑣碎的傳統婚禮,這是民國時期婚禮儀式的一種轉變。1912年,民國政府頒布了第一個正式的服飾法令《服制》,將西服納入禮服體系中,這一法令同時也促進了女性婚禮服的西化進程。1928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婚禮草案》正式規范了中國式“文明結婚”的細則,推動了“文明結婚”的全民化進程。《草案》要求新娘不再穿著上襖下裙、鳳冠蓋頭,而改著禮服長裙,頭戴珠冠花環,披罩紗。其中的“珠冠花環”,實則借鑒了清末鳳冠的造型,并改用大量花朵作為裝飾物;而“罩紗”則是模仿了西式頭紗的造型,但因在中國傳統婚嫁禮俗中,并不崇尚紗質這類透明或半透明的材質,所以中式頭巾采用了淺色的綢緞或其他不透明的面料[6]。
然而,早在20世紀10年代,女性婚禮頭飾就已經開始采用花冠與頭巾的結合。這一時期沒有官方法令的規范,且人們對于新式婚禮的接受仍需要有個消化的過程,因此,花冠披巾在造型上呈現豐富多樣的形式。根據花冠的造型、披巾的長度,筆者將花冠披巾大致分為三種類型,即普通式花冠披巾、綢球式花冠披巾、無冠式花冠披巾。普通式花冠披巾如圖4[13]所示,此圖是1917年北京女師范校長姚崇光之子姚鋈與北京高等師范校長陳筱荘之女陳淑諼的結婚照。陳淑諼佩戴的花冠披巾仍以花冠為底,特色之處在于其披巾的長度和寬度,長長的披巾似白綾一丈,可以將新娘的身體包裹得嚴嚴實實。在新式婚禮中,新娘可以全程露面,雖然花冠披巾沒有了蓋頭遮面,但取而代之的卻是披巾遮身。這一類型的花冠披巾在造型上繼承了傳統蓋頭的遮蔽性,屬于民國初期婚禮頭飾的過渡時期,可以看作民國初期婚禮服飾在西風東漸影響下的一次探索性發展。
民國時期流行時裝表演,展出的服裝都是當時紅極一時的新潮樣式,并對時尚潮流產生重要影響。1930年11月,北平緊隨上海后舉辦時裝表演會,此次表演分別展示了明清、民初現代的新娘服,以及婚禮中的坐帳、交杯儀式等,服裝借自梅蘭芳,并由其提供穿衣指導。梅蘭芳是民國時期著名的京劇演員,擅長旦角,此次表演會展出的新娘服很有可能是來自戲曲演出,那么可以推測戲曲服飾在民國時期對女性婚禮服和時尚潮流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此外,可以從綢球式花冠披巾中看出戲曲元素的影子,如圖5[15]和圖6[16]所示。在傳統戲曲中,很多角色的頭飾是用綢子系結而成的,俗稱“綢子打頭”,以示貧苦、顛沛流離或戴孝的人物特征[17]。而花冠披巾的造型與“綢子打頭”有異曲同工之妙。戲曲中的綢球有單頂
球和三頂球之分,單頂球即頭頂正中的一個大球,稱為頂球;三頂球,還包括鬢角兩側的偏球。因此這一類型的花冠披巾也有單頂球式和三頂球式之分。圖5是1919年溧陽狄芝生與蔣頻珍女士的結婚攝影。蔣頻珍穿著淺色綢襖和馬面裙,頭上的花冠上綴一朵大花球,花球圓、密,大小與新娘的頭顱接近。圖6是1918年周介春君與張舜儒女士的結婚攝影。張舜儒佩戴的披巾花冠不僅在頭頂裝飾一朵大花球,而且在兩腮邊下方處點綴兩朵小花球。左右兩小花球大小相等,且與大花球比例協調。
進入20世紀20年代,隨著西方婚禮觀念的不斷深入,花冠披巾開始向西式頭紗的造型過渡,摒棄了傳統的中式冠頂,逐漸簡化為無冠披巾。相較之前兩種花冠披巾,無冠式花冠披巾在造型上更加接近西式頭紗,披巾的長度明顯縮短,最大的不同之處則是在材質上堅持使用中式綢緞。圖7[18]是1926年北京仁立寶業公司總務處長沈釘毅君與愛國女校高材生孫乃珍女士的結婚攝影。孫乃珍戴的披巾沿著發際線罩住頭發,上邊緣將花邊打褶形成半圓花環形狀,頭頂沒有了冠底和綢花造型,兩鬢處收緊固定,披巾長度縮減至胸前。
1.3 西式頭紗:新式女性婚禮頭飾的接受與流行
20世紀30年代,西式頭紗開始廣泛流行起來,其造型結構同花冠披巾類似,包括頭冠和頭紗兩部分。根據兩者材質及組合形式的不同可分為珠冠頭紗、花冠頭紗和無冠頭紗三種類型。珠冠頭紗(圖8[19])以珠子作為冠底,后接頭紗;花冠頭紗(圖9[20])以小型花朵作為冠底,較花冠披巾更為簡化;無冠頭紗(圖10[21])則是直接將兜紗罩在頭部。西式頭紗與花冠披巾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材質,西式頭紗的材質大多為舶來品,如白銀細格閃紗、銀條方格閃紗等。
至30年代后期,西式頭紗的樣式更加多樣化。1937年第2期的《家庭雜志》中展示了當時歐美流行的最新樣式頭紗,如圖11[22]所示,從左到右分別是衡型式頭紗、流線式頭紗、云映式頭紗、圍浪式頭紗。據當時的雜志報道,衡型式流行于好萊塢,頭紗背部折成兩層花狀,且兩端裝飾銀光花邊;流線式流行于美國紐約,銀條方格閃紗能閃出光亮,且銀光花邊裝飾褶成波浪形;云映式流行于法國里昂,亮點在其背后的堆褶及兩旁的絹花;圍浪式流行于法國巴黎,上流階層舉行教堂或寬大禮堂婚禮時使用為多。
2 “西化”與“化西”:近代女性婚禮頭飾變遷的緣由
近代西學之風盛行,“關于怎樣接受西洋文化的問題”[23]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變革所面臨的重要問題。“西化”是伴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傳播而產生的一種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現象,近似于“向西方學習”的概念,近代中國掀起的西化思潮經歷了從“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的發展階段。“化西”作為“西化”的一種方式,不同于“中體西用”保全儒家思想的本質,化西是對西學的全面化用,即以全面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為前提,以本土化意識為視角,使西方的優秀文化為我所用,進而以吐故納新的姿態走向現代化[24]。近代女性婚禮頭飾在學習西方文化的過程中,結合近代社會基本國情,不斷挖掘中國傳統婚服與西式婚紗的契合因素和融合方式,進而實現了中國女性婚禮服飾的現代化轉化。
2.1?? 國貨運動:近代女性婚禮頭飾的“被動化西”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布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法令,如剪辮、易服、改元。其
中,隨著政治革命而來的改易服式浪潮對傳統衣帽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阻礙力。1911年12月,南京、蘇州、上海、杭州4個同業公所以“提倡國貨,發展實業,改進工藝,推廣貿易”為宗旨,成立中華國貨維持會,與臨時政府的易服令抗衡。在臨時政府提交參議院討論的服制草案中,中華國貨維持會認為“發辮固宜割截,禮服尚待磋商……曾見維新之輩,紛紛改效西裝。國貨銷場日滯,銀錢輸入外洋”[25],力爭將原草案中的“綢呢并用”改為“用中國自制呢”。1912年10月,政府對民族資產階級倡用國貨的意見作出積極回應,在正式通過的《服制》中明確規定了“料用本國絲織品或毛織品”。因此,選擇國產面料是在穿用西式服裝大勢所趨下的關鍵所在。這一規定同時也影響到了婚禮服飾,其中花冠披巾的產生可以說是國人在女性婚禮頭飾上的化西實踐。
有學者認為,民國服裝中的化西方式更立足于現實,考慮了中國本土文化的留存問題及國人對其背后隱含的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的接受問題,以期通過更加自然的方式消除近代國人在接受西方服飾文化時的思想障礙[24]。隨著服裝西化之風的不斷深入,以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對禮服西化的堅決推行,國人開始意識到近代社會服裝西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但考慮到洋貨的大量入侵對國貨經濟的沖擊,他們又不得不采取一些折衷手段以解決國貨與洋貨之間的矛盾。就近代婚禮服飾而言,國人把西式頭紗的簡潔造型“拿來”結合戲曲頭飾元素,并基于服制中勸用國貨的要求,以中式傳統綢緞代替透明紗質作為面料,從而形成了中西風格結合的婚禮頭飾。這次由政府主導的、被動的化西選擇,一方面,維持了國貨經濟的正常運行和優秀傳統服飾文化的代代傳承;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國人在接受西式婚紗時尚時,擔心被扣上“不愛國”“道德失范”等帽子的思想障礙,為后來國人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服裝的現代化奠定基礎。
2.2 審美驅動:近代女性婚禮頭飾的“主動化西”
孫中山認為,“洋布便宜過土布,無論是國民怎么樣提倡愛國,也不能夠永久不穿洋布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國民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那便是和個人的經濟原則相反,那便是行不通”[26]。雖然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的《服制條例》與1912年一樣,明確規定男女禮服均采用“絲麻棉毛織品”,但也無法消除國人對洋布經濟實用優勢的追求,民眾著裝開始全面西化。這一現象并不簡單地反映在許多人都趨向穿西服的選擇上,實際上服裝西化已經極大地改變了國人對服飾美的傳統觀念,開始認同西方服裝觀念中的窄衣文化與人文主義,完成了近代服飾從以“禮”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現代化轉變。
20世紀30年代,西式頭紗成為婚禮頭飾的主流形式。其中,以名媛淑女、電影明星為代表的上流社會女性,成為西式婚紗在中國傳播的代言人。1927年,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上海舉行基督教式婚禮,宋美齡以身穿禮服、頭披白紗、手持捧花的新式新娘形象露面,至此之后選擇西式婚紗結婚的新人愈來愈多[3]。1933年,民國時期知名電影女明星胡蝶與潘有聲結婚時,同樣也選擇了西式婚紗,頭飾方面則采用了當時流行于法國巴黎的圍浪式頭紗,這是此款頭紗首次為中國人所使用[22]。同時,他們的結婚照先后在《電聲(上海)》《明星(上海1933)》《玲瓏》《藝聲》《北洋畫報》等當時著名的電影刊物、婦女雜志中大肆報道。1935年,上海舉行了第一屆集團結婚,要求新娘一律穿著素色綢質連衣裙,頭束白紗。1937年,《家庭雜志》展示了當時流行于歐美的4款最新樣式頭紗,其中頭紗的介紹和評論通過翻譯的方式為國人了解。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化西的方式,在不同語言的轉化過程中,語意由于譯者的本土身份及其所處文化語境的的差異,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服裝評論及其思想內涵的化西現象。
綜上所述,在以審美驅動為內在動力、以名人效應和政策倡導為外在推力的三重作用下,近代婚禮頭飾完成了從“被動化西”到“主動化西”的西化過程,扮演著時尚初探者和引領
者的角色,激活了中國婚禮服飾文化中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成分。
3 “西化”與“化西”對近代女性婚禮頭飾變遷的影響
20世紀以來,西服東漸之風使得女性婚禮頭飾的造型一直處于動態的變化之中,但總是朝著簡潔和西化的方向發展。近代女性婚禮頭飾的這一變遷過程不僅營造出都市新娘的新式形象與文明婚服的新式裝束,而且還體現了婦女解放運動下婚戀觀念的進步和女性自決力的覺醒。
3.1 生理學知識與婚禮頭飾的開放性
英國人類學家、民俗學家詹姆斯·喬治·弗雷澤(JamesGeorge Frazer)在其著作《金枝》中指出:“神人既不能觸地也不能見天,其理由,一方面是恐怕接觸了天地之后神性的毀滅力量將發泄于天地,另一方面又怕神人具有的微妙神性一瀉無余……原始人認為神人寶貴而又危險的生命,無論放在天上或地下都不如懸在兩間之中最為安全無害。” [27]在中國傳統婚禮儀式中,新娘離開娘家時,要由人背上或抬上花轎,到婆家時腳不能沾地,要踩在麻袋或氈布上,同時一直要戴上蓋頭,直到拜堂為止。諸如儀式不僅將新娘與天地分隔開來,而且也確保新娘避免遭受外人或邪魔的侵害。根據法國民族志學家、民俗學家阿諾爾德·范根納普(Arnold van Gennep)[28]的過渡儀式理論可知,拜堂前蓋著蓋頭的新娘處于邊緣階段,她在結構上是“不可見的”,在儀式上又是具有“污染性的”,也就是說,她容易受邪魔侵害,同時自身也具有侵害他人的力量。因此,蓋頭在這一儀式中是必不可少的用品,起著隔離且避邪的功能。
到了近代,受到西方先進科學知識和生理學知識的普及,國人開始意識到男女“身體之構造同,腦筋之維系同” [29],男與女其實在身體、智力、能力等方面并無高低貴賤之分,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對于“封建社會中女性是污穢的”這一觀點的反駁。因此,新娘在從娘家到婆家的出嫁過程中無需使用具有保護功能的蓋頭以隔離、避邪,可以大大方方地露出面容,傳統蓋頭開始失去其實用價值,且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中。
3.2 剪發運動與婚禮頭飾的簡潔化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使得婦女解放運動進一步深入,不僅工、商、學各界婦女大聯盟,連歌女、妓女也投入其中,聲勢浩大。同時開始大力提倡婦女剪發,但由于無政治壓迫、無滿清刺激、無歐美婦女參照標準等原因,剪發運動進行得并不順利。直到1925年,歐洲婦女的剪發之風開始盛行,發式也愈剪愈短,“露出耳朵,露出頭型,露出頸部,短得和男人一樣”“女界斷發之流行,以巴黎為根據地,風靡歐洲,今將及于全世界”,于是中國婦女有所參照了。加之1926年“北伐戰爭”,婦女剪發從軍、支援后方,與軍閥作戰,增強了婦女自覺剪發的決心。中國著名女兵作家謝冰瑩在服兵經歷回憶錄《女兵自傳》中寫道,當時的男軍長認為女生隊最緊要的事情是她們“要把臉上的胭脂粉洗得干干凈凈,不要留一絲痕跡在上面,頭發一律剪短,最好是剃光”[31]。現代中國的女人截發之為普遍化,縱不是受歐戰之后的西風東漸的影響,亦必是自民國十四年(1925年)以來的北伐高潮的產物,或許還是由于這兩種潮流至相激相蕩,卷起波瀾,終于才有這么四處泛濫的猛勢[32]。
婦女剪發運動最直接的影響則是頭飾的簡化,“首飾業,因年來女子提倡剪發,頭上裝飾品已不適用,解放女子,更不樂穿戴金飾”。傳統婦女的挽髻可以承載繁重的飾物,如婚禮儀式上的鳳冠蓋頭,但沒有了發髻的支撐,裝飾繁復的鳳冠很難固定在短發上;相反,簡約的西式頭紗對發型要求低,更容易佩戴在短發上。因此,婦女剪發運動促使新娘對婚禮頭飾的要求從繁重轉向簡約,從中式傳統轉向西式時尚。
3.3 婚戀自決與婚禮頭飾的自由性
近代婚禮頭飾從中式繁復到西式簡約的這一演變過程,從表面上看是民國西學之風盛行之下對于“文明婚服”與“文明結婚”儀式的借鑒與模仿,本質上則是近代女性戀愛婚姻觀念的轉變與進步。在婦女解放運動期間,許多革命者和思想家都對封建婚姻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提出了婚姻家庭革命。如果從女性對自我認識的角度評析近代婚姻制度的改良之路,那么可以歸結為女性戀愛婚姻觀念從“無我”到“發現自我”的轉換[34]。清末,在傳統禮教的嚴苛規訓下,幾乎所有的婦女都遵循著“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女教戒律。這一時期的婦女在婚姻里面沒有自主選擇的權利,必須聽從父母的安排,即“無我”。到了“五四”時期,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社會各界對女性作為個人獨立問題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引起了女性對婚姻戀愛自由度要求的重視。
現代女作家張愛玲認為:“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35]民國時期,以張愛玲為代表的名媛淑女們將衣服作為她們追求時尚、展現自我的表達方式,尤其是在結婚場景中,通過自主設計,表達出“我的婚姻,我做主”的婚戀主張。民國才女林徽因因為當時在加拿大買不到中式禮服,又不愿意穿著千篇一律的西式婚紗,于是在自己大喜之日時就設計了一套旗袍式裙裝(圖12[36])。頭飾的部分更是美麗而別致,冠冕似的帽子兩側,垂著長長的披紗,帽子正中裝飾纓絡。這一設計既有別
于西式頭紗,又不同于花冠披巾,是專屬于林氏的獨具匠心。林徽因雖然一直接受西式教育,但在服飾穿著上依然遵循中式風格,日常穿搭大都是淺色中式上衣和深色裙子,對于婚禮服的自主設計是她追求民族形式的一次創作與嘗試。
中國女性人類學研究學者禹燕提出的“倒置的金字塔”理論認為,作為正常人的存在,其生存結構應該是“精神存在”在上,“社會存在”在中,“自然存在”在下的完美金字塔形狀;但中國古代婦女長時期受到父權制的壓迫,導致女性存在結構發生變異,作為底座的“自然存在”上升為頂端,作為頂端的“精神存在”則下降為底座,形成了倒置的金字塔形狀[37]。“五四運動”之后女性開始從思想上、行動上積極主動地追求戀愛婚姻的自由,喊出了“我的事我做主”的自我主張,這與“五四運動”之前,在中國精英男性話語權領導下以“救國救亡”為價值訴求的婦女解放運動不同。受到先進思想影響的女性認識到完整的“人的存在”的重要性,開始強調要爭取獨立的思考與獨立的人格,尤其是在自由婚姻中,要展示自己的主體意識和掌控能力。她們不甘受約于傳統中式與新興西式婚禮服的規制,以勇往直前的姿態改進、引領近代婚禮服飾變革,顯示出創造自我、模塑自我的身體主動和身體自決,從而提升女性精神存在的層面。
4 結 語
“西化”與“化西”現象共同揭示了近代女性婚禮頭飾發展變遷的內因、現狀和趨向。首先,僅存在于特定歷史時期的花冠披巾是國人對待西化思潮特有的化西實踐,女性婚禮頭飾從花冠披巾到西式頭紗的這一過渡階段,既包括面對國貨運動時的被動選擇行為,又包括認同西式審美后的主動使用行為;其次,在男女平等、發現自我等西化思潮的影響下,近代女性婚禮頭飾的時尚化變遷過程,既體現了頭飾從遮蔽面部到顯露面部的開放度進步,又展示了女性在中西式風格之間轉換融合的自主性設計,更意味著女性婚姻形象從傳統到新式的現代化構建。
傳統女性婚姻形象是在封建禮教背景下,圍繞男性主體意識所形成的,而新式女性婚姻形象則是在以西化思潮為外在推力、以化西實踐為內在動力的雙重力量下催化而成的。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女性婚禮服飾時尚逐漸脫離封建禮教和男權視野的限制,開始了美就是權力的服飾變革,對于引導現代女性服飾時尚發揮了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佚名.記事:國內:創新婚禮[J].女子世界,1904(11):70.
Anon.Memorabilia: Domestic: Innovative wedding[J].Women s World, 1904(11): 70.
[2]佚名.記事:國內:文明婚禮[J].女子世界,1905(3):85.
Anon.Memorabilia: Domestic: Civilized wedding [J].Women s World,1905(3): 85.
[3]王中杰,梁惠娥,邢樂.近代吳文化地區新式婚禮中女性婚服特征分析[J].絲綢,2018,55(9): 86-91.
WANG Z J,LIANG H E,XING L.Feature analysis of women s wedding dresses in new-style weddings in the Wu culture region in modern times[J].Journal of Silk,2018,55 (9): 86-91.
[4]謝夢彬,王蕾,邢樂.民國時期上海女性西式婚禮服特征分析[J].絲綢,2020,57(6): 108-113.
XIE M B,WANG L,XING L.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Western wedding dresses of women in Shanghai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J].Journal of Silk,2020,57(9): 108-113.
[5]付育川.近現代北京地區女性婚服變遷研究[D].北京:北京服裝學院,2021.
FU Y C.Study on the Change of Female Wedding Dress in Beijing Area in Modern Times [D].Beij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2021.
[6]李婧晗,賀陽.淺談民國時期婚禮旗袍的頭飾[J].藝術設計研究,2012(4): 49-52.
LI J H,HE Y.Study on the headdress of the wedding cheongsa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J].Art & Design Research,2012(4): 49-52.
[7]吳自牧.夢粱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WU Z M.Meng Liang Lu [M].Hangzhou: Zhejia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1984.
[8]唐山.江西鄱陽發現宋代戲劇俑[J].文物,1979(4):6-9.
TANG S.Drama figurines in Song Dynasty found at Poyang,Jiangxi [J].Cultural Relics,1979 (4): 6-9.
[9]張彬.宋代女子首服“蓋頭”考釋[J].裝飾,2020(6):68-71.
ZHANG B.An interpretation of women s head dress “ Gai Tou” in Song Dynasty[J].ZHUANGSHI,2020(6): 68-71.
[10]方克.清俗紀聞[M].北京:中華書局,2006.
FANG K.Records of Qing Customs[M].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6.
[11]陳勤建.中國風俗小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CHEN Q J.A dictionary of Chinese customs [M].Shanghai: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2008.
[12]聶光地.結婚留影:中西合壁[J].良友,1929(38):21.
NIE G D.Wedding photo: East meets west [J].The Young Companion,1929 (38): 21.
[13]佚名.姚鋈君與陳淑瑗女士結婚攝影[J].婦女雜志(上海),1917,3(3): 10.
Anon.Wedding photo of Yao Ban and Chen Shuyuan [J].The Ladies Journal (Shanghai),1917,3 (3): 10.
[14]聊.記北平之服裝表演[N].北洋畫報,1930-11-25.
Liao.A record of the costume performance in Beiping [N].Beiyang Pictorial News,1930-11-25.
[15]佚名.溧陽狄芝生君與蔣頻珍女士結婚攝影[J].婦女雜志(上海),1919,5(8): 5.
Anon.Wedding photo of Di Zhisheng and Jiang Pinzhen in Liyang [J].The Ladies Journal (Shanghai),1919,5(8): 5.
[16]佚名.周介春君張舜儒女士結婚攝影[J].婦女雜志(上海),1918,4(11): 12.
Anon.Wedding photo of Zhou Jiechun and Zhang Sunru [J].The Ladies Journal (Shanghai),1918,4(11): 12.
[17]劉月美.中國京劇衣箱[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
LIU Y M.The Wardrobe of Chinese Beijing Opera[M].Shanghai: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2002.
[18]寶記.新家庭:北京仁立寶業公司總務處長沈釘毅君與愛國女校高材生孫乃珍女士結婚攝影[N].圖畫時報,1926-12-12.
BAO J.New Family: Wedding photo of Shen Dingyi,General Affairs Director of Renli Baoye Company in Beijing,and Sun Naizhen,a senior student of patriotic girls school[N].Tu Hua Shi Bao,1926-12-12.
[19]佚名.沈矯如君與孔曝如女士結婚儷影[N].圖畫時報,1928-10 -24.
Anon.Wedding photo of Shen Jiaoru and Kong Jingru [N].TuHua Shi Bao,1928-10-24.
[20]佚名.屈振邦君與王淑琴女士結婚攝影[N].圖畫時報,1927-05-25.
Anon.Wedding photo of Qu Zhenbang and Wang Shuqin[N].Tu Hua Shi Bao, 1927-05-25.
[21]佚名.新家庭:新加坡華僑巨子黃奕住君之第六公子天恩君與傅香姑女士結婚之紀念[N].圖畫時報, 1926-03-21.
Anon.New Family: Wedding photo of Huang Tian en, the Sixth Son of Singaporean Chinese Tycoon Huang Yizhujun, and Fu Xianggu[N].Tu Hua Shi Bao, 1926-03-21.
[22]何漢章.兜紗婚禮服新設計[J].家庭雜志,1937(2):20.
HE H Z.New design of wedding veils [J].The Family Journal,1937(2): 20.
[23]張佛泉.西化問題的尾聲[J].國聞周報,1935, 12(30):13.
ZHANG F Q.Epilogue of the Westernization issue [J].Guo Wen Weekly, 1935, 12(30):13.
[24]張競瓊,許曉敏.近代服裝新思潮研究[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 2018.
ZHANG J Q, XU X M.Study on New Trends in Modern Clothing [M].Beijing:China Textile & Apparel Press, 2018.
[25]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Institute of Histor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e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Shanghai [M].Shanghai:Shanghai People Press, 1981.
[26]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孫中山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 1986.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omplete Works of Sun Yat-sen[M].Beijing:The Public Art and Literature Press, 1998.
[27]詹姆斯·喬治·弗雷澤.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M].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 1998.
FRAZER J G.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M].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1998.
[28]阿諾爾德·范熱內普.過渡禮儀[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
VAN GENNEP A.Rites of Passage [M].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29]金天翮.女界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JIN T S.Nu Jie Zhong [M].Shanghai:Shanghai ClassicsPublishing House, 2003.
[30]佚名.歐洲歸客談斷發流行[N].民國日報(上海),1927-08-23.Anon.European returnees talk about the haircut epidemic [N].Republic of China Daily (Shanghai), 1927-08-23.
[31]謝冰瑩.女兵自傳[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
XIE B Y.Autobiography of a Female Soldier [M].Chengdu: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5.
[32]曙山.女人截發考[N].論語,1933-11-16.
SHU S.Study on woman haircut[N].Lun Yu, 1933-11 -16.
[33]佚名.廣州商業衰落不堪[N].晨報,1928-02-20.
Anon.Guangzhou s commercial decline is unbearable [N].Chen Bao, 1928-02-20.
[34]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LUO S W.Women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M].Shanghai:Shanghai People Press, 1996.
[35]張愛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ZHANG A L.Liu Yan [M].Beijing:Beijing Shi Yue Wen Yi Publishing House, 2012.
[36]張清平.林徽因傳[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
ZHANG Q P.Biography of Lin Huiyin [M].Tianjin: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07.
[37]禹燕.女性人類學雅典娜一號[M].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46.YU Y.Female Anthropology[M].Beijing:Oriental Press,1988:46.
Westerniz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Woman's wedding headdress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LIANG Hui'e1'2, FUYawen1a, XINGLe1b
1a.College of Texti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2.School of Media and Arts Wuxi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ization, Chinese woman's wedding headdress has been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modern times including the fall and flash of the phoenix crown and Gaitou the birth and evolution of shawls with a flower crown the acceptance and popularity of Western-style veils.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rituals ancient women used the phoenix crown when they got married to conceal disgrace and avoid evil.In the 1910s, with the active advocacy of “civilized wedding”, woman,s wedding headdress with Western-style elements became the improved headdress that is the ordinary type the silk ball type and the crownless type.In the 1930s Western-style veils were widely popular and according to their shape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veils with a pearl crown veils with a flower crown and crownless veils.
In the 1910s and 1920s it was necessary to take some compromise means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national and foreign goods because of Western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foreign goods on the national economy.In terms of wedding headdress in the modern times the Chinese borrowed the shape of Western-style veils and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silk instead of transparent gauze as the fabric thus forming shawls with a flower crown that combined Chinese and Western-styles.This marked a passive choice in the Westernization of modern women,s wedding dresses.In the 1930s, people wore the Western-style clothing and began to identify with the slim style clothing culture and humanism in the Western costume concept.Therefore modern wedding headdress with aesthetic drive as the inner driving force completed the Westernization process from “passive Westernization" to "active Westernization“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celebrity effect and policy advocac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modern woman,s wedding headdress began to be open, simple and free under the Westernization.Firstly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advance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hysiological knowledge the Chinese people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erms of body intelligence and ability, and denied the view that "women in feudal society were filth”, so Gaitou, which served to isolate and avoid evil,was abandoned, and the bride no longer needed to cover the face.Secondly, the rise of the woman, s hair-cutting move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implification of woman,s headgear.The simple Western-style veil had less requirement on the hair and was easier to wear for short hair, so woman, s wedding headdress ornament began to shift from being heavy to being simple.Furthermore the Westernal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n imitation of "civilized wedding dress" and "civilized marriage ceremony”, but it was essentially the progress of modern woman,s marriage concept, which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o self" to "discovery of self”.Women began to demonstrate their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control ability in their marriage and they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rul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wedding dresses.So they boldly led the modern wedding dress fashion.
Key words phoenix coronet and Gaitou veils with a flower crown wedding veil civilized wedding modern costu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