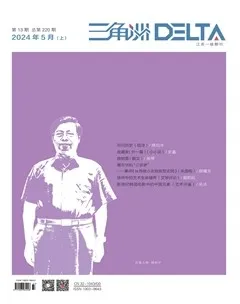《黃仕強傳》中的多元文化交流
季佳陽 齊嘉銳 屈玉麗
《黃仕強傳》附在《普賢菩薩說此證明經》前后,它的創作受到了中原文化與佛教文化的共同影響,在敦煌小說中具有代表意義。因此,對其進行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國傳統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情況,進而探索佛教本土化的道路。本文從《黃仕強傳》的創作概況出發,通過對《黃仕強傳》基本信息和創作背景進行梳理,通過對文本形式與內容進行分析,能夠有效挖掘文本所蘊含的佛教中國化以及民間文化內容,進而探討其中多元文化的交流與體現,分析總結《黃仕強傳》所體現的多元文化之融合。
敦煌小說《黃仕強傳》講述了黃仕強與屠夫同名,遂被冥使誤抓,自訴冤屈,得以再次核查案件,又因為抄寫《普賢菩薩說此證明經》(后簡稱《證明經》)最后復生的故事。故事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的交融。《黃仕強傳》與《證明經》共抄一卷,宣揚佛教義理的同時,既反映了民間信仰,又體現了多元文化交流。
《黃仕強傳》所見佛教中國化
佛教中國化指佛教在中國傳播時逐漸被中國民眾所認可,并最后納入我國古代社會的精神信仰的過程。《黃仕強傳》是唐人為宣教所作的靈驗故事,文本形式和文本內容都體現了佛教中國化。
一、文本形式所見佛教中國化
從文本形式看,《黃仕強傳》同《證明經》共抄一卷,與《證明經》不可分割。而《證明經》又篇幅短小,疑似中原所造。因此,這一文本形式中原文化特征與佛教文化特征兼存,體現了佛教文本的中國化。
首先,《黃仕強傳》與《證明經》共存一卷,小說與經文的結合,是漢傳佛教一種特殊的傳教方式。宣教故事在當時被人們視作經書的一部分,抄寫亦可起到消災禳禍的目的,因而敦煌產生了相當的宣教故事抄本,甚至有些抄本末尾題記還會綴寫“抄經一卷”等字樣。因此,宣教故事與被宣傳佛經共抄的情況符合當時人們視佛教靈驗故事為經書一部分的觀念,將《黃仕強傳》作為《證明經》的一部分進行了連綴抄寫。而這樣的抄寫形式區別于早期佛經的面貌,是佛教中國化的表現之一。
其次,疑偽經常用的編撰方式是提取某部或多部譯經,模仿譯經的結構集撰而成。《證明經》由《黃仕強傳》、正文A部、《佛說證香火本因經第二》組成。正文A部、《佛說證香火本因經第二》為模仿譯經的結構而成。但《證明經》以“聞如是”開篇,交代了說法地點和聽法人物,不同于佛經的基本結構,說明其撰寫過程中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
因此,在文本形式上《黃仕強傳》的整體面貌都體現出了佛教的中國化。
二、文本內容所見佛教中國化
在內容上,《黃仕強傳》將佛教思想與本土觀念相融合,具有鮮明的中原文化特色。
首先,文中基于百姓現實生活建構了地府環境。中國人相信地下的情狀和人間相仿,地府成為與陽間相似的人間都市,這是佛教地獄觀念本土化的體現之一。在《黃仕強傳》中,冥府被描寫得如同現實世界一般:
初入一土城內,如今時州縣城相似。入銅城內,入銀城內,又入金城內。
其次,文中地府官僚體系對現世官府體系的挪用體現了佛教世界觀與中原文化的融合。地府中閻羅王主持公道,守文案人與把文書人負責已逝之人文案的核查與校對,共同構成地府的行政組織。而佛教認為人死后進入地獄,直接承受苦難,無行政組織。
再次,《黃仕強傳》對故事情節進行本土化的建構。其一,由“勾命收魂”而入冥的情節是對佛教宣教故事進行的中國化創造。文中四人來取黃仕強的性命,這種情節在冥游類故事中很常見。
蔣王府參軍沈伯貴,前隨王任安州之日,住在安陸縣保定坊黃仕強家。其仕強先患痃癖,連年累月,極自困篤。去永徽三年十一月,忽然身死。初死之時,見有四人來取,一人把文書,一人撮頭,二人策腋,將向閻羅王處。
文中黃仕強入冥需由四人取命,而在佛教中,入冥之法同自身業力相關。進入六道輪回,承受相應果報,無需地府使者帶人入冥。其二,文中的守文案者向黃仕強索要錢財,改變主人公的生死。以地獄來反映現實,以冥吏的索賄比擬人間官吏之腐敗,是地獄本土化和世俗化的體現。其三,黃仕強在地府中的表現,體現著孝道思想。“仕強諮守文案人云:‘仕強父母死來得廿許日,欲請相見,復得已不?”在文中,黃仕強死后在陰曹地府也心系已經離世的父母,文本對于孝心的宣揚亦體現著佛教的中國化。
最后,黃仕強抄寫《證明經》的目的符合中國民間信仰的基本特點。民眾抄寫《證明經》是為了借助神明庇佑以解決眼前的困難。正如守文書人讓黃仕強抄寫《證明經》是為了讓黃仕強增加陽壽。黃仕強復生后抄經,進而消除痃癖,表明信仰普賢菩薩可以去除疾病。《黃仕強傳》將信仰普賢菩薩的功用融入入冥故事的抄經環節中,也體現著佛教中國化。
多元思想的交融與體現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為了在中國更好地傳播,因此會和我國傳統思想文化進行融合。多元思想之交融。
一、佛教與道教思想的融合
首先看審判行為。佛教認為人死后直接承受業報,無審判一說。文中黃仕強由閻羅王審判后承受殺生業報。審判行為同道教冥界考治有關,指在冥界對亡魂進行拷問。如《太平經》:“大陰法曹,計所承負,除算減年。算盡之后,召地陰神,并召土府,收取形骸,考其魂神。”可見道經中將死者進行拷問,頗似文中黃仕強接受閻羅王審判。
其次是審判經過。黃仕強生前殺豬,死后承擔業報,故被帶至冥府接受閻羅王審判并送入豬胎。佛經有因果報應之說:業報有三報,一是現報,二是生報,三是后報。此三報指“靈魂從消滅了的軀體中不斷地轉移到另一個新的軀體中”。黃仕強殺豬,故靈魂被禁錮在動物體內。
最后是審判中的糾錯過程。糾錯依托“文案”。文案中壽命先定與道經一致:“未生豫著其人歲月日時在長壽之曹”。而在佛教中無先定之說。《黃仕強傳》借鑒了道教命籍文書的觀念。《太平經》:“黑文者死,青錄者生。生死名簿,在天明堂。”道教中青黑簿籍為善者增記,為惡者減壽。佛教認為壽命由己修,沒有生死簿的概念。玄奘法師所譯佛經中有“名籍之記”:“彼琰魔王主領世間名籍之記”。此處“名籍之記”指通過名籍化抽象為具象,說明因緣果報和輪回問題。《黃仕強傳》中的生死簿是入冥者承受因緣果報的依據。將因果輪回、善惡報應的佛教觀念與道教的生死簿結合,體現了佛道思想之交融。曹司需為誤入冥界的黃仕強澄冤。《黃仕強傳》中的“曹司”與我國道教信仰有關,“文案”與命籍文書相當。地府中的“曹司”來自人間官職。曹司本義官署:“至一城郭,引入見一官人,似曹官之輩。”文中的“曹司”掌管生死簿籍,是道教文化不斷發展的結果。
二、佛教與儒家思想的融合
《黃仕強傳》附于《證明經》前,其思想觀念與《證明經》相關。《證明經》由中原人創作,故而會體現我國思想文化,其中有佛教與儒家思想之交融。
佛儒二者對從政者的要求殊途同歸。佛教主張為政之人要服務于民眾的利益,《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于諸國邑所有眾生,僮仆作使、輔臣僚佐,應以諸佛所說四攝而攝受之。何等為四?一者布施,二者愛語,三者利行,四者同事。”儒家主張以民為本,如《論語》:“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證明經》亦體現了該思想:“九者若有眾生高遷富貴輔國大臣。假官力勢斷事不平。以直則曲破小作大。枉殺良善便取萬民。如是之人等亦不得見彌勒。”另外,此處說明作惡者要承擔惡報,不得見彌勒,符合佛教因果報應。由此,佛儒在理念上有相通性。
《證明經》借鑒儒家經典中的句子,體現仁愛思想。《證明經》:“四海知識一如親兄弟。”佛儒在對待苦與樂的態度上也有相似處。佛教提倡不畏苦,不求樂。《優婆塞戒經》:“受苦不憂,受樂不喜”。孔子告誡世人善處困境。《論語·述而》:“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佛教中菩薩直面苦難,為眾生受苦時“不舍不避、不驚不怖、不退不怯,無有疲厭。”不僅如此,正如上文所述,《黃仕強傳》中黃仕強告知守文案人想見已故的母親,亦是儒家孝道的體現,佛教主題與儒家思想的結合,體現了二者在文本中的交融。由此可知,無論是《黃仕強傳》與《證明經》中,佛儒交流都有著鮮明的體現。
《黃仕強傳》為宣傳《證明經》而作,故事廣為傳抄,具有重要的宣教意義。《黃仕強傳》創作的時代,各種思想在中土碰撞,因此在文本內容上體現了佛教思想、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以及民間信仰。《黃仕強傳》附在《證明經》上,這種宣教形式體現了佛教中國化。《黃仕強傳》的創作與《證明經》有關,所以《黃仕強傳》可能受到《證明經》的影響。《證明經》將佛經進行了中國式創造,佛儒與佛道思想的融合,經文滲透中土民間信仰,均體現了多元文化交流。
作者簡介:
季佳陽,女,天津人,塔里木大學人文學院學生,研究方向為敦煌文學研究;齊嘉銳,男,河南葉縣人,塔里木大學科研處,文學學士,研究方向為敦煌文學研究;屈玉麗,通訊作者,女,山東泰安人,塔里木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碩導,研究方向為敦煌文學研究。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敦煌寫本所見東西方文學交流研究”(19CZW031)、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塔里木大學漢語言專業、教育部“文化與邊疆課程思政虛擬教研室”、兵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建設項目“胡楊精神視域下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漢語言專業課程育人體系構建研究”(課程育人)、兵團級一流本科課程——中國古代文學、兵團級課程思政示范課程——中國古代文學、塔里木大學一流本科課程——中國古代文學(TDYLKC202217)、塔里木大學課程思政教學研究中心專項“三全育人視域下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漢語言專業課程思政育人體系研究”(TDGJSZ2204)、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曹氏歸義軍時期于闐與敦煌的文學文化交流研究”(202310757052)、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敦煌本佛教靈驗記所見佛教中國化研究”(20231075705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