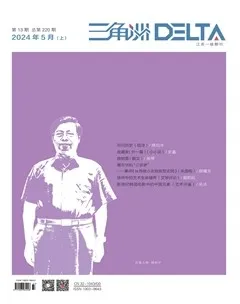社會認同與自由個性之間沖突的解決
朱容瑾
社會與個人的關系問題是從古到今都一直被重視的問題之一。特別是當代,社會高度分化,人們對自由自主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社會對人的規范與監控也在不斷加強,人的自由個性被不斷地壓制,社會認同與自由個性之間的矛盾愈發激烈。針對這個問題,《論語》中或許蘊含了一些有關解決此問題的智慧。
對于個人與社會所存在的兩種關系,一個是社會本位主義,另一個是個人本位主義。顧名思義,社會本位主義是采用整體的辦法,以“社會”這個整體為出發點,并在這個層面上研究解釋社會現象。這種觀點認為個人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但社會并不是個人的簡單集合,因此在研究時把自由意志、個人動機等這些主觀因素的哲學概念排除,并且只有當個人的研究對整體社會的研究具有意義時才加以重新考慮,而這其實在一定意義上導致了“主體”的消亡。
與社會本位主義截然相反,個人本位主義是用個體主義的方法原則對個體進行研究。個體主義的研究方法認為社會由個人組成,而個人與個體之間是有差別的,個體間的差異性和個體的不同行動才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這樣,社會的發展過程就被還原為對個體間交往活動的解釋和理解,從而導致了“社會”這個整體的消解。從社會本位主義和個人本位主義兩種研究視角的區別不難看出,前者強調的是社會的整體性、規范性和約束性,認為個人應服從集體、服務于社會;個人本位主義強調個體的自主性并關注個人權益。這兩種研究的視角正好對應著個人與社會之間會產生的兩種問題,一種是社會壓迫個體的個性發展,另一種是自由個性的過度發展使得社會出現異常。但是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第一種問題發生的情況占據大多數,歷史上許多看似個性自由的時期,實際上也都是由于社會過于壓迫人性所導致的異常結果。
魏晉南北朝,是非常典型的個性自由和社會認同矛盾最為激烈的時期。劉伶縱酒脫衣裸形在屋中,面對人們的譏諷,說出“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入我裈中?”的不羈灑脫;郗太尉選婿,王羲之卻“坦腹臥,如不聞”坦然淡定。這些都表現出了魏晉名士追求任性的自由生活,但這種看似放蕩不羈的自由背后,其實隱藏著當時社會的過度混亂和壓迫,迫使名士們都選擇了叛逆與反抗。循規蹈矩和道貌岸然在不知不覺中消失,飲酒、服藥、著文,一切都開始變得隨意灑脫,自由隨性。從表面上看,這是人自由個性的彰顯,但是實際上,這是一種被束縛的、無奈的自由,是被社會認同所擠壓的。因為魏晉名士的自由實際上都是限制在統治階級規定的范圍內,不問政、不發表政治意見,只是在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最大范圍地享受自由,但是這樣對于才華橫溢、渴望改變惡劣的政治局勢的人來說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同時,這種激烈的矛盾(包括階級矛盾和個人與社會的矛盾)也為中國哲學的發展帶來了寶貴的機會,其中就包括魏晉玄學。玄學是魏晉時期思想文化的標志性成果,玄學家主張是清談或玄談。顧名思義,其特征并不難想見:遠離政治,回避現實,無關道德,蔑視俗務,只關心高深玄遠的理論問題,向往超凡脫俗的高雅生活。
在前幾年,有一個非常流行的人設“積極廢人”,這個人設指的是心態積極向上,行動卻遲遲跟不上的人,他們往往會在間歇享樂后恐慌,時常為自己的懶惰自責。其實這個詞語是帶著自嘲的成分,人們已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弱點,不需要外界指責,索性將之拿出來調侃一下。有人說這其實就是惰性作祟,但是這么簡單地下定論未免有些草率。在此其中其實包含著社會集體心態。“積極廢人”中不僅僅有“廢人”,更重要的其實是“積極”。在傳統的語境中,積極是一個具有正面色彩的詞語,但是在這個詞語中,“積極”正是問題的根源,因為這種“積極”其實是社會與個人之間的矛盾——個人被社會所裹挾而產生的后果。
結合當下的社會情況來看,現代新思想的滲透和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對個體的影響很大,而自媒體的不斷興起更擴大了個性自由所蘊含的領域和范圍。在當代的背景下,個體是行動的主體,有自己的思想、能動性和實踐能力,并有著強烈的依靠自己塑造、創建社會與歷史的愿望。用宗教的語言來說,“每個人都有一個神圣不可侵犯的靈魂”。個體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人們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職業等,也有強烈的自我責任感和義務感,人們認為自己有能力為自己的行為和選擇負責,并且也倡導人的全面發展和解放。
但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這種新的變化也促使人們對財富無止境地追求,導致個人主義、私利主義成風;另外,人們的信仰、信念、穿著風格也具有了多樣化的特征,甚至有些特征完全與傳統背道而馳;不僅如此,個體的行為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許多以往決不允許的行為在當代被貼上“個性化”的標簽以后,反而成為人們都競相追捧的時髦,而個體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突出自我、放大自我,從而引起人們的注意。
所以,個體的風格化、多樣化成為當代的特征,同時對自由、對人的全面解放的追求以及對自主權益的追求也逐漸成為個體的共同呼喚。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現代性的擴展,社會結構不斷細化,社會作為一種外在于人的機構,也有了多樣化的控制機構和整合機構,能對生存于其中的組織、機構、群體,尤其是個人進行法律的、道德的控制,迫使桀驁不馴的人回歸既定的軌道。
作為人的個體就仿佛處于一組同心圓的圓心,每個圈代表一種社會控制體系。最外圈就代表的是政治和法律體制,人們不得不生活在這個體制之下,不能為所欲為。這個體制要求人們遵守法律、依法納稅、不能燒殺搶掠等數不清的條例,并且這種約束、制約不斷地進行擴張、滲透,它的威力已經侵入人們生活中可以想象的各個方面,稍有不慎就會受到懲罰。而在比較極端的情況下,最古老的社會控制手段——暴力也會發揮它的威力,如:執行死刑、對犯罪分子的武裝打擊等。即使在當代民主且有序運行的社會中,終極的制裁手段也是暴力,如果沒有警察或與之相對應的武裝力量,任何國家都不會生存。當然,終極的暴力并不會被頻繁地使用,其實在社會中,暴力的使用都有一定的節制,而且被當作最后的使用手段,因為僅僅依靠暴力的威懾作用就足以對社會進行有效的控制。
向同心圓的圓心即那個孤零零的個體施加壓力的進一步的社會控制是道德、風俗、禮節。雖然這種控制沒有法律的控制那么直接和強硬,但違反了社會的道德與風俗習慣所帶來的無形壓力絕不亞于法律,表面上看被人冷落、受人指手畫腳像是小小的懲罰,但對作為當事人的個體而言這樣的懲罰并不輕,因為他或她有可能一生都被打上恥辱的烙印。由以上可見,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的控制體系是十分嚴密的。
以上這兩種壓力是人人都要承受的相同的控制體系,此外,個人還要受制于其他一些較小的圈子。其中職業對個人的控制也有重要影響,因為一個人的工作決定他大半生都會從事什么事情,會屬于什么性質的群體,有什么樣的同事和朋友。并且在當代社會,許多企業都有其企業文化,因此自己必須保持、體現與其一致的行為方式。同時,職業部門的規章制度、領導的要求都會對個人進行經濟上的制約或控制,稍有不慎就會帶來經濟上的災難,而經濟控制給人們帶來的威懾力同樣有效。
到最后,個體仍然會受許許多多零零碎碎的社會控制,如所參與的非正式群體即:俱樂部、社團、協會等,雖然這種性質的組織門檻低、控制力小,但處理不當仍然會感到不舒服。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想象處于同心圓的圓心位置的個人要受到層層社會規范、法律、風俗等各種約束和控制,幾乎全世界都壓在自己的頭上。這正如一座“全景式監獄”,“監獄中央設有哨望塔,衛兵可對囚犯一覽無遺,社會中的軍隊、工廠、學校、醫院等現代機構等與監獄如出一轍,彼此借鑒,技術共享,只是他們對人的規訓由暴力壓迫轉向心靈馴服,讓人們時刻感到有雙權力的眼睛在監控著自己。”這樣,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它的秩序性、規范性、協調性就必然要對個人的行為加以控制和要求,這就形成了個人的自由與社會的秩序性的對峙。
在實際的生活中,個人與社會是互相依賴的,但面對社會無時無刻對人的控制和監控,個體有更聰明的辦法繞開或顛覆最精巧的社會控制系統,這樣的技巧可以矯正社會壓抑,使人精神為之一振。由于社會給個人提供了一個龐大的機制,使個人看不到自由,因此破解個人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反對社會的控制、張揚個體的個性實現個體的自由成為當代個體迫不及待的需求。最接近自由的表述就是僅僅在某些情況下某種程度上擺脫社會控制的自由。但社會控制已經滲透在社會的每個角落及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這種事實面前,人們并不是無能為力的,而是可以通過一定的技巧達到一定境界從而實現一定的自由。
可見,在當代,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張力在不斷拉大,二者間的關系非常緊張。那么我們作為個人,面對這種矛盾,應該如何應對以保全自我呢?
西方社會學理論中將社會與個人之間絕對對立起來的基本根源在于日常意識和西方社會學思想中一貫具有的那種濃厚的世俗現世觀點,在于這種世俗現世觀點中所包含的那種對人的情欲作為一切行動主導源的肯定,以及由此導出的對情欲滿足和“有”的種種形式,如:擁有、占有、具有、享有等的執著。在這種世俗性占有滿足觀的指引下,“人”必然地要被視為一種不斷地向外延伸、不斷地通過外在于個人且又高于個人的社會來證明或滿足自己的存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以及個人自主性的削弱就不能不是“人”的一種“命運”,要想徹底走出西方傳統社會理論在社會與個人關系問題上所遭遇的困境就必須徹底撤出、拋棄這種執著于“情欲”和“有”的世俗現世觀點,代之以一種新的人生觀。
那么,這種所謂新的人生觀是什么呢?那就是《論語·學而篇》中孔子所教導的“不患人不己知”。“不患人不己知,患不知人矣”這句話意思是,不擔心別人不知道自己,只擔心自己不了解別人。這句話可以與《論語》前文孔子所說過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放在一起來看。在我看來,“不患人不己知”是在教導我們解決個人與社會之間矛盾的策略,那就是“修養自身”,一個人能夠“不患人不己知”,源于其自身的完善帶來的自信,并且需要在突出“個性自由”的同時做到“無求、無功”,達到“人不知而不慍”的君子境界;“患不知人矣”則是提醒我們始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看清社會的本質,深化“修養”的深度,擴張“修養”的廣度,以從容面對社會和個體之間的矛盾,在達成自己目標的同時,做到不被社會所裹挾,形成不盲從于社會主流的心態。
那么,“無求、無功”中的“無”有什么含義,與生活中的“無”有怎樣的區別?在這里,“無”并不是數量上的絕對空無狀態,而是相對于“有”的狀態,是舍棄后的一種狀態,并且是盡量地丟棄,丟棄常人的一些欲望,甚至達到“無己、無功、無名”的逍遙境界。只有達到這種境界,個人與外部社會之間的對立自然也就消解了。但并不是人生而都可以達到“無”的境界,因為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靠“修養”。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都很難做到“無”的境界,原因是對于“有”的放棄,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而這種情況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們不能夠使自己從社會的聯系中解脫出來,底層原因是人害怕孤獨,因而往往屈服于主流的社會意念。可事實上,人唯有讓自己處于孤獨狀態,處于自我超越的心境之下,才有可能把社會擱置起來。而“修養”正是對達到這樣一種孤獨狀態的修煉過程,通過修養,人們便能夠有所體會和覺悟,形成一種凡事不強求隨緣應對、順勢而動的生活態度或生命境界。一旦達到這樣的境界,一切由社會和個人的對立所造成的困境就迎刃而解了。
(作者單位:西藏民族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