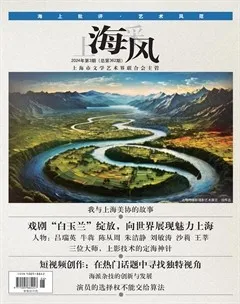園林建筑學家的藝術觀
周正平



已故同濟大學園林學家陳從周教授,趣事頗多。首先,要說一下他名字的來源,《論語》:“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可見,他原名郁文,字從周,后以字行;早年畢業于之江大學,長得瘦,個子不高大,知識面廣博,說話風趣,也有點刻薄;紹興人,其祖、父輩曾為商販,家風好讀書。據陳先生自述,他喜歡讀雜書,好在有計劃地閱讀,除了園林建筑本行業外,陳先生還有許多興趣,以下我略述幾方面。
陳從周的畫
從周先生擅畫,這是文藝界和熟識他的人共知的。有一次閑談,筆者偶爾問起他怎么會作畫的,他告訴我說,在畫畫方面有兩個老師:第一個是杭州“兩浙鹽務中學”的胡也衲先生,兼通中西畫法,擅北碑書,并成立活動小組,對學生中有書畫特長的人特別關照,1920年代,葉淺予
等人受他啟蒙,記得有一期《朵云》期刊曾登載此事。
第二個就是赫赫有名的張大千先生了。從周先生說:認識張大千是篆刻家方介堪介紹的。當時,張大千見到陳從周一幅臨摹石溪的畫,很贊賞,就收他為入室弟子,那張畫后來送給了方去疾先生。但我又據從周先生的老朋友、復旦大學老校友姚心牧先生回憶說:“張大千見到他的畫,認為很有才氣,是自己主動收他為弟子的。”
從周先生還補充說:“取名字要通俗易懂,比如張大千,別人一聽就記住了。”
青年時代,陳從周一心想成為畫家,還在上海開過個人畫展呢!張大千題為“門人陳從周畫展”。那時,他的畫與張大千的很相像,有近似工筆的仕女、山水之類……
我知道陳先生晚年的畫風卻具有另一種趣味和追求:他最喜歡畫竹子和蘭花,而且是墨筆的,很單純,往往疏疏幾筆,表現出俊逸、雅潔的感覺,這正是他的長處,是典型的具有中國士大夫文人內心綜合氣質的畫,當然有所寓意、有所寄托、有所抒發內心的思想情感。盡管他自嘲僅僅是園林建筑學家的畫,但他
的簡筆畫是很令人欽佩的,且不會與他人混淆,無須狂怪,淡淡的,也是一種風格。
關于畫藝,特別是對于畫蘭竹,他的體會是:“畫竹時主枝干要立得住,用筆要挺勁,在這基礎上,添加葉子。” “畫晴竹用墨由深而淡,畫雨竹由淡而深,水分不一,效果不同。”
又謂:“張大千說畫蘭花淡葉子最難了。”但我看陳先生畫蘭花也是葉深花淡。
從周先生畫中的湖石,用筆造型圓渾、淳樸,與古園林建筑真是絕妙相配。
除此,他的寫意墨荷、葫蘆、蕉蔭小鳥、水仙、梅花等畫也很有韻味,只是興趣愛好廣泛,不愿多表現那種費時費勁的畫。
關于好畫的標準,從周先生評說:“畫要看得進去,耐看,讓人有玩味留戀的感覺,就是一張好畫。”又說:“香港、臺灣等地的人,以他們的審美觀左右畫家;作畫如果為了討好別人,畫面格調不會清逸。”
每個有成就的畫家都有尋找自己契入點的思索與苦惱。從周先生堅持自己的趣味和主張。有時畫完一張水墨畫,他會突發高論:“畫,讓每個人都喜歡是沒有必要的,果真那樣,是姨子畫的,也很難做到。”可謂語出驚人。
面對別人稱贊他的畫,陳從周先生有時解嘲說:“別人要我的是園林建筑學家的畫。”又引京昆劇名演員梁谷音的話:“梁谷音說:謝伯伯(謝稚柳)畫是下海,陳伯伯(指自己)畫是票友。”停了一下,又自負地說:“票友也有好的,比如俞振飛過去就曾經是票友(俞振飛先生當時為京昆劇的最高權威)。”諸如此類的話還有:“紅極一時未必流芳百世,流芳百世未必紅極一時。”看來他內心是很自重的。
對于畫壇風氣,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某次,家里來了不少客人,閑談中,陳先生又說道:“許多人的畫是鈔票,我的畫是草紙(上海話:鈔、草諧音,聽起來很有意思。)但大便急了,鈔票不能擦,草紙可以擦擦。”講得一本正經的,在座的人無不
笑倒。
喻蘅先生對我說:“陳從周喜歡小青年,他畫畫,愛贈送后生。理由是:年輕人會很崇敬地珍藏著,同輩人隨手棄置,不重視的。”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我至今精心裝裱并收藏著這些字畫。
當代“紹興師爺”的個性
陳先生性格中有遺老味,許多人是知曉的:比如住房要底樓,可種植花草,為“得地氣”;早點中大餅最好吃,而且要吃咸的大餅……
王蘧常先生是陳從周岳父蔣謹旃的表弟,也是他的老師。按陳從周《隨宜集》中自述:“自大學時代起,就一直沒有中斷過師生情誼。”記得1988年6月,王蘧常先生九十壽誕,顧廷龍、蘇淵雷、鄭逸梅、蔡尚思、周谷城等發起,滬上文壇名流云集,真是好熱鬧,陳從周當眾拜倒磕頭;過后,其內侄蔣雨田與我往訪,閑談中問:“果有此事? ”陳先生提高嗓門答道:“真的,那還有假?”我們都很吃驚,躲在一旁偷偷地笑。
從周先生還參加過修繕松江古代園林的工作,據友人林曉明兄親眼所見、親口告知:1988年,廣富林地區明代陳子龍墓修繕竣工儀式上,陳從周當場跪倒,口稱:“給五百年前的老祖宗磕頭。”當時,在眾人眼里,
這是很驚人的壯舉。
從周先生有很雅致的集聯,如:“人間詞話花間集,月滿樓臺景滿園。”上一句集兩本古詩詞的書名,下一句描寫園林建筑美景,這是我很喜愛的。
有為杭州絲綢廠的集聯:“天增歲月人增壽,云想衣裳花想容。”把大好時代,美艷衣飾的含義都表達出來了。
還比如勸人做事要堂堂正正的集聯有:“仰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但從周先生偶爾會挖苦別人,黃仲則有詩句對聯:“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已是憤世嫉俗了,他改為:“十有九輸天下事,百無一可眼前人。”真是進一步發展。
有時引舊聯:“辛苦與人談時事,不妨聽我吹牛皮。”引得眾人都笑。
陳從周先生有時談起話來,既刻薄又滑稽,使人窘迫后又忍俊不禁,帶著紹興師爺的遺風。
曾說:“文采好的女人往往不夠漂亮,比如臺灣作家三毛……”
對時下人的頭銜越來越多,他嘲弄道:“名片就是明騙,片子就是騙子……”
又一次,其內侄蔣雨田持扇面請他為友人作畫。陳先生寫竹一枝,稍稍停頓,在扇的右側題句:“板橋畫竹愛罵人,余也愛罵人。”我們看了都不住地發笑,他白了一眼,在左側又題:
“從今往后不罵人。”大家越發笑了,確實寫得有趣,但他日后始終未能改掉罵人的習慣。
陳從周與戲劇
陳從周先生熱衷于京、昆戲劇。
有一次,我請求說想跟他
學習古典園林建筑方面的知識,他睨了我一眼說:“沒那么簡單的。”看來,他清楚我的短處與長處。他知道我對于書畫、詩詞有所知曉,進一步啟發說:“欣賞京、昆戲劇藝術,演員的身段、手姿、唱腔,對你會有幫助的。”
有幾次,他邀請上海昆劇團的演員來同濟大學演出,并拉我同去聽戲。俞振飛年邁,只在臺上略站片刻就退場了,真正演出唱戲的是華文漪、梁谷音、岳美緹等人。某晚,我與陳先生的內侄蔣雨田同坐在觀眾席,印象中最深的是一出潘金蓮還魂纏西門慶的鬼戲,女旦角由梁谷音飾演。
京、昆劇界這么多演員中,陳從周最捧場的是梁谷音的唱腔,近乎迷戀。就我所知:他將自己早年留下來最好的畫多給了
梁谷音,還勸她在報端寫短小的文章。他修繕上海豫園大假山和長廊,完工后,將其中的一段命名為“谷音澗”。當時,從周先生曾抄錄給我一首《聽梁谷音昆曲于豫園》的詩,讀來很有雅韻:“名園何處不宜人,脈脈山泉出谷音。花下忘歸猶點筆,曲終似水鬢邊清。”從周先生日后畫磐石蘭竹,常以此為題材,他給我畫的一幅“谷音澗來風自香”的橫長水墨畫卷,是我最為喜愛的。
許多名人好客,這話對陳從周先生來說確實是不假的。雙休日時,他的家里往往像茶館似的,高朋滿座,又每每聽其高談闊論。末了,陳先生經常要親自將客人送到門口。有一次,我詫異地問其何以如此,他告訴我說:“過去,梅蘭芳送客要到看不見人的身影才回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