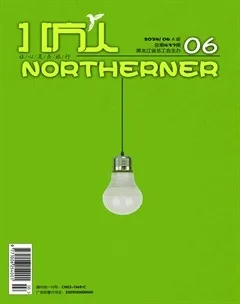新生
三爵

一
在節奏如馳的醫院,一舟是個不入群的女孩。單薄的她,穿著同樣單薄的T恤和牛仔褲,綁一根麻花辮,發絲被? 白的日光燈氳出毛茸茸的邊沿。她安靜地坐在血液內科候診區最后排的角落里,蜷著腿,手里捧著一本卡通記事本,不說話。
那天,我帶著一份緊急會診邀請,從另一個院區的病房趕來,請血液內科的醫生協助評估病情。我看到一舟的胳膊,臂彎處鑿滿針眼。我瞥見她有些蒼白的臉和嘴唇。她十六歲。我的第一個念頭是白血病——好發于少年兒童的血液系統惡性腫瘤。
門診醫生調取了一舟的病歷。意外的是,并沒有白血病的征兆。血常規的結果也只有一處異常:中性粒細胞百分比及絕對值減低。“是惡性疾病嗎?”我問。
她搖了搖頭:“不像。”
我們繼續查閱了一舟的其他檢查結果。我驚訝地發現,在短短半年里,她竟然先后做過二十余種檢查,且有些項目做過不止一次。
一舟的手指在發抖,嘴角微微抽搐。她的母親站在旁邊,幾次欲言又止。確認其他的檢查都沒有異常,我剛要解釋,一舟忽然哭了。
“我要做穿刺,”她抽噎著說,“我一定是白血病,請您給我開檢查。”
“沒有證據指向白血病,”接診醫生皺起眉頭,“大概率是感染。”
“我必須做穿刺,”一舟拼命地搖頭,“給我開檢查,我不怕痛。”
“聽醫生的話。”她的母親說。
一舟縮在凳子上,渾身顫栗。她張開嘴,開始大口呼吸,好像喘不過氣似的。
我把一舟的母親喊出診室。關上門的剎那,她也哭了,略顯佝僂的脊背靠在門框,雙手捂住臉頰。我認真地打量著她——面前是個約莫四十歲的女人,矮胖,綰發,發膠在燈下折出不協調的高光,穿一件發皺起球且不合節令的大衣,手背上青筋遍布。
“孩子有沒有哪里不舒服?”我問。
“哪里都不舒服。”她苦笑著說。
“具體是什么表現?”我繼續追問。
“有時肚子疼,有時腿沒力氣。”她說,“還有心慌。”
“病毒感染也會導致這個指標減低,但過幾天就會恢復。”我繼續解釋道,“最近換季變溫,學校人流量大,容易發生感冒流行。”
她揉了揉眼,什么也沒說,只是靜靜地聽著。
半晌,她再次深呼吸,鼓足勇氣,嗓音喑啞。
“去年秋天,孩子就休學了。”
二
我用工作微信添加了一舟的母親為好友。
她的頭像是一只航行在海面上的帆船,昵稱叫作“山川”。
我再次看見一舟的時候,是在精神科病房。她仍然不入群。我接管病床的時候,她獨自蜷坐在床上,披散著長發,懷抱那本卡通記事本,安靜地望著墻上的一幅水彩畫。
也許還在生氣,一舟并不愿意和我說話。一舟的入院初診是焦慮癥。
接續的幾天,一舟都不和我說話,也不和其他同齡人交流。她情緒很淡,唯獨會在提及檢查結果的時候表現出些許興致,卻在被告知一切正常后,短暫的興致又消失了。
“她好像很希望查出重病。”主治醫生說。
辦公室外響起叩門聲。我去開門,看見一舟站在外面,她怯生生地看著我,手指攥緊衣角,身體明顯地顫抖。
“怎么了?”我問。
“我想做心臟造影。”她說。聲音細若蚊鳴。
“我心慌,”她接著說,“去年就開始心慌,心跳得快。我吃過降血壓藥、控心率藥、營養神經藥,都不好。我一定得了不治之癥。我聽說,吃藥治不好的,大概率是絕癥……”
“但我們沒有找到病灶。”我說。
“我不信!”一舟著急道,“一定是有儀器漏掉的毛病,或者是醫生漏診。”
“這樣吧,”主治醫生說,“我給你預約明天的心臟彩超。這項檢查不用打針,并且比造影安全,并且也能計算你說的那些指標,如果有結構性異常,很少漏診。怎么樣?”
“很少,是多少?”一舟問。
三
一舟的診斷改成了疾病焦慮障礙。這個病,也被稱作“疑病癥”。
翌日查房結束,我給一舟的母親打電話。電話那頭,我聽見擴音器叫賣的聲音。我把一舟的診斷告訴了她。我說,今天上午,孩子一直在寫作業,寫得很認真,字跡工整。她在電話那頭沉默良久。
一舟整個上午都在寫作業。期間,我去病房和她講檢查的注意事項,借機指著她放在床頭的記事本,半開玩笑地說:“這里面藏了什么秘密呀,可以給我看看嗎?”
一舟對我的態度好轉了不少。她靦腆地笑了笑,翻開記事本,遞給我。扉頁里寫著一句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字跡和她寫的作業一樣工整。九月十三日——她寫道——高二上冊數學第一單元課后題、英語作文一篇、英語閱讀理解五篇、古詩詞理解兩篇。在“英語作文一篇”后面,用紅筆打了一個小小的對勾。
我饒有興致地拿出手機,拍了一張照片。“讀高二?”
一舟紅著臉說:“我去年就沒上學了。”
“可是你的功課并沒有落下。”我說。
“我在自學,”一舟說,“每次學校考試,我也會做模擬試卷。”
說著,她找出書包,把一沓做完的試卷找出來。試卷中間,夾著一本漫畫雜志。雜志落在床上,一舟觸電似的哆嗦了一下。
“喜歡看漫畫?”我笑著問。
她用力點了點頭:“嗯。”
“我也喜歡。”我說,“我還喜歡畫畫。”
“我也喜歡!”一舟眼睛一亮,“我以前拿過很多獎。”
“是嗎?那太好了!”我指著墻上那幅雛菊,“我們這兒有好多小藝術家。過兩天,我給你找來畫筆和顏料,你畫一幅,我們裝裱起來,掛在別的病房。”
就在這時,一舟的母親忽然推門而入,走到床邊掃視一番,拎起那本漫畫雜志,“嚓嚓”兩下,當場撕碎。她把碎紙甩進垃圾桶,轉身指著一舟,紅著臉大聲吼道:“不爭氣的丫頭!爹媽拼了命賺錢供你讀書,你呢?看閑書,現在學也不上了,你對得起誰?”
吼完,她“砰”地一下摔門走了。一舟訥訥地坐著,眼神凝滯,身體抖得更厲害。我下意識地掩上了病房的門。門鎖卡牢的剎那,一舟沙啞地咳嗽了一聲,開始小聲啜泣。
后來,我得知,她家境并不富裕。母親在附近開雜貨鋪,父親是煤礦工人,夫妻常年兩地分居。除去學雜費,薪水勉強供給吃穿用度。零幾年的時候,曾一度申請低保。一舟是家里的獨女。她對繪畫很有天賦。學習水彩不到一年,就在比賽中獲得了全國一等獎。她學習也好。去年六月,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取重點高中,卻在入學一個月后,再也無法堅持學業。
“初二以后,我就沒再畫畫了。”一舟說。
“能不能告訴我,那時發生了什么?”我問。
一舟緘默了片刻,旋即小聲說道:“初二下學期的期中考試,我的成績下降了兩分。媽媽在我面前燒掉了我的畫材,她不允許我學藝術。”一舟輕輕地說,“她還故意燒傷了自己的手。她說,這是她對自己的懲罰。她要讓我看著她懲罰自己,這樣我就會明白她的苦衷。”
她講述自己的往事,語氣寡淡得像一杯白水。
我聽完,胸口像蒙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翳。
“媽媽說,她這樣做,是因為她很愛我。”
四
“她很愛我。”
這句話,在我心頭埋進了一根刺。
我想給一舟安排心理咨詢。但接續的幾天,我都沒見到她的母親。
一舟沒再和我提起畫畫。僅有的幾次交談,都在我工作暫歇的片刻。她怯怯地走進辦公室,向我咨詢檢查結果。在我反復告訴她一切正常后,她仍會糾結于報告單上微不足道的增減,并且要求繼續檢查。藥物已經用到單日最大劑量,但短期內收效甚微。
常規治療幾日后,一舟的情緒開始起伏不定,常常低落、哭泣,夜晚被噩夢驚醒。某天早查房后,我向一舟交代用藥注意事項,無意間看見了她手臂上新添的傷痕。
我意識到,我必須為她做點什么。
回到辦公室,我撥通了一舟母親的電話號碼。短暫的靜默后,背景仍然嘈雜。她接通了,但聲音急躁,大概正忙。
“治不好,對吧?”
“沒那么嚴重。”
我隱約聽見她沉重的呼吸。
片刻,她自語似地喃喃:“我毀了我的孩子。”
傍晚六點,她回到了病房,仍是如前的裝束,面容疲憊,風塵襲身。
“我們家就這一個孩子。”話音剛落,她嗓音一哽,兩行淚滾落桌沿。“去年,她爸在礦場摔斷了腿,算作工傷,老板賠了三萬塊。但是因為腎病、肝病,腿腳沒好利索。他讀完初中就沒再念書,我呢,小學都沒畢業。我倆都明白,現在臟點、累點不算什么,有文化最重要。盼著,盼著,盼著孩子以后能考大學、出人頭地,別再吃我倆吃過的苦……”
“其實孩子很用功。”我說,“好幾次查房,都看見她在寫作業。她的課程從來沒有落下,甚至還在超前學習。”
她眼眶更紅:“要是能上學就好了。”
“聽她講,她從前成績非常好。”我接著說。
“經常馬虎丟分,”她說,“簡單的計算都做不對。”
“可這都是很小的錯誤,很容易改正。”我說。
“說得容易!”她說,“以小見大,積少成多。”
我嘆了口氣。“她很聽話,并沒有忤逆你的要求,”我說,“但是你可曾想到,太過自律的孩子,往往會把自己逼向另一種極端。她習慣了對自己嚴苛,又把這種嚴苛泛化到其他方面,比如疾病。錯誤的認知使她無法獲得滿足感,也無法理解‘完美的真正含義。”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她打斷我,“這是優點,不對嗎?”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并不是優點。心慌是焦慮的軀體反應。而她對于嚴重疾病的懷疑,其根源正是過度的完美主義。”我調出一舟最新的血檢報告,說:“中性粒細胞恢復到51%,證明上次的異常的確只是病毒感染所致,不用考慮白血病,更無需骨穿。”
她看著報告,張了張嘴,卻沒出聲。
“也許你認為這是愛,你在為她的將來著想。但對她而言,這種窒息的愛其實是難以承受的。”我說,“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更好?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你用傷害自己作為要挾,強迫她追求那個無法描摹的‘更好,反而會促長她的怯懦、自卑,直至積聚成疾。”
她用力揉了揉眼睛。
“其實很簡單。人只有不斷地試錯才能有所收獲,這并不意味著馬虎或者失敗。我們做家長的,應該允許孩子犯錯,并且她也要學會允許自己犯錯。”
我接著說:“解開束縛,還給她成長的自由。”
終
周末,一舟出院了。
我回歸于忙碌的臨床工作,漸漸淡忘了一舟的故事。直到三個月后,我從運河老街游玩返回,這段往事方才煥新。那趟旅行中,我在一個岔口見到了一舟母親經營的雜貨鋪——它的名字叫作“山川”,是一間鑿在住宅底層的半地下室,無窗。五六平米的水泥地上雜貨擁躉,外面門可羅雀。
彼時,我正在護士站等待年度考核,背書背得有些昏昏欲睡。毫無征兆地,一舟出現在病區門口,笑盈盈地向我招手。腦后的麻花辮上,別著一只鵝黃色蝴蝶結發卡。
“我已經去上學了。”她說。眼眸撲閃,臉微微紅著,酒窩臥在嘴角。她遞給我一張白底紅字的信封,里面裝著一張書簽、一枚葉脈標本和一張寫滿的明信片。明信片背面是她畫的水彩—— 一朵金色的雛菊。
我將書簽和葉脈標本夾進隨身攜帶的指南手冊。那張畫著雛菊的明信片,被我壓在桌板下面,和我珍藏的票根和其他的記憶掠影并排。一個月、半年、一年。五年、十年。它會永遠留在此時此刻,見證著另一種意義上的新生。
(摘自2024年第3期《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