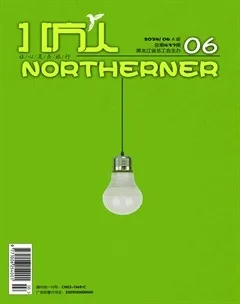大地的哲學課
傅菲
蜣螂
去水庫的路上,看見一只蜣螂在推羊糞球。羊糞球比蜣螂兩個身體還大。我蹲下來,看它推。路是水泥路,路面平整。它用前肢推,像農夫推獨輪車上重重的糧食。
路面有一個碗狀的坑洞,是打樁人留下的。蜣螂推著推著,羊糞球滾落坑洞。蜣螂爬下坑洞,繼續推。羊糞球落在兩個小石塊之間,推不起來。蜣螂換了個姿勢,用后肢往后蹬,以倒退的方式推。羊糞球緩緩往坑坡上滾。在接近路面處,羊糞球卡在水泥角上,蜣螂不斷地蹬,羊糞球松動了,卻滾了下來,壓著它一起滾下坑洞。
蜣螂繼續推,然而又失敗了。
再而三,三而四,蜣螂不妥協。我想起希臘西西弗斯神話。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巨石上了山頂,因重力又滾下山底。西西弗斯周而復始,永無止境地推著巨石。
蜣螂推了八趟,耗時九十三分鐘,最終把羊糞球推上了路面。我被它悲壯的努力深深震撼。
冬蜂
冬日,我去山塢看人割棕衣。割棕人站在木梯上,一手抱著棕樹,一手用彎刀割棕衣。我問割棕人:“割這么多棕衣做棕墊還是撬蓑衣?”
“給蜂箱壓箱頂。風太大了,蜂會凍死。”割棕人說。
山口有一塊空地,擺了二十余箱蜂。我昨天上午去看過,蜂箱口的邊沿躺了很多死蜂,腹部朝天。我想,這些蜂采蜜回來,來不及進蜂巢,便死在了家門口。如大雪之日返鄉的人,跋涉了千山萬水,到了村前月下溪橋,卻再也走不動了,撲倒在橋上,望著舊年的大門。
蜂場是生命最歡騰的地方,蜂舞如瀑瀉,振翅如弓弦震顫,發出嗡嗡嗡的金屬之聲。冬日卻冷寂,但仍有一只或幾只蜂飛出蜂箱,去山林采蜜。這時花已非常稀少,我只看到了紫菀、野冬菊和尚未完全凋謝的油茶花。在一朵紫菀花里,我還找到一只死蜂,它的口器還插在花蕊里,翅膀裹著淡黃色花粉。
蜂,讓我想起了農夫,只要腳可以著地,手可以動,就會去地里干活,無論天多冷,風多大。
麻雀
我做了一個有關麻雀吃食的實驗。在院子的圓桌上用筲箕做了一個簡易的捕鳥籠,然后藏身廚房,半掩著門,盯著圓桌。一刻鐘后,麻雀來了六只,站在圓桌上東望西望,圍著筲箕小步跳。它們在筲箕外圍走了三分鐘后,一只麻雀進去了,小心地吃起飯粒。吃了幾粒后停下來,叫了幾聲,其他麻雀進去吃了。
我沒在筲箕嘴扎麻線,筲箕不會罩下來。麻雀吃了十幾分鐘,飯粒全吃完,然后飛走了。
我先后撒了三次飯粒,每次都由一只麻雀先試探性啄食,確定安全了,再通知其他麻雀一起享用。
2019年,我去鄱陽湖做候鳥保護調查,余干縣野保站站長說了小天鵝進食的故事。上百只小天鵝去湖灘覓食,由一只小天鵝先吃,半小時后,吃食的小天鵝沒有意外發生,其他小天鵝才開始進食。若有意外發生,小天鵝全部飛走,再也不會來。
做了麻雀吃食的實驗,我相信了他的觀察:為同類生存而犧牲的精神并非人類獨有。
愛是一種天賦。
(摘自百花文藝出版社《風過溪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