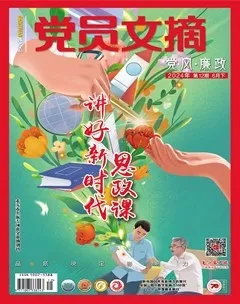基層減負進行時
張棖 喬棟 申智林

基層減負,松綁的是形式主義的束縛,擰緊的是實干擔當的狀態。以馬不離鞍、韁不松手的韌勁,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必將為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更堅強的作風保證。
精減文山會海
去年年底,陜西省漢中市西鄉縣私渡鎮微信工作群發布了一項優撫對象自然減員登記任務。私渡鎮紅安社區第一書記舒澤統計后直接通過微信群上報,用時不過5分鐘。
“以前此類工作必須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加蓋公章層層上報,一折騰就是一兩天。現在很多工作動動手指就處理好了,高效又便捷。”舒澤說。
陜西省將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列入工作方案、納入省委巡視,著重整治文件、會議“明減暗不減”,“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檢查過多等突出問題。
“多頭、層層要求下級報材料或報表,不僅沒有必要,還會讓本就人手緊缺的基層負擔加重。”西安市蓮湖區委常委、紀委書記周興鵬深有感觸地說。
為了根治備受基層詬病的重復報送問題,蓮湖區紀委監委打通壁壘實現信息跨部門共享,對于全區紀檢監察系統可以合并報送的文件,由一個部門牽頭收集;同時還破除“唯紅頭文件”的思維模式,鼓勵各單位通過郵箱、公文傳輸系統等渠道報送文件,讓信息“多跑路”,干部“少跑腿”。
西鄉縣則通過設置基層監測點,掌握動態信息,推動基層負擔問題專項治理走深走實。通過鎮級基層監測點,及時準確掌握基層負擔動態。每月對發文多、會議多、檢查多排名前三的縣級部門發送提醒函,糾正出現的問題和偏差。
“通過基層監測點的反饋,掌握基層負擔情況,從而有的放矢安排工作,做到文件可發可不發的堅決不發、能合并發文的堅決合并、已作出部署的不再發文。”西鄉縣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說。
卸下“指尖”之負
胡曉燕是重慶市永川區朱沱鎮民政救助崗工作人員。過去,她負擔最重的一項工作就是“填表”:她曾負責低保、特困、高齡失能老人等20多項報表填報工作,且每項報表都需層層上報、審核把關、簽字確認。她每月用于填報報表的時間占上班時間1/3以上,手機里各種工作QQ群、微信群多達60多個。
而現在,胡曉燕只需在“渝快政”里的“一表通”里維護相關數據即可,每月所用時間僅為半天。
2023年,永川區將基層反映強烈的工作“報表負擔”問題作為攻堅課題,探索打造“報表+臺賬”數字化融合場景,于當年9月在全市率先全面投用“一表通”應用,推動基層減負、治理增效取得顯著成果。
永川區大數據局副局長李曉莉介紹,其主要做法就是依托數字重慶“1361”總體構架,在基層智治體系下,構建“131”架構,即:“渝快政”統一入口,數字臺賬、智能報表、分析調度3個核心模塊,1個鎮街數據池。
永川區還對高頻報表拆解、集成,經5輪迭代優化,形成涵蓋黨的建設、經濟發展、民生服務、平安法治四大板塊的標準化臺賬93個,涉及“人房地事物組織”等字段3519個,涵蓋鎮街95%以上的工作需求。
以殘疾人相關報表為例,過去,各鎮街需向永川區殘聯、區民政局、區農業農村委等多個部門定時報送相關報表11張次,這些報表包含大量重復字段,如殘疾人姓名、持證狀態、家庭經濟狀況等,此前需在不同表格上重復填報。如今,各級、各部門間數據自動關聯、實時更新后,這些字段自動生成并合并為“殘疾人信息臺賬”,不再需要人工填報。

“‘一表通不僅減輕了基層干部的負擔,也減輕了區級部門的工作強度。”永川區民政局副局長黃豫軍說,過去,他們向鎮街收集一張報表,從制發報表到人工錄入匯總,平均需要兩天時間;現在通過“一表通”制發報表,各鎮街錄入數據后,平臺就自動生成匯總報表,從制發一張報表到匯總數據的時間減至現在的20分鐘。
明確服務事項,辦事更加順暢
2023年8月29日下午,正在村委會為村民登記特困人員認定資料時,湖南省長沙縣果園鎮新明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黃季明的電話急促地響起來。

“工程我支持,但青苗損失補償沒談妥,我不同意。”電話里,村民彭帥反映起自己的煩心事。
原來,前些日子,一條遷建的高速公路擬通過新明村,最近正做地質勘探工作,探樁打到了村民的稻田里,彭帥正是其中一戶。
“別著急,相關補償有明確規定,不會讓你吃虧。”耐心勸解完村民,黃季明隨即將記錄下的情況上報鎮政府。主管征地拆遷的工作小組對接施工單位,處置意見很快達成。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員就到村里同村民開展協商。丈量面積、明確標準、議定賠付細節,不到半個小時,一場涉及征地拆遷和青苗補助的工作就順利結束。

“今年湖南省出臺關于規范村級組織工作事務、機制牌子和證明事項的若干措施,要求不得將村級組織作為行政執法、拆遷拆違、招商引資、安全生產等事務的責任主體,事關征地拆遷,村級組織只需要協調當事雙方即可。”黃季明說。
過去,政府項目涉及的征地拆遷,有些單位往往將任務指標直接分派到村一級,這讓村級組織非常為難。
“口頭許諾做村民工作,回頭還得找有關部門申請兌現。”黃季明說,“責任落在身上,卻沒有與之相匹配的資源,工作負擔自然很重。”
2022年,長沙縣出臺關于規范村級小微權力運行的指導意見,梳理出59項權力清單指導目錄,明確了村級組織開展工作的制度依據、職責范圍和運行流程。
機制理順、負擔減輕,從繁重又細碎的常規事務中解放出來,黃季明如今能騰出更多時間帶著村民發展產業。
整合規范掛牌,優化檢查評比
2024年2月15日,在河北省衡水市武邑縣審坡鎮東里官村,返鄉過年的村民張春暉到村委會咨詢自家老房子的不動產變更相關事宜。令他意外的是,村委會門口原先掛著的一堆牌子只剩下了4塊。
東里官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張紅江說:“去年開展清理規范行動以前,村委會門口掛了不少的牌子,室內還有40多塊制度牌匾,并且規格不一、標準不等、質地不同、顏色各異,被村民戲稱為‘補丁墻。”

“多掛一個牌子,可能就需要多填一個表格,多交一份總結材料。各種臺賬、報表,有的要求一月一報,有的要求在線填報,給村干部增加了負擔。”張紅江說。
2023年下半年,針對部分農村干部群眾反映的村級站點設置多且重復,導致標牌、牌匾過多過濫的問題,武邑縣深入開展調查研究。
“‘牌子多‘掛牌熱,反映出農村基層承擔的任務過重,接受的檢查考核評比過多。”武邑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張宗利說,武邑縣委將村級辦公服務場所標牌牌匾清理規范行動作為開展主題教育的抓手,整合、取消并制止新增各類標牌牌匾,切實為基層減負松綁。
為配合整治,武邑縣還針對掛牌背后的相關文件通知、檢查評比等方面問題進行清理規范。全縣524個村級組織共計清理規范各類標牌、牌匾約1.85萬塊,取消或優化檢查評比26項。
(摘自《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