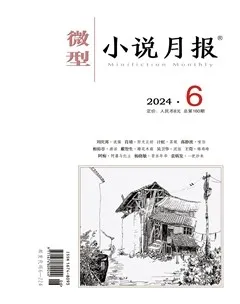啞伯
蔣靜波
啞伯死了。
堂兄告訴我,啞伯臨終前,突然開口,整整說了一天一夜,說得嗓子都啞了。嬸嬸捂住啞伯的嘴,讓他以后再慢慢說。那嘴卻像決堤的渠口,怎么也關不住。關了幾十年的話,如湍急的流水,嘩嘩嘩,流個不停。最后,嬸嬸和堂兄聽得打起了瞌睡。等到他們醒來,啞伯的嘴還大張著,人卻沒了氣息。
啞伯是我父親的兄長,他其實不啞。年輕時,因說話犯了事,被打斷一根肋骨,打落兩顆門牙后,還被抓了進去,一關五年。出來后,他說:“以后,我再也不說話了。”他真的說到做到。漸漸地,同輩便叫他啞子(啞巴),小輩則在原來對他的稱呼前加上一個“啞”字。他也不惱,仿佛那就是他的名字。
起初,嬸嬸很傷心,也不明白,好好的一個人,怎么就成了啞子?
啞伯在藥箱里找到一袋麝香追風膏。那是家庭常備的一種傷膏,遇到風濕關節痛、肌肉酸痛、挫傷扭傷時,人們一般不去醫院,就用這種傷膏在患處貼一張,基本能消腫止痛。不過,不到十分難受時,人們一般不舍得用。
啞伯取出一貼傷膏,貼在嘴上。傷膏像一個巨大的創可貼,將嘴巴和下巴牢牢地蒙粘住。濃郁的膏藥味彌漫在整個房間。在嬸嬸驚詫的目光中,啞伯走向外面。
人們見到啞伯,不管是熟悉的或陌生的,都嚇了一跳。誰見過傷膏這般用法!有人將啞伯當成了精神病人,離他遠遠的。除了吃飯和晚上睡覺,啞伯的嘴一直不離傷膏。起先,嬸嬸試著開導他說話。他就指著像貼著封條的嘴,搖搖頭。嬸嬸拿他沒辦法。
一天早上,嬸嬸得意地說:“昨夜你說了好多夢話,響著呢。”堂兄也說:“對,我在樓上也聽到了。”
啞伯似乎受了驚嚇,渾身顫抖,臉色灰白。那天晚上,他沒將傷膏取下。
幾天后,啞伯的嘴邊和下巴因傷膏引起過敏,一片紅腫,起了疹子。他改用紗布和膠帶蒙嘴。紗布比膏藥小一些,露出了下巴。兩個月后,啞伯的嘴巴像是結了痂的傷口,不用包扎或蒙住了。他已習慣了遇到任何事情也不發出一點聲音。
啞伯從灰堆里掏出一塊石板和一支石筆。黑色石板,A4紙那么大,白色石筆,這是啞伯上小學時學寫生字的學習用品。遇到必須交代事情時,啞伯就在石板上寫字,如“我去趕市了,下午回”“某人喪事,全家都去”等等。石板上的白字,抹布一擦就沒了。
后來,石板碎了,啞伯只好改用紙筆。不過他用得很少,能不寫的盡量不寫。他將每一張寫了字的紙都親自收起來,劃根火柴燒成灰燼才放心。
啞伯的脾氣倒是好了許多。以前,對于看不慣的人和事,不管何時何地,他會當場發作,罵娘,或揮拳頭,得罪了好多人。現在,遇到同樣的情況,他最多黑著臉,別過頭,匆匆離開,一副與他無關的樣子。這一點,倒是讓嬸嬸省心多了。
當地結婚有一項很重要的儀式——端茶(敬茶)。喝喜酒前,新娘子得一一向男方的長輩端茶。新娘邊雙手敬茶,邊恭敬地說:“爹、娘,請喝茶。”長輩大聲應一聲,喝幾口茶,奉上一份茶鈿(紅包)。堂兄結婚前,曾托我父親說服啞伯,新娘端茶時,做公爹的總得應聲。啞伯應承了。
到了那一天,新娘子端茶時,人圍得里三層外三層,他們最大的興趣其實是來看啞伯怎么開口說話。新娘子向啞伯奉茶,啞伯動了動嘴唇,誰也沒聽見他應聲。事后,啞伯在紙上寫道:“我真的應了,自己聽見了。”
有一段時間,啞伯學手語。
他天天走五六里路去學。回家后,啞伯兩只手像玩石頭剪子布游戲一般,翻來覆去做動作。他示意嬸嬸和堂兄跟他學,他倆不理。堂兄直接對啞伯說:“我們又不啞,學什么手語。”啞伯很失落,只好放棄。自己對自己做手勢,有什么意思。
啞伯比真正的啞巴還啞。我認識的一個啞巴,雖不會說話,但若誰犯了他,哇啦啦哇啦啦地叫得山響,三四里外也聽得見。可啞伯卻啞得無聲無息。有一天半夜,嬸嬸去解手,發現啞伯在床上翻來覆去,大汗淋漓。問他:“怎么了?”啞伯指指右下腹,齜牙咧嘴。嬸嬸問:“很難受嗎?”他點點頭。
堂兄急忙叫救護車。到了醫院,醫生說:“馬上動手術。”并責怪家屬:“闌尾都穿孔了,為什么這么晚才來?要出人命的知道嗎?”嬸嬸、堂兄辯解:“病人沒說,我們不知道。”醫生說:“闌尾穿孔很痛,起碼痛了一天了,病人怎么會不說?”嬸嬸、堂兄怎么也不明白,痛到這種地步,他為什么不叫一聲。
棺柩在堂前停了三天兩夜。按當地風俗,死者的老伴不必守夜。可是,那兩夜,嬸嬸一直從夜晚守到天明。白茫茫的月光照在清靜的堂前,嬸嬸注視著那張微微張開的嘴,感覺那里隨時可能會發出聲音。
選自《金山》
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