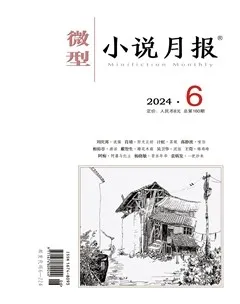爐火
李敏
雨終于在傍晚時細成霧絲絲,山路濕透了,黏黏一層粘腳濕泥巴。遠山罩著一層薄霧。
摩托車順著彎彎山路往上爬。花白頭發的摩托車司機,伸著脖子,抿著嘴,骨骼凸起的兩手緊握著搖晃不定的車把,像個勇敢的斗牛士。后座上男人背著鼓鼓的雙肩帆布包,神情緊張地盯著前面。拐過一個急彎,又一個急彎,接著是一個大斜坡,摩托車突突突一陣油門,又突突突一陣油門,路面泥濘被擰成蛇的樣子。車前進幾米,又滑下來,兩人腳撐了地,騙腿下車。
“就到這里吧。”司機說。
“哦,我背包太沉了。”男人說。
“路滑,爬不動,你也看見了。”司機說,含了一點兒委屈。
男人彎腰,把大背包往肩上推了推說:“那就到這里,辛苦你了,多少錢?”
“約二十里山路,收你四十元吧。”摩托車司機說。
男人掏出一張百元鈔票遞給司機。司機接過,手伸進口袋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說:“哥找不開。”
男人說:“都給你了。”
“那哪行,多收你六十塊錢,這樣吧,記下我號碼,下山時,打我電話,我來接你,不收錢了。”摩托車司機卷好錢,放進了胸前口袋,系上扣,說了電話號碼,讓男人記下。他摸出紅塔山煙,彈出半支遞給男人,男人伸手,又縮回來,說:“不吸了,戒了,酒也戒了。”
司機笑了笑,縮回手說:“戒了省事。”他抽出一支煙卷含在嘴里,上下摸火。
男人摸出一個之寶牌黃銅浮雕防風打火機,啪,藍色的火咝咝跳動,遞給司機,說:“給你了。”
司機放手里掂了掂,摩挲著,抬胳膊抹了一把額上濕漉漉的頭發,眼角魚尾紋蕩漾開來,說:“城里的打火機真好,山里買不到這樣的,我拿了去顯擺顯擺,你也快些走吧,別等天黑了。”他順手裝打火機進褲兜,抬腳上車,踹著火,叼著煙卷,突突突地蜿蜒而下。
他背起包,繼續沿著小路往上爬。拐過“之”形路,穿過一片樹林,繞過三個風車。天黑時,男人腳上沾滿泥巴,停在一排青瓦老房子面前。石墻斑駁,門窗破舊。男人伸手摸了摸石縫里的青苔,擦去額頭上的汗水。
他走到最南邊的房子門前,深吸一口氣。
坐完高鐵坐汽車,坐完汽車坐摩托車,步行四五里,終于到了。
他敲了敲虛掩的杉木門,沒有人應答。他輕輕推開,屋里一地昏黃的光,燈懸在爐上發出朦朧的光圈,煤爐子上坐著陶壺,噗噗冒著水汽,幽藍的火苗圍舔著壺底邊活潑潑地舞蹈,空中浮動著潤潤淺淺的草木味。男人環視室內,木板搭起的桌上,一摞一摞小學生作業,語文、數學、英語、科學,還有一摞繪畫。桌邊大肚陶罐里插著野菊花和干樹枝,樹枝上掛著一串風鈴,還有兩年前他賣給她的梅花夜光表,藍瑩瑩的指針嗒嗒走著,椅子上搭著她的舊羊絨大衣。
門吱呀一聲被推開。她站在門口,手里提著水桶,身穿對襟棉布袍,腳上是方口布鞋,整個人說不出的素凈。看見他佇立在那里,她笑了,抬手把一綹頭發別在耳后,輕聲地說:“來了?”
男人說:“來了。”
女人問:“媽心臟好些沒?”
男人說:“還好。”
男人問:“還是十七個?”
女人說:“十九個了。”
男人說:“幸好這次我買了二十個,天暖和了,再添些別的。”男人一陣輕松,夜鳥歸巢的感覺。他過去接過水桶。她虛掩了房門。
男人看著她。她摘下男人的帽子,彈著肩上細碎的濕,說:“這雨霧,七天了,要發霉了,還要下嗎?”
“一會兒看看,若起風,雨就會停。”他說。
她取了一條干毛巾,輕輕抽打男人的衣服,從衣領到褲腳。她搬來兩只木墩,分別放在爐子兩邊。她說:“你坐,我來沏茶。”男人坐在爐火邊,烤著爐火,全身舒適,關節咯吧咯吧地松開。
她用茶盤端來紫砂陶壺、陶罐、兩個粗瓷碗,說:“帶來的茶杯沒了,咱用大碗吧。”
她用開水燙熱了紫砂壺,倒掉了壺里的開水,拿起銀茶匙,從陶罐里盛出幾匙茶葉放進茶壺,再次沖滿開水,蓋嚴壺蓋。她又提起水瓶,將開水慢慢澆遍壺體,穩、準、柔。香氣裊裊中,一雙小巧白手提腕、蹺指,舒舒展展,仿佛還是在大茶樓里擺茶道的那雙。
人生很奇妙,兩年前,商場、酒樓、茶室、高爾夫球場……即便厭倦,他們兩人也一樣在軌道里循環,直到偶然一次跟朋友來這里參加捐贈活動,她便無法放下山中那十幾個沒有老師的孩子了,就像他放不下冠心病的母親。
這雙手從從容容地沏茶,茶香飄逸出來,是糯香熟普洱。她的習慣改了很多,比如飲食、服飾、化妝、作息,但喝茶的習慣一直沒改。她為男人倒了半碗,又為自己倒了半碗。
杉木門吱呀開了條縫,一陣晚風帶著春意涌了進來,翻動著桌上的作業,風鈴丁丁零零、丁丁零零地響。隔著爐火,她臉上發著美麗的紅光,微笑著看著男人。
選自《小說月刊》
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