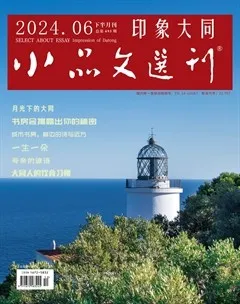關于歷史的15個真相
莫少儒

1、定義人類文明的方式有很多種,我比較關注的是人類各個階段的食物來源問題,這在各個發展階段都是首要問題。
不同的食物來源或生產食物的動力來源決定著不同的文明形態。因此,我定義人類文明依次經歷了采摘(狩獵)文明、農業(畜牧)文明、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當前正處于商業文明和科技文明的交界,未來還將迎來智能文明。
2、采摘和狩獵本質上都是采集食物,畜牧和農業本質上都是復制食物。畜牧是較為低效的對動物的復制,農業是較為高效的對植物的復制。
在農業發展的初期,由于產量低下,勞作艱苦,人類的生活并不好過。
在堅持了非常漫長的時間之后,農業進入成熟階段,真正意義上解決了人口增長和食物供應不足這一組矛盾,出現了剩余食物,并因此迎來人類歷史上的首次社會化分工。
3、社會化分工必然會產生階級,階級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新增了一個動力——階層流動。至此,這個動力會成為關鍵動力,一直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并且這個動力將不會消失——即意味著,階級不會消失。
4、在人類進入農業文明之后,一個國家的地理環境、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個國家農業文明的發展程度。
以我國為例,考察其地理環境、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你會發現她具有形成封閉帝國的先天要素。為了更顯著,一定要對比歐洲。
在地理條件形成的屏障之內,短暫的分裂將被長久的統一取代,農業的發展需要穩定,而穩定則需要特定模式的帝國。
5、秦始皇是個偶然,但帝國是必然。
這個觀點的底層是地理決定論。秦始皇靠一己之力、一人之愿,無法構建一個帝國。當時的中國也不可能繼續維持相互制衡的聯邦,否則周王朝就不會覆滅。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組建帝國,是歷史的必然。但秦王朝注定短命。
6、在當下,痛罵秦始皇是一種正確。但是,秦始皇該罵的點是其殘暴乖張、荒淫無度、殺害無辜,而非創建秦制。創建秦制非秦始皇一人之意愿所能為。
7、任何權力的底層都是暴力,沒有例外。但僅僅依靠暴力,任何權力都沒有辦法長久維持,因此需要故事。
8、暴力為權力提供了基礎,故事為權力提供了穩定。
本質上來說,故事讓權力可以合理地使用暴力,為權力擁有者提供了合法性。
在周王朝時期,故事通過周禮“演繹”出來,通過各種儀式使其深入人心。后來孔夫子要恢復的,就是這個周禮。受歷史局限,夫子很天真,他也不想想,如果周禮真的有用,怎么會出現春秋?
9、后來,故事逐漸演變為法律,彼時的法律還很粗糙,但與今天的法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維護其對應文明的秩序。
法律不為人類幸福負責,也不會為正義負責,只為秩序負責。幸福、公平、正義這些內容,是秩序下的衍生品。
10、秦始皇通過郡縣制將其權力和王法伸入到疆域內的各個地區,妄圖只依賴暴力和法律統治那么大的疆域,過于自負,注定失敗。
劉邦的聰明在于,和各地望族達成默契——至此,家國同構成為維持帝國統治的核心操作。國有國法,是為王法;家有家規,是為家法。
朝廷和地方這一組關系中,地方指的是各地宗族,而非各地政府。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根源在此。
11、再次強調,中國古代社會自秦朝起,就不再是封建社會,而是帝王專制社會。帝王專制并非某個人的意志使然,而是所有人的“共謀”,是歷史的必然。
農業生產需要穩定,穩定需要專制,專制需要帝王,帝王需要穩定,所以選擇與地方宗族“合作”。后來,又選擇了儒家成為帝國穩定的一塊基石。
12、董仲舒是講故事的高手,他或許真的以為“君君”所以“臣臣”,他或許真的以為在帝制之下,臣子還能像周王朝的三公那樣制約王權。如果他真的這么以為,只能說他和孔夫子一樣天真。不論怎樣,董仲舒對帝制的“貢獻”絕不比秦始皇小。
13、獨尊儒術之后,儒家的職責就只有一個——為帝制服務。一方面鞏固皇權的合法性,一方面協助皇帝治理國家。
皇帝是老板,貴族是股東,百姓是被收割的群體,官員是打工仔。打工仔的最高職位是CEO,即宰相。在帝制王朝下,CEO很危險,因為帝王沒有商業文明時期大老板的覺悟。
14、地方的父權即是朝廷之皇權的影子,絕對權威,不容質疑。在知識分子界,樹立了以孔夫子為代表的“師權”。
師權、父權和皇權,本質是一致的,都是不容質疑的絕對權威。其中,師權和父權都在為皇權服務,是皇權的支柱。中國傳統文化中將“質疑”是為“忤逆”,從根源處已經決定了這一點,這造成中國歷代知識分子都在讀“死”書,行“愚”孝。
讀死書這一狀況,在今天并未有多大改善。
15、搞歷史的很容易把自己搞成上帝視角,聽歷史的也容易把自己聽成上帝視角。但是歷史,尤其是古代史,真實性能達到80%那就非常逼真了。就這80%真的歷史,還是挑挑揀揀寫出來的,想要還原當時的各種情況,基本沒戲。
選自“認知演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