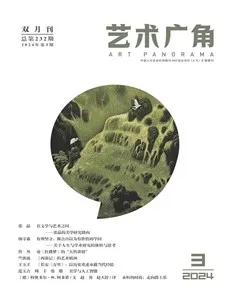“天下共同體”何以可能
摘 要 與西方“現代世界體系”的遭遇使中國傳統“天下秩序”遭遇合法性危機,走出危機的可能在于擁抱“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同時超越“世界體系—天下秩序”二元對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天下共同體”屬于相互闡釋關系,“天下共同體”既賦予“天下”以其應有“形而上品性”,也保證了“天下天下化”邏輯歷史性與“天下秩序”的當下化進程,而“天下天下化”邏輯在使“天下無外”理念逐步現實化的同時也推動“天下共同體”的逐步生成。賈平凹、姜戎與徐兆壽小說的價值在于以各自方式相繼呈現了“天下秩序”危機化、“天下秩序”之現代創生可能及“天下共同體”所以生成的文化邏輯。
關鍵詞 國民性批判;現代世界體系;天下天下化;中華民族共同體
本世紀初,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先后出版了《懷念狼》(2000)、《狼圖騰》(2004)、《荒原問道》(2013)等與“傳統天下觀”相關的三部小說。其中《懷念狼》與《狼圖騰》將魯迅“國民性批判”與對天下觀的反思予以結合,《荒原問道》則對“傳統天下觀”現代創生可能所需文化人類學背景展開詩學暢想:“傳統天下觀”現代創生(“天下天下化”)以“中國式現代化”為背景,“中國式現代化”認可“進化論”思想中積極因素的同時主張以“天下共同體”生成為最終理想。因為天下是所有天下人的天下,所以“天下天下化”邏輯演進所生成的“天下秩序”就應將差異化文化模式予以包容,這就要求“天下天下化”進程要具備超越西方“天國天下化”邏輯的可能,這種可能在使“天下秩序”超越西方現代世界體系的過程也超越“體系—秩序(普遍—特殊)”對立而向“天下共同體”演化。
一、問題之提出:“天下天下化”與“國民性批判”
《懷念狼》中敘事者與馬先生在小鎮閑聊時就“天下”去意義化發出感慨:“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可以有大學問的,現在的味道全變了!古人那是騎一只毛驢飲風餐雪,一路上飽受著艱難也飽受著山光水色……現在呢,除了這次我特意要尋找狼,別的人和我別的時候不是坐了電氣火車和飛機,萬里路幾個小時就到了呢……手術式導彈戰爭再也不能產生浴血搏殺的英雄,天下這個詞越來越沒了意思……”[1]“天下”去意義化是因支撐天下秩序的物理與心理—文化空間“動態平衡”機制失效,若文化距離存在被擴大可能,那么“天下大同”即是幻影;但既然“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大同”就該是可容納差異的天下,對待“差異”無非“同化—涵化”兩種方式,“同化”屬于“民族或文化中心”話語,而“涵化”則需不同族群在生活方式層面的良性互動,而“同化—涵化”互動就涉及因與西方文明遭遇而生成的“國民性批判”,這也是《狼圖騰》題旨所在。人物“陣陣”在反思中國近代落后原因時認為“最難學的是西方民族血液里的戰斗進取、勇敢冒險的精神……魯迅早就發現華夏民族在國民性格上存在大問題……華夏的小農經濟和儒家文化……軟化了華夏民族的性格,華夏民族雖然也曾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但那是以犧牲民族性格為代價的,也就犧牲了民族發展的后勁”[1]。那么魯迅“國民性批判”與“天下天下化”是什么關系?
回顧魯迅“國民性批判”相關文獻,可發現其涉及中西文明歷史化進程中“世界體系—天下秩序”相互關系,因西方現代世界體系在其全球空間拓展中使“天下被弱化”而導致文化反思,西方世界體系“中心—邊緣”空間規劃中中國文明面臨“融入與排斥”二元選擇。“融入”意味著邊緣化,而“排斥”意味著對所謂“普世文明”的拒絕,其文化后果或接受西方文明關于“東方中國”形象的定型化投射,被動“融入”西方世界體系即成為西方文明“全球空間”規劃中的“客體對象”,而主動反思則意味著一種“反客為主”的文化姿態。由于雙方文明發展階段存在較大差距,處于現代文明階段的西方及其發展模式就成為處于傳統階段“中國文明”的效仿對象。于是“傳統的”就成為落后的,關于“何以落后”之反思就演化為“中國國民性”批判,西方文明“自然—文明”二元模式就成為對中國文明發展階段的評價標準,內涵權力宰制的西方文明“文化/種族中心”話語模式就成為中國學者對自身文明發展過程予以評價的先驗框架。在“西方—東方/文明—野蠻”先驗框架及其種族權力投射中,中國“天下秩序”因遭遇西方世界體系邊界之拓展而使“天下天下化”邏輯遭遇困境,并在反思中生成強者崇拜;但悖謬的是強者崇拜反而刺激了傳統中國文明中潛在的“民族或文化中心意識”,并生成“我—他”對立情緒,這不僅造成本民族成員在反抗外敵過程中的內在分裂,也因分裂持續而使曾維系共同情感的“天下秩序”被解構。
需要指出的是,魯迅“國民性批判”反思是對西方“民族國家”模式的超越。為西方“國民性話語”提供話語前提的是內在于西方世界體系的“國家體系”,即國家的可能以“國家體系”先在為前提,而“國家體系”意味著一整套關于國際交往及文明交往標準預設,文明發展階段的差異顯化為現實層面國力強弱對比。這種差距使“國民性批判”轉化為一種怨恨心理,并因差距持續擴大而導致內生性恐懼、進而生成為文化防御姿態。因潛在文化中心意識的顯化而將“華夷/滿漢”二元差異絕對化就成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談論中國民族問題的慣常邏輯。魯迅由“傳統倫理”向“文化劣根性”的轉移,使“國民性批判”與“天下秩序”邊界拓展及其可能聯系起來。面對西方“世界體系”邊界的持續拓展,當代中國需在創新國家治理模式的同時,在文化層面對“天下天下化”邏輯予以反思;“國民性批判”的要點在于對中國文明“天下秩序”現代創生可能性的反思。
“天下秩序”是傳統中國國家治理的哲學基礎,“天下國”則是國家治理過程的擔當者。在中國“王朝地理學”空間框架中,“王朝稱名”差異及不同王朝合法性都是以“天下秩序”維護者自居、進而獲取其王朝正統。理想形態的“天下秩序”是以“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與荒服)為基礎形成的由內而外推、等級化多重同心圓結構。處于不同層次的人們與“天子”間維持不同層次的政教關系,并因天子對其控制力度的強弱程度而有“化內—化外”之分,“化內”者接受天子直接統治而“化外”者則對天子統治保持著名義服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由此體現為三種秩序:“天子—官僚”君臣秩序、“中央—地方”郡縣大一統秩序及“天子—四夷”天下秩序。這意味著以“天下秩序”為基礎的“天下國”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概念。作為一種由儒家學者提供理念、經由歷代王朝政治實踐生成的(區域性)國際秩序,“天下秩序”之實踐可能即“中國文明”以其“典范”式存在為區域性國際關系提供秩序化可能。隨著西方“現代世界體系”邊界的拓展,“天下秩序”在遭遇危機的同時也被迫接受西方現代世界(國家)體系的知識社會學闡釋體系,這一方面使“天下”成為一種客體性存在,同時也要求“中國”成為現代世界體系中的合格成員,中國由此面對著通過學習并遵守以國際法為主的條約體系,而為世界體系所接納的任務。
但這個需遵守的“國際法條約體系”是中國知識分子所不得不學習的關于“國際社會”秩序化的知識社會學體系,這就使中國學界陷入“天下秩序—世界體系(天下體系—民族國家)”、“非此即彼”式悖論,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相互配合并共同促進了西方現代“國家體系”及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現代世界體系的生成,這也對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及其國家觀(民族觀)產生影響:雖然“天下”還是那個“天下”,但與“天下秩序”生產與再生產相關的話語卻被轉換成歐洲民族主義話語,而其內含之“非此即彼”邏輯也被不自覺地運用在近代中國革命所需要的“種族話語”邏輯及其生產過程中,并激發了諸如“夷夏/滿漢”對立基礎上的“華夏民族主義”話語。雖然他們套用了西方民族國家形式,但骨子里依然還是“天下秩序”的繼承者或維護者。
與現代國家體系一樣,以自由主義為特征的現代政治學說也是西方知識社會學體系組成部分之一,立足西方政治社會學展開“國民性改造”在給予個體自由選擇的同時也放棄了對個體道德世界的干涉,那么所面臨的不僅是尼采所呈現的“末人社會”,更是一個不同民族或族群對立紛爭乃至沖突的民粹主義世界,“末人社會”即天下秩序“天下化”邏輯失效階段。在遭遇西方“世界體系”過程中,曾經作為道德典范的本土儒道及中國化佛教都沒能成為全民族的共同信仰。“儒教雖然被統治者看中并大加利用,但‘儒家的說理體系對一個絕大多數是文盲的民族來說,并沒有起到西方高級宗教那樣把整個文明從原始黑暗引向光明的作用。它造成了中華文化的斷層,同時又把這個斷層掩蓋在士大夫文化發展的光芒中,使中華民族的絕大多數處于比單純的原始文化狀態下更悲慘的境地。”[1]如果說中國文明之人文精神缺乏超越性價值屬于理論預設,那么由魯迅“國民性批判”反思所生成之傳統“天下秩序”之現代創生可能則是對該預設的超越。“天下秩序”現代創生源自“天下共同體”理念的超越性,因為“天下共同體”理念就歷史地內在于“人類命運—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結構中。
二、從“人類命運(中華民族)共同體”到“天下共同體”
“人類命運(中華民族)共同體既是對西方民族主義(漢族中心主義)的超越,也是中國文明“天下秩序”歷史性演化的結果,二者結合使“人類命運—中華民族共同體”有演化為“天下共同體”的可能。在華勒斯坦看來,西方現代世界體系空間拓展已經達到極限,其本質上源自歷史資本主義在全球化過程中遭遇的積累困境、政治合法性困境與地緣文化困境。“資本主義文明也是圍繞一個過去從未占過統治地位的地緣文化命題建立起來的。這個命題就是:個人作為所謂歷史主體的中心作用。個人主義代表一種困難的選擇,因為它是一把雙刃劍……資本主義文明強調個人的首創的精神……個人主義還有另一方面,這就是地緣文化論會存在困境的原因。個人主義助長了一種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特別劇烈的競爭,因為它肯定不是少數精英的競爭,而且是整個人類的競爭。不僅如此,在邏輯上這是無限制的競爭。”[1]地緣文化困境源自西方文明中心論(“獨天下之利”)及其民族中心主義思維,該思維不但使內在于西方世界體系的“國家體系”成為競爭性而非合作性體系,同時也使東西關系呈現出“普遍—特殊”對立傾向,而走出歷史資本主義地緣文化困境的出路就在于倡導合作而非對抗性地緣文化,這是中國文明“天下共同體”理念超越性使然。
與西方文明“獨天下之利”相比,中國文明歷史文化邏輯所生成之“中華民族共同體”內涵“共天下之利”空間思考,并在超越傳統天下觀“中心—邊緣(核心—邊疆)”空間關系的過程中沿“王朝地理學—革命地理學—發展地理學—新文明空間”向度展開。“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尋求獨立自主的解放斗爭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探索歷程,都是在東西方地緣政治之爭的大背景下為爭取生存、謀求發展空間而進行的……中國近現代歷史空間的轉型是一部從‘王朝地理學到‘革命地理學的發展史。”[2]“革命地理學”解決的是東西方地緣對抗中由被動依附而轉向“地域獨立與地緣自主”,但蘊藏于“天下秩序”中的深層次文化結構問題并未因革命勝利而解決,因此“革命地理學”尚需向“發展地理學”演化,并在超越歷史資本主義“地緣文化困境”的同時向不同文明形態間差異共生演進。這就使“中華民族—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超越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可能,因為亨廷頓只看到文明差異與對立,而沒看到文明交融。
作為“天下共同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之歷史性生成也是“天下天下化”邏輯逐步內化的過程。如果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立足于全球社會對不同文明模式關系予以協調,那么不斷內化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就要求對中國文明全域空間關系展開整體反思。其中既涉及“城鄉—區域關系”協調發展,也需超越因“傳統天下觀”及其“中心—邊緣”空間模式所形成的傳統文化心理。立足于“天下共同體”之“外—內天下”雙重空間,如果說“天下共同體”邏輯外延意味著“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那么其邏輯內涵則首先意味著“天下是中國人的天下”;如果說“天下共同體”為天下人所“共有、共建與共享”,那么“天下共同體”首先應為中國人所“共有、共建與共享”,這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之于“天下秩序”要義所在。若該推理可接受,那么魯迅“國民性批判”價值就在于從文化心理上超越西方人類學知識框架(自我—他者/西方—中國)的過程中,跳出西方民族主義“主人—奴隸”邏輯,并在全球社會層面超越“世界體系”局限(界限)過程中推動中國“天下秩序”向“天下共同體”演化,關鍵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內化及“天下一家”文化心理的持續塑造。魯迅的“國民性批判”如此,賈平凹、姜戎及徐兆壽關于“天下”反思同出一脈。魯迅和賈平凹都生于傳統修齊治平文化邏輯中,魯迅所憤怒者是因“國”已不治而“天下”失其太平;賈平凹緊隨魯迅直面社會個體痛苦和彷徨狀況,是“家—國”問題雖因政治穩定而背景化,但“天下治(大治)”仍處于不確定狀況,遭遇“世界體系”使“天下天下化”邏輯須在協調自身“內平衡”過程的同時也需協調“世界體系—天下秩序”間“外平衡”過程,這是徐兆壽《荒原問道》主要關懷所在。
三、在超越對立中生成天下共同體
如果說“天下秩序”的“內平衡”存在決定著“秩序—體系”過程中“外平衡”的可能,那“內平衡”之生成則主題化于前述小說“城—鄉”“農耕—游牧”“中心—邊緣”等系列對立關系中,超越諸對立關系中事關“天下秩序”現代創生與“天下共同體”的生成可能性。小說《懷念狼》以山地狼與人關系入手對“國民性批判”予以關注,類似問題在賈平凹小說《高老莊》中也出現過。《懷念狼》延續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賈平凹之“尋根”,是一部多聲部交響曲,是“對故鄉經濟、文化、民風、山水的探尋性描述,是放開眼界審視中西文化以尋覓自己的美學立足點,是對現代意識的思考和追求……‘尋根是一種現代意識所催發的開放,它是在中西文化發生碰撞時去探尋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內質和中國文化的底蘊……”[1] 西方世界體系在其邊界拓展過程中與“天下秩序”的遭遇在《懷念狼》中具化為“狼與羊”對抗:“爛頭說這地方什么野物都有,最多是狼和黃羊,黃羊抵角粗大有力,狼多的時候,它們怕狼,狼也怕它們,狼是銅頭麻稈腿豆腐腰,黃羊就專門抵狼的腰,一頭撞過去狼就癱在那里了,現在狼少了,黃羊就稱王稱霸,它們愛窩里斗,抵開仗了人是輕易不敢靠近的,常常就相互殘殺,數量也越來越少了”[2]。作為“國民性批判”指向的傳統文化陰暗面,《懷念狼》影射“天下秩序”因承平日久而失去進取精神后就陷入內斗。“人是在與狼的斗爭中成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了驚恐、孤獨、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死亡的境地。懷念狼是懷念著勃發的生命,懷念英雄,懷念著世界的平衡”[3]。理解“世界平衡”需結合《懷念狼》中另一人物成義的英雄言說。在英雄先后將禍害村子的白虎與青龍殺死后,英雄卻被村里人當成禍害而殺。“村人歡呼他,又是設宴慶功,他喝下一壺酒,得意地說:是英雄就要為民除害,你們還有什么事可以讓我去干嗎?村人說:沒有了白虎青龍,但還有一個害,如果這個害除了,天下真的就太平了。英雄問:是誰?村人說:是你。英雄吃了一驚:是我,怎么能是我?”[4]這就觸及“天下太平”和“世界平衡”間的關系協調:“天下太平”屬于“內平衡”,因為傳統中國“天下”乃是“家天下”,天下是君王可代代相傳的家產,“天下國”即中央王朝基于“家天下”觀念而建立起來的“血緣—倫理政治共同體”,因此“天下太平”即以“天下主”自居的“王朝”由其“血緣—倫理秩序”出發在將“周邊族群”按“親疏遠近”關系予以差異化空間配置的過程,中央王朝“通過‘結盟‘和親‘納質‘賜姓等方法擬制的人身關系中,中央王朝與夷狄酋邦之間也是有長幼尊卑秩序之分的。兄弟之國有長幼之分,和親雙方亦有翁婿之別,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中,‘親親‘尊尊原則的具體體現”[1]。這種經“由內而外—由親及疏”差異化空間配置過程達成的“天下秩序”的平衡是短暫的;隨著王朝進入由鼎盛而衰落期,“天下秩序”因危機狀況而使“世界平衡”問題凸顯,并結構化為東西方“天下秩序—世界體系”間關系協調問題。
面對西方“世界體系”邊界不斷拓展,傳統“天下國/秩序”因不能有效應對而使作為其合法性基礎的“血緣—倫理秩序”陷入困境,并體現在《懷念狼》因維護商州生態平衡而是否需引進“新狼種”的思考中。“以前只知道烏克蘭豬是從蘇聯引進的,長毛絨兔是從安哥拉引進的,沒聽說過狼也引進,外國的東西都比中國的厲害,新狼種是什么樣兒,如果引進投放了,還能不能讓打獵?”[2]立足生態學角度,處于“內平衡”狀態的“天下秩序”遲早會因系統內部不同要素“自交換”過程在達其“閾限”后趨于失衡,這一點體現于小說人物人格及身體殘缺等方面,這是賈平凹對“天下秩序”內在缺陷的文化反思。傳統社會中的人因閉鎖于其社會身份或階層限制中而主要體現為一種功能性存在,這意味著“家天下”中“身體”肉身化過程是缺失的。“破缺”是人格化或社會化過程之難以展開或過早結束所致,所謂“新狼種”引進恰恰是期待“文化—人格結構”之更新。
與《懷念狼》類似,《狼圖騰》中也有類似“養狼”情節。“他養狼,在精神上是褻瀆,在肉體上是通敵。他確實觸犯了草原天條,觸動了草原民族和草原文化的禁忌。他不知道還能不能保住小狼,還該不該養狼。但是他實在想記錄和探究‘狼圖騰,草原魂的秘密和價值,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曾對世界和中國歷史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狼圖騰,隨著草原游牧生活的逐漸消亡而消亡……”[3]如果說《懷念狼》中“天下秩序”遭遇合法性危機,那么《狼圖騰》中“天下秩序”則因合法性危機而進入自我懷疑。除非借助“外力”主動更化,否則“天下秩序”將被解構,這種外力就是“暴力崇拜”。作為文化反諷主義者,張繼(小說人物)視儒家文化為“羊性十足的弱者的哲學,全然不懂得儒家‘剛健中正的品格和堅毅誠信、博厚悠遠、仁愛通和的精神,不知道儒家文化代表著一種高度文明的文化,既不是什么狼精神,更不是什么羊性格,而是人和人道的精神”[4]。文化反諷有可能生成歷史虛無主義。“蒙古人不僅信奉‘天人合一,而且信奉‘天獸人草合一,這遠比華夏文明中的‘天人合一,更深刻更有價值。就連草原鼠這種破壞草原的大敵,在蒙古人的天地里,竟然也有著如此不可替代的妙用。”[5]蒙古人所信仰的“天人合一”屬于“騰格里信仰”,一方面“‘天是監臨下民、支配一切、至高無上的‘異己力量。另一方面,‘天又是根據人們的‘德來賞善罰惡的。‘天的絕對權威和作用的顯現,必須經過‘德這個中介……人與神的關系便轉變為人與人的社會關系”[6]。作為一種“以德應(配)天”倫理思想,“騰格里信仰”內涵在對自我有限性予以主動認可的基礎上順應自然規律,由此去理解《狼圖騰》中“天葬”描述,可認為“狼性”即生命的自我獻祭,即以自我求死方式回歸“騰格里”。不過禮贊“騰格里信仰”不能以批判農耕文化為前提,“世界上最早被統治集團擰軟耳朵的人群就是農耕民族。直到如今,‘執牛耳仍然是許多人和集團孜孜以求的目標”[1]。即使我們不再主動去“執牛耳”,但也必須有能力去捍衛自己的“耳朵”,所以《狼圖騰》也在提醒我們發展經濟的同時不能忘記曾經的歷史。我們不可能去征服和壓迫別的民族,但我們不能因此遺忘近代以來列強給我們帶來的深重災難。因此姜戎關于狼性精神的書寫正是對反抗與斗爭精神的肯定。如果說“騰格里信仰”所培植的是勇敢、自我獻祭“狼性”精神,那么生活于儒家“天下秩序”中的個體則因身份閉鎖而呈現出“順服”(羊性)狀態,這就使《狼圖騰》與“國民性改造”問題聯系起來:天下秩序若不具備容納“中原/農耕—草原/游牧世界”之可能,那么“天下秩序”之改造是否應以西方“世界體系”為標準?而這正是《狼圖騰》矛盾所在:以西方“現代世界體系”為標準是對“西方—東方(中心—邊緣)”模式的認可,該認可是《狼圖騰》“農耕—游牧”二元對立敘事框架的文化前提,但該前提及由此生成的《狼圖騰》創作是反歷史的,它本質上“是一種反人性、反文明的道德……一個嚴峻的事實是,我們的文化正處于一個固有秩序解體、固有規范失效的變構過程……追求權力和金錢的功利目的高于一切……價值和信仰出現真空狀態,人文精神呈現危機情形”[2]。立足賈平凹《懷念狼》所呈現“天下秩序”與“世界平衡”遭遇來看,“狼性精神”還是需要的;但對“狼性”的需要不能以“暴力崇拜”為目的,因為“需要狼性”走向“暴力崇拜”是對“天下共同體”的背棄,但因反對“二元對立”走向另一種“二元對立”卻屬于歷史退步。如果說《懷念狼》使“天下秩序”與“世界體系”對立被凸顯,《狼圖騰》中凸顯“草原狼”提醒人們不可因“剛健驍勇”精神需要而走向“暴力崇拜”,《荒原問道》中的“荒原狼”意象的建構則在超越前述“二元對立”的同時進而上升到“天下秩序”形而上品性。更重要的是,三部作品在空間方面呈現出由“王朝地理學”“革命地理學”向“發展地理學”空間轉向(商州—蒙古草原—河西走廊),這種轉向在超越“農耕—游牧”對立的同時為“新文明空間”的生成奠定了文化前提:“天下共同體”之可能取決于“天下無外”理念。
四、天下無外如何可能?
徐兆壽小說《荒原問道》于2013年出版,小說以夏忠和陳子興為代表的兩代知識分子成長歷程為主線,在時空交互展開中就“荒原”內涵及文化救贖可能予以詩性觀照。如果說賈平凹“商州”使“世界體系”與“天下秩序”相互遭遇而處于危機狀態,姜戎之草原及“騰格里崇拜”對處于危機中的“天下秩序”提出一種激進化途徑,但因其歷史虛無取向也不可取。那么徐兆壽作品中“荒原”意象的出現則對以“內平衡”過程來達成“救贖”可能的“天下秩序”的“現代創生”提出一種極為可取的方向,即以“中原中心”為基礎的“天下秩序”是否可能在跨越其“血緣—倫理秩序”、并在向“天下秩序”邊界之“荒原”地帶擴展中獲取其再生可能?“荒原”所以荒原者除卻自然地理意義之外,還象征著兩性間情感的缺乏。比如小說人物王秀秀對夏忠所表現出來的性渴望。“流放者”夏忠也是多余人,其被“流放”于“西北”是因作為地理極遠且文化邊緣地帶的“西北”原本就是處于傳統“天下(王化)”之外的,不能或拒絕為“王道”所感化者自然應被排除在“王道”之外。小說最有價值之處還在于知識分子關于“荒原”的態度。面對“荒原”,夏忠只感到絕望,“他向著荒原的深處走去,離鐘老漢和羊群越來越遠,但荒原上除了荒原還是荒原……他不知道這一切都掌握在誰的手里”[1]。需要改變的是人,而人的改變可以促進其生存環境的改變,否則人可能為環境制約而陷入斗爭,對此《荒原問道》再次以“狼與羊”關系予以詩化。
首先是夏忠(好問先生)打狼這一情節,對于自然地理意義上的荒原來說,能夠成為其主人的要么是狼,要么是人類自己。而如果“人”成為荒原之主,那么“狼”將縱橫于荒原。對于文化荒原,可成為其主人的要么是對原有文化予以“現代更化”,要么在被動地接受“他者”文化過程中失去自身文化根性,這是西方“現代世界體系”邊界不斷東向擴張之所欲。對于西方“現代世界體系”邊界不斷拓展,“天下秩序”若不能予以有效應對,只能在被動“融入”的同時不斷邊緣化,邊緣化的“天下秩序”則不可避免地走向封閉進而陷入內爭。因此“荒原狼”本質上是人類欲望的化身,當占有或控制欲成為“人性”深處主導趨勢,人自身就披上了“魔鬼”裝束,人之死意味著人身上狼性的生成,而狼性生成則意味著人性沉淪。“很多年后,即使在遙遠的希臘海灘上……我還是會睜著眼睛做夢。我夢見自己一個人到了我們村子西邊的戈壁荒原上,本來我跟著大伯在放羊,后來我就一個人去找那只走散的小羊。剛開始我看見它在無邊的荒原上孤零零地奔跑著……越跑越遠……我跟著它不知怎么去了一個陌生的村莊……村莊里一個人也沒有……我發現那個村莊比荒原更可怕。”[2]無人“村莊”比“荒原”更可怖,那個村莊并非由人們自然匯聚而成,那“村莊”是流放者們苦役地,對此徐兆壽以詩性語言予以質問:
人性道德范式的創造者,人類的先鋒,尊敬的孔子/……/大道運行時,天下大同,可為什么從黃帝到文王天下都姓姬/大道不行時,天下歸家,可為什么你還要贊成這不幸的家天下/你說,虎不食子,天下歸仁,但為什么禮不下百姓……[3]
如果說邊界不斷拓展的“世界體系”是“天下失序”的外因,那么由“天下失序”而“天下秩序”之現代創生可能則首先要求超越前述“血緣—倫理秩序”或“西方體系”而向更具包容性的“天下共同體”生成,核心問題即天下如何無外?
小說《荒原問道》開篇處,徐兆壽安排了兩處關于“天”的描述,一處是“阿拉善的天”,另一處是“祁連山的天”。關于“阿拉善的天”的言說是對《狼圖騰》中“騰格里崇拜”的回應。而在后來關于“祁連山的天”的言說中徐兆壽則將“天下”及其“界外”之地聯系起來。“祁連”是匈奴語“天”的意思,祁連山則是“天之山”,也被稱為“騰格里大阪”。根據蒙古騰格里信仰,“天”是生命的給予者,而河西居民則出于對水及水神的崇拜,認為祁連山是神山與母親山;在“天的那邊”即祁連山那邊,而“我”打算先去張掖、然后過扁都口而祁連縣。祁連縣在祁連山腹地,那么出了“祁連山”就進入蒙古高原及青藏高原,幾經輾轉最后又回到“騰格里”懷抱中,回到“天或自然本身”渾樸圓一中。換言之,“天下無外”可能源自對于“天”的去倫理化或去政治化。“不管是儒家對‘天的敬畏還是道家對于‘天的效法,‘天基本上都被人格化和倫理化,自然的‘天不復存在,而作為自然一部分的人也在天的倫理化過程中隨之滅失。在儒家那里……人被嵌入禮制社會的等級秩序中,并在社會秩序中才有了所謂人格,而這樣的‘人,往往又是一個等級或地位的稱謂,不是一個自然人的表達。”[1]“自然人”覺悟到自然規律,進而有可能在超越種族或文化差異過程中促進“新文明空間”生成。而“新文明空間”中的天下屬于去倫理化“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共享與共建”天下,是基于騰格里信仰“天人合一”內涵而萬物共生的“生命共同體”。這種“生命共同體”視野使《荒原問道》對“天下無外”詩化過程展現出一種“文化人類學視野”,這一點被呈現于黑子詩歌《質問》中:
上帝,亞伯拉罕的主/我在約旦河畔尋找著你/我想問幾個問題/那應許之地……可曾是我的故鄉……尊敬的穆罕默德的主啊/如果生命只是為了延續/如果活著只是為了接受/如果一切都不能自主……生命還有什么意義/那么,“我”在哪里……洞悉秋毫變化的釋迦佛祖……生命若不被感知,生命可曾存在……生命若只需要空虛,只需要靜守/那么,是誰創造了這樣煩惱的生命……逆來順受的老子,恍惚中的先知/我也有個問題問你/道是何物……你說,是非對錯都在變化之中/那么,善也就是惡,惡也就是善/可為什么痛苦沒有變成幸福?[2]
這是一種關于“天下—生命共同體”可能性的追問,只是分屬人類的不同群體是否有可能超越自身有限視野而走向對話,從而為生成人類社會“新文明空間”予以奠基,這就需不同人群間關系協調及人與自然關系協調。成功協調需要一種超越性視野,《荒原問道》結尾時,老知識分子夏木繼續返回荒原,年輕教授則坐飛機去希臘做孔子學院中方院長,這就許諾了一種協調姿態。因為問題關鍵不在于協調是否可能成功,而在于因為意識到問題而為協調之展開所做的努力,因此“天下—生命共同體”的展望還是可預期的。
〔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學共同體專項課題“共同體場域下中國國家邊疆治理文化要素關系研究”(2022GTT04)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車鳳成:北方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劉宏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