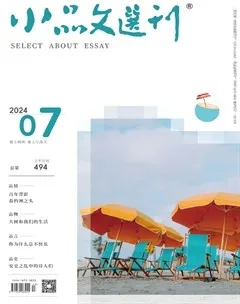我的創作生活回顧
郁達夫
一個人活在世上,生了兩只腳,天天不知不覺地走來走去,走的路真不知有多少。你若不細想則已,你若回頭來細想一想,則你所已經走過了的路線,和將來不得不走的路線,實在是最自然,同時也是最復雜,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面前的小小的一條路,你轉彎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輩子也走不了。有時候你以為是沒有路了,然而幾個圈圍一打,則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今天的路,是昨天的續,明天的路,一定又是今天的延長。
約而言之,我們所走的路,是繼續我們父祖的足跡,而將來我們的子孫所走之路,又是和我們的在一條延長線上的。
外國人說,“各條路都引到羅馬去”。然而到了羅馬之后,或是換一條路換一個方向走去;或是循原路而回。各人的前面,仍舊是有路的,羅馬決不是人生行路的止境。所以我們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它接合起來,連成了一條直線來回頭一看,實在是可以使人驚駭的一件事情。
路是如此,我們的心境行動,也是如此,你若把過去的一切,平鋪起來,回頭一看,自家也要駭一跳。因為自家以為這樣平庸的一個過去,回顧起來,也有那么些個曲折,那么些個長度。
我在過去的創作生活,本來是不自覺的。平時為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于無聊之際,拿起筆來寫寫。不知不覺的五六年間,總計起來,也居然積寫了五六十萬字。
兩年前頭,應了朋友之請,想把三十歲以前做的東西,匯集在一處,出一本全集。后來為饑寒所驅使,乞食四方,車無停轍,這事情也就擱起。
去年冬天,從廣州回到了上海,什么事情也不干,偶爾一檢,將散佚的作品先檢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沉淪”“蔦蘿”兩集,修改了一下,訂成了一本“雞肋”。現在又把上兩集所未錄的稿子修葺成功,編成了這一本“過去”。
對于全集出書的意見,和各集寫成當時的心境環境,都已在上舉兩集的頭上說過了,現在我只想把自己的“如何的和小說發生關系”,“如何的動起筆來”,又“對于創作,有如何的一種成見”等等,來亂談一下。
我在小學、中學念書的時候,是一個品行方正的模范學生。學校的功課,做得很勤。空下來的時候,只讀讀四史和唐詩古文,當時正在流行的《禮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說和林畏廬的翻譯說部,一本也沒有讀過。只有那年正在小學校畢業的暑假里,家里的一只禁閱書箱開放了,我從那只箱里,拿出了兩部書來,一部是《石頭記》,一部是《六才子》。
暑假以后,進了中學校,禮拜天的午后,我老到當時舊書鋪很多的梅花碑去散步。有一天在一家舊書鋪里買了一部《西湖佳話》和一部《花月痕》。這兩部書,是我有意看中國小說的時候,和我相接觸的最初的兩部小說。這一年是宣統二年,我在杭州的第一中學里讀書。
第二年武昌革命軍起了事,我于暑假中回到故鄉,秋季開學的時候,省立各學校,都因為時局關系,關門停學,我就改入了一個教會學校。那時候的教會學校程度很低,我于功課之外,有許多閑暇,于是就去買了些浪漫的曲本來看,記得《桃花扇》和《燕子箋》,是我當時最愛讀的兩本戲曲。
這一年的九月里去國,到日本之后,拚命的用功補習,于半年之中,把中學校的課程全部修完。
翌年三月,是我十八歲的春天,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這一年的功課雖則很緊,但我在課余之暇,也居然讀了兩本俄國杜兒葛納夫的英譯小說,一本是《初戀》,一本是《春潮》。
和西洋文學的接觸開始了,以后就急轉直下,從杜兒葛納夫到托爾斯泰,從托爾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更從俄國作家,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后來甚至于弄得把學校的功課丟開,專在旅館里讀當時流行的所謂軟文學作品。
在高等學校里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
后來進了東京的帝大,這讀小說之癖,也終于改不過來。就是現在,于吃飯做事之外,坐下來讀的,也以小說為最多。
這是我和西洋小說發生關系以來的大概情形。在高等學校的神經病時代,說不定也因為讀俄國小說過多,致受了一點壞的影響。
至于我的創作,在《沉淪》以前,的確沒有做過什么可以記述的東西。若硬的要說出來,那么我在去國之先,曾經做過一篇模仿《西湖佳話》的敘事詩。在高等學校時代,曾經做過一篇記一個留學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戀愛的故事。
這兩篇東西,原稿當然早已不在,就是篇中的情節,現在也已經想不出來了。我的真正的創作生活,還是于《沉淪》發表以后起的。
寫《沉淪》各篇的時候,我已在東京的帝大經濟學部里了。那時候生活程度很低,學校的功課很寬,每天于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館里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愿意用功,誰也想不到將來會以小說吃飯。所以《沉淪》里的三篇小說,完全是游戲筆墨,既無真生命在內,也不曾加以推敲,經過磨琢的。
記得《沉淪》那一篇東西寫好之后,曾給幾位當時在東京的朋友看過,他們讀了,非但沒有什么感想,并且背后頭還在笑我說:“這一種東西,將來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國哪里有這一種體裁?”
因為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混亂得很,適之他們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過博得一小部分的學生的同情而已,大家決不想到變遷會這樣的快的。
后來《沉淪》出了書,引起了許多議論。一九二二年回國以后,另外也找不到職業,于是做小說賣文章的自覺意識,方才有點抬起頭來了。接著就是《創造》周報、季刊等的發行。這中間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
一九二三的一年,總算是我的最高產的一年,在這一年之內,做的長短小說和議論雜文,總有四十來篇。
這一年的九月,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為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里雖感到了許多苦悶焦躁,然而作品終究不多。
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這一年在武昌大學里教書,看了不少的陰謀詭計,讀了不少的線裝書籍,結果終因為武昌的惡濁空氣壓人太重,就匆匆的走了。
自我從事于創作以來,像這一年那么的心境惡劣的經驗,還沒有過。在這一年中,感到了許多幻滅,引起了許多疑心,我以為以后我的創作力將永久地消失了。
后來回到上海來小住,閑時也上從前住過的地方去走走,一種懷舊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將我的創作欲喚起。一直到現在止,雖則這中間,也曾南去廣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來做過偉大的東西,但自家想想,今后仿佛還能夠奮斗,還能夠重新回復一九二三年當時的元氣的樣子。
至于我的對于創作的態度,說出來,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一句話,是千真萬真的。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描寫,無論你客觀到怎么樣一個地步,若真的純客觀的態度,純客觀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藝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滅了。
左拉的文章,若是純客觀的描寫的標本,那么他著的小說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又豈不是同他一樣的么?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豈不是也和他一樣的嗎?
所以我說,作家的個性,是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里頭保留著的。作家既有了這一種強的個性,他只要能夠修養,就可以成為一個有力的作家。修養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己的體驗。
美國有一位有錢的太太,因為她兒子想做一個小說家(她兒子是曾在哈佛大學文科畢業的),有一次寫信去問毛姆,要如何才可以使她的兒子成功。毛姆回答她說:“給他兩千塊金洋錢一年,由他去鬼混去!”
我覺得這就是作家要尊重自己一己的體驗的證明。
關于這一層,我也和一位新進作家討論過好幾次。我覺得沒有這一宗經驗的人,決不能憑空捏造,做關于這一宗事情的小說。所以我主張,無產階級的文學,非要由無產階級自身來創造不可。
他反駁我說:“那么許多大文豪的小說里,有殺人做賊的事情描寫在那里,難道他們真的去殺了人做了賊了么?”
我覺得他這一句話,仍舊是駁我不倒。因為那些大文豪的小說里所描寫的殺人做賊,只是由我們這些和作家一樣的也無殺人做賊的經驗的人看起來有趣而已,若果真教殺人者做賊者看起來,恐怕他們不但不能感動,或者也許要笑作家的淺薄哩!
所以我對于創作,抱的是這一種態度,起初就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將來大約也是不會變的。我覺得作者的生活,應該和作者的藝術緊抱在一塊,作品里的individuality是決不能喪失的。
若有人以為這一種見解是錯的,那么請他指出證據來,或者請他自己做出幾篇可以證明他的主張的作品來,那更是我所喜歡的了。
選自《達夫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