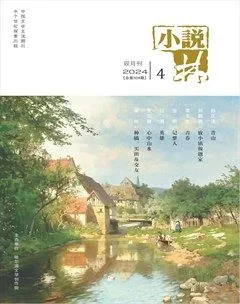找出一個線頭,織成一部小說
劉鵬艷
最初蹦出我腦海的,只是一個題目。我寫小說從來信馬由韁,如同我小時候寫作文從來不打草稿,我相信好的文章是自己生長出來的,規劃它或者規范它,都不自然。一粒種子撒下去,它長它的,你滿心歡喜地看著它破土而出,長成花,長成樹,長成什么樣子都好,就算是矮小的多肉又怎么樣呢?我也不大考慮結構,結構長在它的身體里。有時候它甚至不需要結構,比如這篇小說,我相信勻停的結構只會肢解它的完整性。寫出來一看,它正是昆德拉所說的那種氣質模糊的小說,而我喜歡把它稱為東拉西扯、言不及義的小說。
就像殺豬各有各的殺法,寫小說也是各人各法,有的詼諧,有的正經,有的細膩,有的粗獷,有的先鋒,有的傳統,結果當然是各花入各眼,頂好大家都找到自己舒服的寫作方式,并且遇到心心相印的讀者,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小鎮做題家”是一個很有趣的群體,在我讀書的年代,它大抵是勤勉和奮斗的代名詞。那時候沒有遍地開花的補習班,想考出好成績,唯一的辦法是看書和刷題。當然,天才除外。無論什么年代,少數天才是不用站在起跑線上的,但凡對起跑線是否“公平”斤斤計較的人,必然平庸。大多數人都認為,高考雖然未必絕對公平,卻是目前最公平的選拔人才的機制,多少人通過高考改變了命運,實現了階層的晉升甚至躍遷,因此它在一定時期內是不可動搖的基本政策。我無意挑戰公眾的認知,不過我想表達的是,即使通過高考而獲益的人,他們也未必感到滿足。因為對于命運,所有人都莫衷一是。
當然這并非小說的主題。一部小說,擁有一個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主題,我以為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那很容易寫成一部報告文學。我喜歡多義的小說,喜歡復調的敘事,喜歡豐富和充沛,喜歡謎語和懸念,生長性一直是我追求的藝術品質。
這部小說中的主角沒有名字,他,她,他們,已經足夠了,還能找出比這更有代表性的名字來代表那個時代的那個群體嗎?我想我不能。他和她是幸運的,他和她又有那么一些不滿足。從世俗的層面看,這種不滿足來自于人生的參差,可是從更為幽深的角度來看,真正的不滿足來自于我們與來處的割裂,以及不識歸途的浩蕩遺憾。
神話是文學創作的重要來源之一,那些遙遠先民對于世界的樸素理解,有時候也會讓具有現代意識的我們感到燒腦。小說里的鍋店子,真實地存在于我的家鄉,我從小聽父母說鍋店子的故事,明知它是假的,卻有揮之不去的影響力。它經過一部分虛構以后,變得更加生動和富有趣味性,我不確定是我帶有生活經驗的創作賦予了它的生長,還是它本身具有給我的生活進行賦能的生長性,總之那遙遠的民間傳說如此頑強地生長著,經年不衰,直至有一天長成了一篇任性的小說。我承認,神話中的主題和象征都被我蓄意篡改了,借以傳遞更為深邃的意義和情感。在此之前,神話是神話,小說是小說;在此之后,小說就是神話,神話就是小說。
由于神話被重新解讀和重構是創作的應有之義,我捏造故事時如有神助。那個做題的小鎮青年和我在精神上有相通之處,卻也不盡相同,他更老實一點兒,而我喜歡耍花槍,把他想不明白的事情用一種荒誕的方式表述出來,希望在潦草的原型推演中得到某種神啟。結果,我也還沒想明白——這大抵是小說最有意義的地方,它的生長,最終使我獲得生長,而這永恒的生長無始無終。
想到父母給我講的故事,心中會覺得溫暖,那種口口相傳的溫度,比文字更親切。現在我們給孩子講故事,再沒有那種代代相傳的地域文化色彩,現代城市的流動性和融合性使兒童更容易接受普適性的文化,就像我們習慣了普通話之后,再也無法流暢地說出家鄉話。每當我回到故鄉,都覺得自己再也無法融入那個曾經孕育過我的地方。我看著它,看著那些依然在它的土地上熱火朝天地哭著、笑著、生活著的人們,總有一種淡淡的憂傷和遺憾。
很難說哪種故事,或者說哪種講故事的方法更好一些,世間之道講究的是法無定法,無論哪一種方法,為求更廣泛地傳播總要便宜行事。在我的寫作圖示中,先找到一根線頭,由此生發,自由地編織一篇小說,這是最舒服也是最容易成功的方法。當然,我對“成功”的定義,門檻很低,有可能引發其他較為嚴肅的寫作者的質疑,他們兢兢業業、精益求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喜歡反復修繕自己的作品。我尊重他們的寫作方法,但我委實是一個懶惰的人,一旦寫完一篇小說,復盤的時候最多進行修辭上的潤色,再就是改改錯別字。我喜歡它自由生長的過程,也就允許它最終長成自己的樣子,就像一個小孩子,你生養他,看他長大,但是沒有辦法修改他。
《致小鎮做題家》這篇小說其實也書寫了成長,一個人的成長,以及一代人的成長,這種成長統統是不可逆的,倒回去,重改,不可能。在我看來,接受人生的這種內在一致性,尊重它的生長邏輯,能夠讓我們獲得心靈的解脫和超越。一生一次的成長,那么難,那么痛,那么深情,那么溫暖,回望舊時來路,已然草木成行,不必后悔沒有仔細地修剪過它們,它們正是你努力生長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