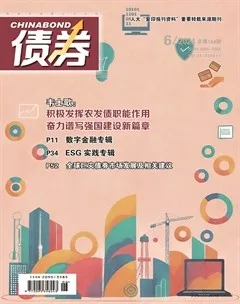全球巨災債券市場發展及相關建議
摘要:近年來,全球巨災債券發展迅速,已成為巨災風險分散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巨災保險市場、服務國計民生已上升為國家戰略,發展巨災債券市場具有促進保險市場和資本市場發展的雙重積極效果和戰略意義。建議破除制度障礙,加快培育我國巨災債券市場,促進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良性互動,提升巨災保險的風險保障功能。
關鍵詞:巨災債券 特殊目的保險公司 巨災風險模型
加快巨災債券市場發展,是貫徹落實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關于加快巨災保險保障體系建設的重要舉措,是落實國務院《關于加強監管防范風險推動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若干意見》的關鍵手段,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體現。但受法律制度尚未突破等因素約束,目前我國境內仍不能發行巨災債券,無法引入資本市場資金“活水”支持巨災保險市場發展,也未能給投資者提供新的投資品種,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資本市場的活躍發展。加快培育我國巨災債券市場,有助于實現保險市場與債券市場良性互動,提升巨災保險的風險保障功能。
巨災債券簡介
(一)巨災債券的產生背景
一是傳統再保險市場保障能力不足。20世紀90年代初期發生在美國的安德魯颶風和北里奇地震,使世界63家財產意外險公司破產,巨災再保險供不應求,再保險費率從1991年到1994年上升了一倍多,傳統再保險市場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在此背景下,業內人士開始將目光轉向資金實力雄厚的資本市場,希望通過資本市場為巨災風險提供充足資金保障,找到傳統再保險的替代品或補充方式,達到擴大保險資金來源、轉移和分散巨災風險的目的。
二是金融市場創新。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金融管制放松和金融自由化浪潮涌向保險市場并不斷深化,從資產業務證券化向負債業務證券化拓展,由此催生了巨災風險證券化市場。巨災風險證券化是保險公司負債證券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主要思路是通過發行收益與特定巨災損失相聯結的債券,以資本市場投資者代替傳統風險承擔者(如再保險公司),將保險風險轉移到資本市場。這不僅引發了一場傳統再保險經營方式的變革,也推動資本市場誕生了基于保險風險的金融創新工具,被稱為“保險風險證券化”。
三是巨災風險管理數字化發展。巨災債券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全球巨災風險管理數字化和智能化發展。美國等發達保險市場不斷加快災害數據積累與共享,實現災害數據資產的有效開放利用。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美國出現了RMS、AIR等全球知名的巨災風險模型,被全球投資者公認為巨災債券標的風險評估、定價和管理的通行標尺,有力支持了巨災風險向全球資本市場轉移。
(二)巨災債券的運行機制與要素
1.巨災債券的發行與管理機制
一般而言,有巨災風險分保需求的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政府部門、實體企業等作為巨災債券發行人,委托中介機構設立一家特殊目的保險公司(SPI,也被稱為特殊目的實體SPE、特殊目的工具SPRV),由該SPI發行收益與指定巨災損失相聯結的債券,將保險公司或再保險公司承擔的部分巨災風險轉移給資本市場的債券投資者。
巨災債券觸發條件包括SPI的實際損失、巨災風險模型計算得出的損失、獨立機構發布的行業損失指數、巨災事件的物理參數(地震震級、風暴等級等)等達到約定數值。如未達到觸發條件,債券投資者將獲得本金及債券利息,反之則可能無法獲得利息甚至損失本金,以此補償發起人的巨災賠付支出(見圖1)。
2.巨災債券的發行要素和參與主體
一是巨災債券的發行人與投資者。全球大約有數百家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主權國家政府、超主權國際機構、實體企業及金融機構參與巨災債券的發行、交易和管理,巨災債券已經成為保險風險證券化的成功范例。
二是發行利率。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巨災風險預期損失率(Expected Loss)、無風險利率(Collateral Yield)和風險加成(Insurance Risk Spread)。以美國市場為例,巨災風險預期損失率一般結合災害歷史發生情況,由巨災風險模型進行預測;無風險利率由美國國債市場決定;風險加成是債券投資者與發行人結合同期資本市場流動性、巨災保險承保周期等情況談判協商確定的。
三是發行期限。一般由自然災害發生周期決定。據知名巨災債券數據庫ARTEMIS統計,期限為3~4年的巨災債券占比最大。截至2023年末,3~4年期債券占全部巨災債券發行額的51%,4~5年期占比在27%左右。
四是發行和交易場所。巨災債券可以在交易所進行公開發行和交易,也可以以私募方式定向發行和交易。
五是服務巨災債券發行的建模公司。巨災債券的成功發行主要依賴風險建模公司對巨災風險損失的預期評估。據ARTEMIS統計,目前存量巨災債券中,使用AIR Worldwide模型的巨災債券遙遙領先,存量規模約360億美元;使用RMS模型的存量巨災債券排名第二,存量規模約60億美元;使用EQECAT模型的存量巨災債券排名第三,存量規模約20億美元。
六是巨災債券承銷商。據ARTEMIS統計,怡安證券(AON Securities)拔得頭籌,承銷的存量巨災債券發行規模約230億美元。位列第二、第三位的分別是GC證券(GC Securities)和瑞士再保險資本市場解決方案公司,承銷的存量巨災債券發行規模分別約為170億美元、100億美元。
全球巨災債券市場發展現狀
經過30多年的發展,保險連接證券(包括巨災債券、巨災互換、巨災期權、應急資本、行業損失擔保、壽險債券、基準風險交易等產品)市場發展迅猛,其中交易最為活躍和最具代表性的是巨災債券市場。
(一)巨災債券發行規模持續上升
近年來,尤其是在2017年美國三大颶風哈維、艾爾瑪和瑪麗亞造成保險行業巨額資本損失后,全球巨災債券發行規模加速上升。據ARTEMIS統計,2016年全球發行巨災債券37筆、67億美元,2023年共發行95筆、164億美元,2024年前5個月已發行50個項目、117億美元。1996年1月至2024年4月,全球累計發行巨災債券約1700億美元。
(二)巨災債券的投資收益較高
巨災債券的標的是巨災風險,與其他主要金融資產的相關性較低,整體投資收益受金融市場周期影響較小,因而能夠有效提升投資組合多樣化并降低總體投資風險,成為投資機構追捧的對象。據ARTEMIS統計,2002—2023年,巨災債券的年均投資回報率為7.1%,高于市場大部分金融資產收益(見圖2)。
(三)有力分擔自然災害保險損失
從全球范圍看,自然災害造成的全球保險損失目前年均在1100億美元左右,巨災債券存續額已接近保險損失的一半。巨災債券市場已成為發達國家巨災風險分散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保障對象是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的自然災害(見圖3)。
境內發展巨災債券市場具有特殊意義
發展巨災債券市場有利于解決再保險公司在承保巨災保險時尤其是大災過后的資本不足問題,是利用市場機制實現巨災保險分散的重要解決方案,對于我國巨災保險市場乃至財政金融體系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減輕財政補貼負擔
當前,我國巨災保險市場發展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為投保人提供保費補貼,甚至由財政部門全額采購巨災保險服務,財政面臨較大負擔。發行巨災債券屬于市場化解決方案,能夠將巨災風險轉移至資本市場,有利于減輕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壓力。例如,在美國加州地震局管理的加州地震保險計劃中,通過發行巨災債券獲得的活動保障能力占該計劃總保障能力的24%以上,成為巨災債券運用非常成熟的案例。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下屬的國家洪水保險計劃、日本的地震保險計劃,均發行巨災債券向全球投資者募集資金,這是其轉移風險的重要手段。
(二)促進巨災風險轉移,保障保險市場安全
傳統再保險市場是保險公司承擔巨災風險損失的第一道屏障,但面臨承保能力不足的突出問題。尤其是在大災之后,全球再保險市場主體主動收縮承保能力,大幅抬升巨災風險承保價格,導致保險公司無法購買到價格合理、供給充足的再保險保障。發展巨災債券市場,有利于解決保險制度在跨期積累資本和分散風險等方面能力不足的內在缺陷,調劑巨災再保險承保能力供給,為政策性巨災保險項目的多層次風險分散增加一項重要且廣闊的資本市場通路,因此成為很多發達金融市場建設巨災保險市場的重要一環。
(三)促進與全球標準接軌,引領我國保險市場高質量發展
在巨災保險市場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國面臨保險市場主體資本實力與承保能力不足,災害及保險賠付數據基礎不完善、標準不統一,以及巨災風險模型不夠成熟等問題。運用國際通行標準和操作模式發展巨災債券市場,有利于解決上述問題,實現巨災保險業務全鏈條與全球再保險市場、國際巨災債券市場的接軌,推動我國巨災保險市場進入更高發展階段。
(四)有利于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再保險中心
發展巨災債券市場,為尋求與傳統金融產品低關聯度的投資者增加了選擇。從國際視野看,目前包括巨災債券在內的保險連接證券發行量中,亞洲占比僅為2%,亞洲巨災債券市場發展潛力巨大。從對外開放戰略層面看,促進我國巨災債券市場發展,有利于吸引國內外發行人、投資者、證券服務機構聚集上海等金融開放前沿城市,培育聚焦保險業務的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助力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再保險中心。
從國際經驗來看,傳統再保險中心(如美國、英國、百慕大、新加坡及我國香港地區等)均鼓勵在本地發行巨災債券,形成與本地金融中心、保險中心相得益彰、相互促進的良好局面。以我國香港地區為例,2021年生效的《保險業條例(2020修正案)》為保險公司在港發行巨災債券提供了法律基礎。該修正案第133條規定,滿足相關條件的主體可在香港申請設立特定目的保險公司、經營特殊目的業務(SPB)。為吸引巨災債券發行人,香港特區政府還推出了債券發行成本補助計劃。截至2024年4月末,香港地區已成功發行5筆全球性巨災債券(見表1)。
發展境內巨災債券市場面臨的問題及建議
(一)面臨的主要問題
1.尚需法律和監管支持
完備的法律法規和有效的監管是促進巨災債券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目前涉及巨災債券的法律基礎、監管框架和機制尚不完善。例如,依據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設立保險公司需滿足最低2億元注冊資本的要求。而發行巨災債券的SPI資本金一般為象征性的1元,在債券存續期結束后SPI即注銷,所承擔的功能與普通保險公司有很大區別。目前,我國法律在SPI設立方面尚缺乏相關規定,這成為巨災債券在境內發行的主要障礙。此外,對SPI、巨災債券發行和交易、巨災債券額度等方面的監管分工尚未明確,這是境內部分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尋求在境外發行巨災債券的主要原因。巨災債券的稅務及會計處理問題尚無定論,阻礙了債券的發行和投資者交易。同時,價格透明度對于二級市場交易至關重要,巨災債券市場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和投資者保護不足問題也需要加以解決。
2.災害數據化、數字化建設相對滯后
一是我國災害數字科技水平有待提升。不同于傳統精算保險模式,巨災風險計量對致災因子、承災體和歷史災害數據高度依賴。目前,我國保險業災害數據可得性弱,災害數據與保險的結合度低。對數據敏感性的擔憂及缺乏數據社會化共享服務機制,使得保險業僅能通過項目合作或市場化采購等方式獲取加工后的數據,數據質量、更新頻次、采購成本等均不能滿足巨災風險量化模型建設需要,無法建立完備的巨災風險數據庫,制約了巨災風險模型的開發和產品合理定價,導致在向國際市場分保時難以獲得境外機構的認可。另外,我國還需要建立可靠的災害監測基礎設施,搭建長周期、質量可靠的數據庫,以有利于開發更受國際投資者歡迎的參數觸發型巨災債券產品。
二是巨災風險模型仍需加快迭代升級。巨災保險發展進入災害數據資產化、智能化階段,巨災風險模型已被證明是巨災債券風險評估、定價和管理的寶貴工具。但國際上現有的幾大巨災風險模型主要適用于美國或歐洲等成熟保險市場,在模擬我國自然災害損失時,受限于數據可用性和模型質量等,缺乏客觀性和準確性。目前,中再巨災風險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率先研發出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洪澇、臺風和地震3個主要巨災風險模型,服務國內保險損失計算、定價和債券設計,性能全面超越國際同類產品,打破了對RMS、AIR等傳統主流模型的依賴。但是,研發適合中國災害發生規律、保護中國災害數據安全的巨災風險模型依然任重道遠,在模型服務廣度、預測精度等方面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3.市場環境建設有待加強
從供給側看,我國巨災保險發展時間短,經驗不足,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及監管機構對于巨災債券這類新型金融工具尚需深刻認識與理解。從需求側看,國內資本市場不夠發達,投資者對巨災風險證券化產品不熟悉,巨災債券投資群體也處于培育之中。在巨災債券市場發展初期,往往是低標準化、低流動性的,容易出現交易量小、買賣價差大等問題,可能影響投資者的投資意愿和配置需求,對此也應著手準備預案。
(二)相關建議
1.加快完善我國巨災債券法律監管框架,完善巨災債券基礎設施體系
針對前述問題,建議在立法層面實現突破,如針對設立SPI進行規范,為建立巨災債券發行體系創造先決條件;在債券市場監管、保險業和證券業監管方面,針對巨災債券作出合理分工,加強協助。
服務商是巨災債券發行與交易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包括律師、重置代理人、承銷人、SPI管理人、信托管理人、支付銀行、賠款審核人、賠款準備金審核人等。建議加快國內相關行業針對巨災債券業務的實踐培養,打造完備的服務生態體系。推出發行費用補助制度,吸引亞洲地區乃至國際巨災債券在上海國際再保險交易中心
發行。
2.加快巨災保險市場建設,完善巨災風險數據基礎,推動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巨災風險模型迭代升級
一是持續提升自然災害數據監測、搜集、整理與分析能力,采用先進監測技術,實現更密集的地理覆蓋范圍,提出可靠的維護計劃,確保自然災害數據質量。
二是建議災害管理部門在確保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向保險業開放災害普查數據庫,共享各類災害數據。
三是在已初步開發并商用我國巨災風險模型的基礎上,未來需要加快迭代升級步伐,有力支撐我國巨災債券市場高質量發展。
四是加快我國巨災保險市場建設,加強巨災保險產品、承保、理賠、統計口徑等體系建設,推動巨災保險運營管理各環節標準化運作,完善巨災風險分散機制,為巨災債券發行夯實發展基礎。
3.培育巨災債券投資者群體,提升巨災債券投資能力
對國內投資者而言,如何正確理解和投資巨災債券,需要一個教育過程。建議在推動金融業高水平雙向開放的進程中,適當鼓勵國內投資者對海外巨災債券進行試點投資,逐步培育國內投資者對巨災風險管理和巨災債券發行、交易較為熟悉的市場環境。(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在單位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