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漢普頓的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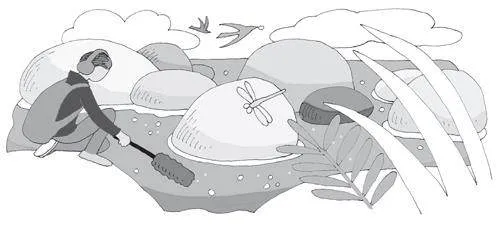
三月,江水清淺,卵石露出。有的露出來一點兒,有的露出來半個,有的全部露出,干干的就是河底了。有的長圓,有的渾圓,有的歪歪愣愣,或者更多歪歪愣愣的圓。有的扁圓,像個大月亮,如果含礦物質(zhì)就像黃月亮、紅月亮、青銅月亮。通常有鶴飛翔,不時地點水,點卵石,有時點著點著就落在石上。我一開始在客棧落地窗看到白鶴,下到江邊它們飛走了,后來發(fā)現(xiàn)一只留下來,我想那就是我。江水嘩嘩,不是滔滔,滔滔得是大石頭,嘩嘩聲主要是一道卵石攔水構(gòu)成的,不知是否人工,總之一線卵石高出水面。嘩嘩是總體聲音,走近甚至站在上面,就是分解的聲音了,正如小提琴不是一把,卵石也是許多,有自己的聲音。
蹲下打開手機錄音設(shè)備錄音,由遠及近,最終貼在瀑上,石頭有大小,浪花有高低,便幾乎貼在水上石頭上,錄出了參差,瑟音,豎琴、小提琴,甚至中提琴,沒有大提琴,因為沒有大石和倒木。這樣形容已粗疏了,實際要細微得多,無限的細,微積分一樣,芝諾悖論一樣:飛矢不動。耳朵變得異常靈敏,不敢說比水和陽光靈敏,當然更比不上鶴,但比以前的自己靈敏多了。赤腳慢慢到了下面的靜水灘石,水差不多就在滿目的石縫流。沒人動石頭,但是我動了,挪動一顆卵石,形成新的水流,就有了新的聲音,至少感覺是新的,我想如果我是鶴,大概會聽出低頻類似黑管的聲音。因為移動,我發(fā)現(xiàn)石下面的水比漫過石的聲音還要豐富得多,細微得多,在密密麻麻僅露一點的小石頭上簡直像鳥叫,嘁嘁喳喳,忘我地傾聽,不斷地挪動,甚至移動一個樹枝,一片滯木……
戈登·漢普頓是聲音生態(tài)學(xué)家,大自然錄音師,他讓我的耳朵獲得重生。在讀到他的書之前我想都沒想過挪動一塊石頭,聲音會有什么變化。10年前我知道了戈登·漢普頓,讀了他所著的《一平方英寸的寂靜》,這改變了我。因為有了戈登·漢普頓的耳朵,我才開始反思,“大”是我們的習(xí)慣,“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我們的習(xí)慣,而不細分、不注重小的事物,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聽到什么就是什么。其實,當我們關(guān)注那些細小之物時,世界會變得很不一樣。
(摘自《草原》2024年第3期,稻荷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