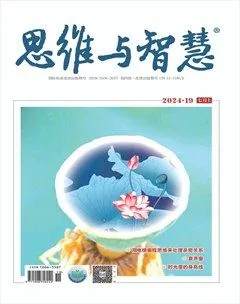古琴的情感
鄭學富
古琴,又稱瑤琴、玉琴、七弦琴,又有焦尾、綠綺等別稱,是中國傳統撥弦樂器,為中華傳統文化之瑰寶,有著3000多年的悠久歷史,被尊為“國樂之父”“圣人之器”。古代文人對琴情有獨鐘,將琴寫進詩文中,托物言志,以琴寓情,抒發情懷。
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第一首詩《國風·周南·關雎》就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詩句。琴瑟之好,流水知音,伯牙、鐘子期的故事流傳至今,琴臺被視為友誼的象征。馮夢龍的《警世通言》說,伯牙在子期死后吟唱道:“摔碎瑤琴鳳尾寒,子期不在對誰彈!春風滿面皆朋友,欲覓知音難上難。”李白感慨“鐘期久已沒,世上無知音”,表達了詩人知音難覓的孤寂落寞之情。董庭蘭是盛唐時的著名琴師,擅長演奏七弦琴,技藝十分高妙,但是曲高和寡。高適贈詩與他:“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后來,董庭蘭因琴藝出眾受到當朝宰相房琯的賞識,做了他的門客,常年跟隨左右。崔鈺有詩云:“七條弦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終憐得董庭蘭。”
古有“士無故不撤琴瑟”和“左琴右書”之說,琴位列“琴棋書畫”四藝之首,被文人視為高潔雅致的象征,他們以琴修身養性,以琴靜心悟道。薛能《送馮溫往河外》詩云:“琴劍事行裝,河關出北方。”琴與劍是古代文士的必備行裝。士大夫的居家擺設,常常是墻上一把龍泉寶劍,幾案上置放一把名貴古琴,既透露出主人的修養志向,也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征,劍膽琴心是也。白居易月夜泛舟,援琴吟唱:“七弦為益友,兩耳是知音。心靜聲即淡,其間無古今。”表達了詩人內心的平靜與淡泊,彰顯出對人生、對自然的熱愛和對現實世界的深刻思考。王維仕途坎坷,晚年隱居藍田輞川,寫下了《竹里館》:“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傳達出詩人清幽寧靜、高雅絕俗的境界。李白“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曾經豪情萬丈的李白把最鐘愛的酒與琴相融,唱出了晚年心中的那份孤獨與寂寞,更顯其一身仙風道骨,瀟灑不羈。劉禹錫的《陋室銘》:“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可見其淡泊的人生境界、高雅的生活情趣。
竹林七賢嵇康對古琴文化的超越,體現在他對古琴的偏愛與精神契合上。他在《琴賦》中云:“眾器之中,琴德最優。”“識音者稀,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表達了他對知音難覓的慨嘆,將古琴視作了他的知音。嵇康在臨刑前,坦然自若,從容不迫。他看了看太陽的影子,知道離行刑尚有一段時間,便向兄長嵇喜要來平時愛演奏的琴,在刑場上用生命的最后時刻彈奏一曲《廣陵散》,以慷慨激昂的旋律表達心志,讓后世的許多文人雅士留詩感懷。李白詩云:“誰傳廣陵散,但哭邙山骨。”陸游詩曰:“世間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文天祥感慨道:“萬里風沙知己盡,誰人會得廣陵音。”
南宋紹興八年(1138),正當岳飛率領大軍準備大舉收復中原,北上伐金之時,宋金“議和”,趙構命令岳飛不準與金兵作戰。岳飛的抗金大業不但受到趙構、秦檜君臣的忌恨迫害,張浚、楊沂中、劉光世等人也被阻撓,岳飛有曲高和寡、知音難遇之嘆。他在被強行召回的途中,憂傷地輕彈瑤琴,寫下了曲折哀婉、令人千古感嘆的詩詞《小重山》:“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壯志難酬的岳飛孤掌難鳴,滿腔的報國熱誠無處申說,將自己的心事寄托于琴弦,來表達憤懣、苦悶的心情,展現其沉郁悲愴之情懷。
蘇東坡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古琴聲聲,境由心造,古人通過彈奏古琴,表達恬逸、閑適、虛靜和幽遠的心境。無論是《高山流水》《梅花三弄》,還是《廣陵散》《滿江紅》,琴聲已經融入古代仁人志士的情感之中,賦予了詩詞幾多豪情。
(編輯 兔咪/圖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