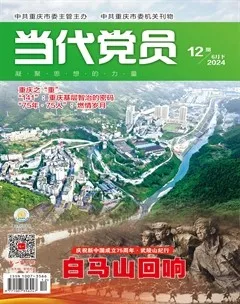踏遍青山 只為熱愛
陳一豪

現在的城市人很少見過山,真正的大山。
我說的當然不是某某自然景區,那種買一張門票便能享受的直進直出的旅游式體驗,那是有人的山,是供人觀賞的山。
我說的山,是花費九牛二虎之力,爬上某一座山峰,喘息甫定,舉目四望,卻看見遠方仍是重重疊疊的山影,在無聲地向你召喚。
群山疊嶂、懸崖峭壁,絕美風光、萬分寂寥,在重慶,有一群人面對的正是這種山。最近,我到重慶市開州區采訪了獲得2023年度“感動重慶十大人物” 特別獎的重慶雪寶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崖柏科研團隊。
之所以“特別”,是因為他們潛心攻關十幾年,扭轉了崖柏極度瀕危的狀態,更是因為這是一支了不起的隊伍。
團隊負責人楊泉是我的第一個采訪對象。與山打了半輩子交道的他,發須皆白。或許是雪寶山真有靈氣,他看起來倒真有幾分仙氣。
2002年,楊泉參與籌建雪寶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他認為,要有效保護好崖柏,就要精準掌握保護區內所有野生崖柏的生長情況,同時進行科研觀察,逐步破解崖柏的更多未解之謎。
為此,10個人的科研團隊逐步組建完成。除了楊泉,還有已在深山堅守10年以上的黃吉蘭、張光箭、周李萍,以及后來加入的鄔黎、朱志強、王雷、吳浩、蔡松余、邱宇華。
手扳巖、王家巖、駱駝峰……為了探尋崖柏,他們幾乎走遍了保護區每個角落。行走在懸崖峭壁,露宿在山澗野外,抓過毒蛇、對峙過黑熊。聽到這里,我覺得這個故事已有幾分傳奇色彩。
楊泉打斷了我。“讓你來一個星期可能你會覺得新鮮刺激,但如果是一個月,又或是一年呢?”楊泉的話讓我有些汗顏。此刻,看著他的白發和胡須,我感到一陣寂寥涌上心頭,那是理想信念與萬頃深山碰撞后留下的“傷痕”。
車上,忍受顛簸的同時,我聽著楊泉的科普宣傳。
一開始,崖柏扦插繁育用的是野生老樹枝條,但枝條生根寥寥無幾。事后分析原因,是老樹生命力太低。
后來,改用種子繁育成樹的枝條,但生長狀況也不理想。看來生根劑、消毒劑、營養劑等配比不能完全照搬其他扦插植物。
再后來,調整藥物配比,自配樹苗基質,這次居然成功了,扦插苗成活率達到25%。
一年又一年改進技術、總結經驗,2019年,該技術終于成型,扦插苗成活率超90%。
2020年起,保護區決定建設崖柏規模化繁育科研基地。在人員不足、資金缺乏的情況下,團隊成員全程參與、日夜奮戰,一年時間,出圃苗木達100萬株。
沒有人在意今天是工作日還是周末,因為從睜眼到閉眼,面對的全是工作,今天干不完的,明天接著干。家屬上山探親,看見隊員們深陷的眼窩和黝黑的皮膚,所有的家長里短瞬間只剩下心疼和關切。
這個團隊里,有在山林里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的老前輩,也有剛入行的年輕人,他們之前是城里娃、外鄉人……但在這里,他們全都一樣樸實、純粹。而這,都源于他們對自然的責任感,究其根本,這份責任感是對自然保護事業的熱愛,是對大山的熱愛。
車子在滿月鎮甘泉村路邊停下,我們沿著不足半米寬的生產便道往田野深處走去,幾個自動化實驗大棚呈現在眼前。
楊泉說,這是他精心挑選的地址,他們準備在這里大展拳腳,種上樺木、槭樹、連香樹等植物,當然,還有他們最珍惜的崖柏。
隊員們說,想讓崖柏走出雪寶山,到更多地方去。現在,崖柏已經去到了內蒙古大青山、云南高黎貢山保護區等8個地方開展遷地保護和適應性研究,目前情況很樂觀。他們更遠的夢想,是讓崖柏從珍稀瀕危物種名錄中除名。
夜幕四合、鳥雀歸巢,我們才匆匆下山。臨行前,楊泉神神秘秘地拿出一個小瓶子,向我介紹起來:這是他們自主研發、自購設備,利用廢棄崖柏枝條成功提取的崖柏精油,有極大的醫藥價值。“我研究了一輩子崖柏,但我感覺它還有許多未探明的知識。”楊泉興奮地說,“希望到你們下次來時,能看見漫山遍野的崖柏樹苗。”
看山一日,讀山數載。對于人類來說,山,絕不僅是供人觀賞的風景。每一座山,都是一部卷帙浩瀚的百科全書,承載著生態文明的價值。
今天,這群“山友”所做的,仿佛就是“育樹”。
這事平凡嗎?平凡。
做這平凡事偉大嗎?太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