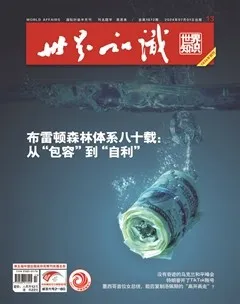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圖景與人民幣的國際化
張禮卿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
自1971年“尼克松沖擊”發生以來,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所謂的“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或“牙買加體系”時代。
后布雷頓森林體系至今已經運行50多年了,伴隨著美元與黃金的脫鉤,國際貨幣體系徹底進入信用本位時代。盡管“雙掛鉤”不復存在,但美元依然是全球儲備體系的中心。由于美國擁有高度發達和開放的金融市場,加上強大的網絡效應,美元作為主導性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沒有發生顯著變化,目前在全球儲備貨幣體系中的占比仍然接近60%。在信用本位時代,國際貨幣體系是否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政府債券的信用以及美國貨幣當局的貨幣供給狀況。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具有明顯的缺陷和不合理之處。從其50年的發展來看,美元的過度特權造成的全球金融動蕩影響了外圍國家的經濟金融穩定,使得全球經濟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受到質疑。這是因為,美國在根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實施貨幣政策時,常常對其他國家產生巨大的溢出效應。由于全球金融周期的助推,這種溢出效應嚴重影響了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和金融穩定。譬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和退出對新興市場經濟體造成巨大沖擊,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啟動的無限量化寬松政策引發全球流動性泛濫和通脹壓力的快速上升,2022年上半年開始的持續加息再次對全球經濟金融穩定(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產生顯著沖擊。
此外,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大量持有美元儲備資產,特別是大量持有低收益的美國國債,這意味著“窮國”以很低的投資回報率在向“富國”輸出資本,使得資本進一步向“富國”集中,從而影響了全球經濟資源分配的公平性。
改革的方案
過去幾十年間,為了克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國內外學者提出過不少改革方案,其中主要包括回歸國際金本位,創設單一世界貨幣、實施基于特別提款權(SDR)的超主權貨幣,實行改良的美元本位以及發展多元儲備貨幣體系等。
從歷史經驗可知,由于黃金的開采數量和速度遠遠跟不上國際貿易和投資將其作為媒介工具的現實需要,加上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無法利用信用創造來進行反周期調節,因此,回歸國際金本位的方案完全沒有可行性。近年來出現的一些建議,如比特幣本位、大宗產品本位制等,也因為同樣的原因不具有可行性。
單一世界貨幣和基于SDR的超主權方案比較理想,可以徹底解決特里芬難題帶來的內在不穩定性。這兩種方案曾經受到多位頂級國際經濟學者和政府官員的推崇,如美國著名學者理查德·庫珀、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等。不過,這兩種方案需要主要經濟體在政治上具有足夠的合作意愿。由于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擁有一票否決權,只要美國不贊成,超主權貨幣方案就不可能實現。而且,從技術上講,基于SDR的超主權方案存在嚴重局限,即直到目前為止,SDR使用范圍僅僅局限于IMF系統內部的官方清算,并沒有任何商業性的流通使用。

2024年6月12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維持在5.25%~5.50%之間不變。
然而,任何事務都不是絕對的。隨著國際競爭格局的變化,上述方案還是存在機會加以推進,而且不排除經過長期努力有實現的可能,近十多年來SDR被更加頻繁的分配和使用就說明了這一點。2009年,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IMF分配了2500億美元等值的SDR。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IMF再度分配了6500億美元等值的SDR。未來,在面臨全球流動性危機的時候,IMF或將繼續分配一定數額的SDR。經過長期努力,SDR有望成為多元儲備資產體系中一個逐漸重要的組成部分。
改良的美元本位方案是指,如果美國貨幣當局在實施貨幣政策時能夠變得足夠自律,并且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愿意盡量兼顧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金融情況,而其他國家也能盡量避免不當的財政貨幣政策,從而使全球范圍的國際收支失衡情況從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那么繼續實行以美元為中心的信用貨幣本位制度具有可行性。這一方案的支持者包括已故的著名國際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等。然而,要使美國和世界各國均實施比較自律的財政貨幣政策,需要相關國家實行高度合作和有效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這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比之下,多元儲備貨幣體系方案可能是較為可行的次佳方案。多元儲備貨幣體系是指由幾種貨幣共同承擔國際儲備貨幣的功能。這一體系的形成,是基于競爭的自然選擇,而不是出于大國共同的政治意愿。由于貨幣競爭的存在,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將會變得相對自律,因為如果某個儲備貨幣發行國出于國內經濟增長或穩定目標而過度擴張其貨幣發行,那么其貨幣勢必貶值,該幣種在全球儲備貨幣構成中的比重勢必下降,而其他儲備貨幣的比重勢必上升。同時,特里芬難題也會因為被多種儲備貨幣分擔而變得相對緩和。但該體系有可能帶來主要貨幣匯率之間頻繁的大幅波動,也需要通過加強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來予以應對。
多元儲備貨幣體系的形成將是一個長期過程。截至目前,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占比接近60%,歐元占20%,日元占5.35%,英鎊占4.97%,人民幣占2.9%。美元國際地位的衰落雖不可避免,但歐元、人民幣何時能成為與美元同等重要的貨幣,目前還難以判斷。展望未來,如果歐盟與中國能有效地增強各種有利因素,創造各種有利條件,那么多元儲備貨幣體系形成的步伐或將加快。
人民幣能否成為多元儲備貨幣體系的一極?
近年來,人民幣在SDR中的比重提升(目前已達到12.28%)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特別是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提升。但人民幣要想在未來10年至20年成為多元儲備貨幣體系中的一極,還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人民幣的國際化必須依托于我國經濟的穩定和金融體系的開放。
第一,努力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對于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當前,由于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美國及其盟國對我國的技術封鎖和全球供應鏈轉移等因素,在短期內我國經濟面臨不少挑戰。而且,由于人口加速老齡化、技術進步緩慢、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國際經濟碎片化、地方債務風險顯著上升和民營企業投資信心不足等問題,我國經濟的長期增長面臨著更加嚴峻的考驗。為了應付可能發生的增長持續放緩,從而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持久的基礎性支撐,我國需要堅定地深化面向市場的經濟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不斷完善投資營商環境,特別是加強對民營企業家的產權和權益保護,通過更為廣泛和深入的結構性改革,讓市場活力得到充分發揮。
第二,加快技術進步,構建新的出口貿易優勢。
德國馬克和日元國際化的經驗均表明,保持出口貿易優勢對于貨幣國際化非常重要。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在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指引下,利用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成功地確立了全球最大貿易國的地位。不過,在人口紅利逐漸消退之后,我國需要加快技術進步,構建新的出口貿易優勢,以便繼續保持世界最大貿易國的地位。
第三,深化國內金融改革,加快完善市場化的金融體系。
一個具有高度流動性、規模足夠大和開放的政府債券市場,對于人民幣國際化極為重要。目前,我國的國債市場規模已居全球第三,但由于流動性不足等原因,仍然難以滿足外國投資者擁有高流動性和高安全性人民幣金融資產的需要。為此,應繼續擴大國債市場規模,豐富期限短、流動性強的品種,并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同時,還要不斷提升A股市場的定價能力和投融資效率,為外國投資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資本市場工具。要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增強其彈性,以便在更為開放的金融市場環境下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應加快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特別是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體系的建設,并繼續在具有潛力的國家和地區增設清算行。
第四,適當加快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同時加強宏觀審慎管理。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CED)提供的數據,盡管經歷了20多年的開放努力,但目前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度僅為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16% 。可以認為,如果沒有資本管制的繼續放松,沒有資本賬戶的進一步自由化,人民幣國際化很難再有顯著發展,甚至很難繼續前行。擴大開放必然會帶來金融穩定風險,需要進行有效管理。經過多年的探索,在管控跨境資本流動風險方面,我國已經積累了不少成功經驗。通過及時的技術調整,相關部門能夠有效防止跨境資本流動在短時間內的大進大出,從而實現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2021年11月15日,北京證券交易所正式鳴鐘開市,這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幕。
第五,加強國際經濟與金融合作,積極參加全球金融治理。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市場驅動過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促成各種經濟和金融條件的形成,從而實現間接推動。不過,通過加強國際經濟和金融合作,政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直接推動,如中國人民銀行促成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就是一種直接推動。在當前,中國政府可以通過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框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以及低收入國家減債和緩償進程,不斷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并利用“一帶一路”上的貿易和投資合作機會,逐漸提升中國在全球貨幣金融事務中的影響力,由此帶動人民幣國際化。
第六,繼續探索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領域使用的可行性。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探索數字貨幣的國家之一。2019年底,數字人民幣已相繼在深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和冬奧會場景啟動試點測試。2021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加入了國際清算銀行支持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這是推進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一項積極探索。未來,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領域的探索可以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一,在零售層(用于日常交易),數字人民幣將主要定位于服務在中國旅居的境外用戶,以滿足他們的普惠金融需求。其二,在批發層(用于銀行之間或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相關機構可繼續推動數字人民幣參與貨幣橋項目有關試驗。其三,以開放和包容方式探討制定法定數字貨幣標準和原則,在共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過程中,妥善應對各類風險挑戰。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