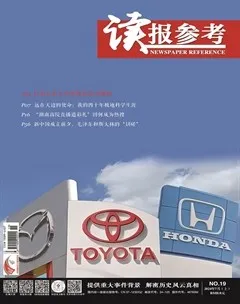在廟底溝遺址,尋找華夏的“華”
“廟底溝類型的影響力持續了1000多年,并與其他文化相互作用形成文化網,它們便是最初的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曾經這樣說道。
60多年前,廟底溝遺址重見天日
60多年前,為配合三門峽黃河水庫規劃和建設,國家成立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1953年的一天,考古學家安志敏率隊到河南陜縣(今河南省三門峽市陜州區)開展調查。當乘坐火車路過該地時,鐵道路溝兩壁露出的灰層及灰坑引起了他的注意。憑借專業人士的敏感,也就這一眼,讓深埋于地下6000余年的廟底溝遺址重見天日。
發現于1953年的廟底溝遺址,是新石器時代考古領域的重大突破,在考古學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001年,廟底溝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入選全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廟底溝遺址位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湖濱區,處于黃河支流青龍澗河下游左岸二級階地的前緣地帶,西北距黃河僅1公里左右。依托較為優越穩定的自然環境,廟底溝先民們長期安定地生活在陜、豫間的黃河峽谷地帶,創造出了輝煌的廟底溝文化。2021年10月17日起對外開放的廟底溝博物館,基于廟底溝文化和考古遺址的發掘,服從文物保護規劃的整體要求,盡力保持原有地形地貌特點。
廟底溝彩陶上的花瓣紋,或許就是華夏之“華”的由來
晨曦初照,記者走進廟底溝博物館,鏤空花飾的巨型穹頂在陽光下通透晶瑩,若幻若真。“博物館大廳穹頂的紋飾,來源于廟底溝時期的代表性紋飾——花瓣紋。”博物館講解員董婉容說。
距今6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期的典型代表,也是仰韶文化的成熟階段。彼時,農業生產已經較為成熟,社會復雜化程度加劇,出現并形成了區域中心聚落,彩陶技藝也得到較大發展。
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曾以精準形象、頗具詩意的“重瓣花朵”理論,來解讀中華文明綿延至今的起源密碼。他指出:“中原好比花心,是中國史前文化的中心。圍繞中心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是主體,主體部分涉及的山東、燕遼、甘青、江浙、湘鄂、巴蜀等文化區都好比內圈的花瓣。在內圈之外,還有外圈的花瓣,如閩臺、粵桂、滇、康藏、新疆、內蒙古、東北等文化區。這三重結構組成的花朵,每部分之間都緊緊相連、不能分離,具有文化上高度的向心力與凝聚力。”
廟底溝博物館的展覽便以嚴文明的“重瓣花朵”為理論依據,以歷史發展軸線的順序,展覽面積5473平方米,展出文物3344件(套),講述廟底溝文化“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發展歷程、文化面貌及影響。
“廟底溝時期的彩陶數量眾多,色彩艷麗,圖案繁縟,技術高超,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的。”董婉容說,廟底溝彩陶的母題紋樣中,最具特點的是旋紋和花瓣紋。“華夏彩陶到了仰韶時代的廟底溝文化時期,發展到頂峰,成為史前華夏文明進程中的里程碑。廟底溝文化彩陶上的花瓣紋,就是綻放在中原地區的‘中華文明之花。”
在古漢語里,“花”“華”同音,“華”的本義為“花”,金文中的“華”字就是花朵加上花蒂的樣子。不少學者認為,廟底溝彩陶上的花瓣紋,或許就是華夏之“華”的由來。
廟底溝博物館館長王宏民解釋,仰韶文化廟底溝時期的主要特點是彩陶,彩陶上多是花瓣紋,“華”字同“花”相通,周邊還有華山,所以,中華的“華”和華山的“華”,很可能就是從廟底溝文化起源的。
“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階段花紋以寫實為主,到了廟底溝階段是仰韶文化最繁榮的時期,紋飾逐漸抽象,說明了人類智慧的進步。”王宏民說。
文化意義上“最早中國”的形成
廟底溝文化中特有的文化因素——彩陶,對周邊地區產生了極大輻射,東到海濱,西達甘青,南抵江漢,北越河套的廣大地區,都發現了受其影響的彩陶,從而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彩陶時代。“在這一傳播過程中,能夠發現其中蘊含著明顯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也充分說明了在反映中華文明突出特性方面,廟底溝文化具有重要作用。”王宏民說。
廟底溝階段也是仰韶文化最有擴張力的時期。花瓣紋包括幾何紋,影響到中國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它不僅是中國史前第一次藝術浪潮,也標志著文化意義上“最早中國”的形成。如果說仰韶晚期逐漸進入了文明社會,那么,仰韶文化廟底溝時期正是文明社會形成的關鍵時期。
新中國第一份新石器時代考古報告《廟底溝與三里橋》中指出:“以廟底溝為代表的龍山文化遺存,確有它自己的特征。而且代表著一定的發展階段,很像是從仰韶到龍山的一種過渡階段。在分布上也相當廣泛,因此,我們暫稱它為廟底溝二期文化。”
廟底溝遺址的發現,實證了中華民族的祖先從遠古時代起,經過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直至商周,在黃河流域綿延不斷地發展并創造了高度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