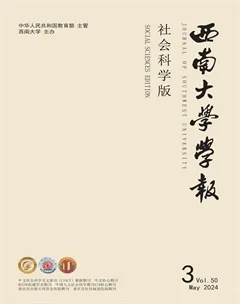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規則解析
DOI:10.13718/j.cnki.xdsk.2024.03.008
作者簡介:楊林,重慶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通訊作者:袁文全,重慶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機構養老發展的法治保障研究”(22BFX120),項目負責人:袁文全。
摘" 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認定、喪失及身份喪失后的權益保留,關系到農村居民的切身利益,科學的制度設計是引導鄉村善治、助推共同富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二次審議稿)》(以下簡稱《草案二次審議稿》)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定義及認定應以戶籍為基礎,但不宜強制要求成員的基本生活保障需以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財產提供,也不應把二者之間形成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作為成員身份定義的必要條件。喪失成員身份的規定中,可以用“戶籍+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類型劃分方式,把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等群體排除在組織成員之外。對于務工、經商、服役、就學等原因“暫時離開”的成員,其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等核心財產權益的保留時間不宜一概而論,可根據權益性質確定合理的保留期限。《草案二次審議稿》可通過細化、完善涉及成員身份的相關規定,保護農村居民合法權益,提升農村居民參與自我管理的積極性,促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規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鄉村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2;D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24)03-0096-11
一、問題的提出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將“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納入我國2035年發展的總體目標[1]。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2]。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應然目標,也是未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實然理想狀態,鄉村“三治”融合發展是實現上述目標的必由之路。基于上述邏輯順序的演進,可展示出鄉村治理實踐中村民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的決定作用。由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規則的重要性得以凸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直接關系到當事人能否享有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權、被征收征用土地補償費分配權等核心財產權益,關涉農民切身利益,是鄉村治理“三治融合”框架下自治、法治的基礎內容。“身份認定規則—獲取身份—享有權益—參與治理”四者之間的內在聯動邏輯關系明顯環環相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規則決定農業從業人員是否具有成員身份,獲得和保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才能獲取基于身份享有的上述各種身份權益和財產權益,而獲取權益的期待和實現則是調動成員參與鄉村自治、提高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內生驅動力。因此,成員身份的認定規則不但是鄉村治理法制化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還是全面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前提,也和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促進共同富裕緊密契合。
然而,鄉村治理法治化目前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規則”缺失或“現代法缺失”[3]。《草案二次審議稿》的公布及未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正式頒布,將從頂層制度設計上徹底解決上述問題,指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及鄉村治理法治化的推進,但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規則的討論及建議頗多,《草案二次審議稿》未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定義及身份認定標準起到定分止爭、統一指引的作用。成員身份的認定問題是基層治理、司法實踐和理論界研討所面臨的一個難題,學界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認定標準一直未形成有說服力的通說[4]。秦靜云認為農村集體成員身份認定需要堅持確保原有入社人員及其衍生人口的農村集體成員身份底線,授權農村集體成員決定其他類型人員是否獲得農村集體成員身份[5]。肖新喜更看重成員身份的社會保障性質,主張將強制性的社會保障標準與任意性集體接收標準相結合,以此規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確認標準[6]。吳昭軍建議在成員身份確認中引入動態系統論,列舉影響成員身份確認的因素,按照重要性進行排序,認為戶籍不宜成為當下乃至未來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主要標準,只能作為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婚姻關系之后的后順位考慮因素[7]。宋春龍呼吁成員資格界定的統一標準宜采用形式標準和實質標準相結合的形式,即在認定成員資格時將常住戶籍作為形式要件,將生活關聯度、是否盡義務等作為實質標準[8]。就司法實務而言,因法律未對集體成員資格的概念及其如何判定進行綜合全面的規定,給當前人民法院處理此類糾紛帶來了巨大困惑,各地法院針對此類案件在審判實務中的處理方式和認定標準不盡統一[9],或使司法裁判缺少法律依據,對司法裁判工作造成極大障礙[10]。河北高院在一些判決中認為,戶籍是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基礎,當事人具有所在集體經濟組織的戶籍,應依法取得該集體組織成員資格;遼寧一些法院在判決中以實際生活生產地為確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主要標準;四川部分法院裁判認為,確定是否具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關鍵在于當事人是否享有該集體經濟組織生產資料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上述情況代表了當下對身份認定規則研究的主流方向,即幾乎都是以法學抑或法經濟學角度為出發點,以身份認定規則對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影響為歸依,極少從鄉村治理角度出發闡明身份認定規則對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法治化現代化的作用和影響,使鄉村治理多重學科的闡釋邏輯有所缺失。此外,各地司法實務中對相關涉訟案由的不同裁判,對鄉村治理目標的穩定和諧也造成了一定影響。
本文旨在通過梳理當下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實務操作,進而剖析《草案二次審議稿》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定義及身份認定標準的缺憾,試圖證明《草案二次審議稿》定義要求成員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成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可能全面實現,成員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財產為基本生活保障的規定也有其非必要性,同時對成員身份喪失標準、部分成員身份喪失后保留其財產權益的規定展開探討,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提供參考與建議,其最終目的是期許在頂層法律制度的指引下,規范鄉村治理實踐,以完善法治提高鄉村自治能力,并以此能力投射農村德治領域,提高村民經營管理、民主決策、公益活動、社會服務的積極性,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要完善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讓農村既充滿活力又穩定有序”[11]。
二、地方制度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的類型化標準
及《草案二次審議稿》存在的不足
過去數十年來,在無頂層法律規范指引的情況下,各地出臺的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及指導性文件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認定辦法可謂多樣復雜、標準各異,甚至一地一策,地相鄰而法不同。具體而言,目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主要有單一戶籍標準、戶籍與年齡混合、戶籍與特定義務或特定身份相混合為標準等四種情況。
單一戶籍標準,即基本以戶籍作為確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唯一標準,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辦法》第八條規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人員,應當確認為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一)農村土地二輪承包時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且戶口一直在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村的;(二)父母雙方或者一方為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且戶口一直在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村的;(三)因合法的婚姻、收養關系,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村的;(四)根據國家有關政策,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村的。”通過梳理我國農民身份與擁有土地權利的歷史邏輯關系,會得出單一戶籍標準極具合理性的結論,但把戶籍作為確定集體成員身份單一標準的同時,應輔以規定激勵成員為組織盡到力所能及義務的措施,以及失去戶籍或身份后部分財產權益的保留辦法等細則,以此完善標準。
戶籍與年齡混合,即以擁有當地戶籍且年齡達到一定條件作為確定成員身份的標準,例如《湖北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凡戶籍在經濟合作社或經濟聯合社范圍內,年滿16周歲的農民,均為其戶籍所在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社員。”這里的“戶籍+年齡”方式略顯疏漏,弊端明顯,很可能會導致利益驅動下的富裕集體經濟組織的人口膨脹[12],也將未滿年齡要求的戶籍人員排除在外,剝奪其權益,實屬不公。
戶籍與特定義務混合,即以擁有當地戶籍且履行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義務作為標準,例如《廣東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規定》第十五條:“原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成員,戶口保留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規和組織章程規定義務的,屬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這里的“戶籍+特定義務”方式給無法履行義務的老弱病殘及離鄉打工、經商人員造成了獲得身份享受權益的困難,也有欠妥之處。
戶籍與特定身份相混合,即類型化分類社員種類,不符合所列類型之一的人員即不屬于村經濟合作社社員,例如《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第十七條規定:“戶籍在本村,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遵守村經濟合作社章程的農村居民,為本村經濟合作社社員:(一)開始實行農村雙層經營體制時原生產大隊成員;(二)父母雙方或者一方為本村經濟合作社社員的;(三)與本社社員有合法婚姻關系落戶的;(四)因社員依法收養落戶的;(五)政策性移民落戶的。”此處“戶籍+特定身份”方式主要針對歷史成員或社員的確認,而對嗣后繼受身份的規定中的某些條款反而弱化了對戶籍落地的要求。四川、黑龍江等地在省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條例》中沒有具體的認定標準,兩省都是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條例》中確定大致原則后讓縣級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區域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確認具體程序、標準的指導意見,以致下屬各市縣呈現更為多樣的認定標準。
2022年12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首次亮相并公開征求意見,其中有關成員身份定義及確認標準因關乎農民切身利益而尤為醒目。《草案》明確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定義、確認、加入、退出,以及確認成員爭議的救濟程序,總結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的實踐經驗,彌補了長期以來的立法空白。全國人大關于《草案》的說明中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制定對于鞏固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對于維護好廣大農民群眾根本利益、實現共同富裕等具有重要意義,是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中最為堅實重要的頂層制度設計,是法治化鄉村治理的首要參照。《草案》及《草案二次審議稿》在成員的定義、確認、退出規定中,雖參考了司法實踐和地方立法,但對于前文所列的紛繁多樣、多元復合的成員身份確認方法并無提煉統一、去弊留優的清晰指向,反而表現出對各地治理實務產生明顯路徑依賴的特征,此種路徑依賴并沒有妥適考慮到地方立法及基層治理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供給權威法律資源的渴望,以及該法優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獨特地位的任務,從而導致“急用先立,宜粗不宜細”的制度設計理念與現實脫節、制度供給對實務執行指引效果較差、實用主義功能較弱等問題。地方和農村基層如果在基于《草案二次審議稿》框架下自主決定成員的定義、確認、退出規定,勢必延續當前標準各異、復雜多樣的局面,使未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更符合實際”“更便于實施”及定分止爭的法律效果無法完全顯現,從而無法突出法治化鄉村治理所帶來的對農村社會和諧穩定局面的推動作用,故而對原則性存瑕、靈活性過強的《草案二次審議稿》相關內容還有較大的討論空間。
三、對《草案二次審議稿》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定義的解釋分析
《草案二次審議稿》關于組織成員的定義應成為相關問題的難題之解,決定地方立法及治理實務的演繹方向,農民對土地的必然依附及戶籍與身份的深度綁定,是確定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定義及身份認定標準的歷史邏輯基礎。對具有強烈身份屬性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所派生的財產權利的給予,以及解釋此領域的特別法人成員權制度及成員權利保護,都應以上述歷史邏輯為基礎。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定義一定要回望歷史、兼顧現實,公平公正、易于操作,呈現科學的法理和清晰的指向來對成員之定義及權利進行公示。
(一)以戶籍為基礎認定成員身份的合法性
隨著城鎮化、鄉村振興及共同富裕戰略的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帶給成員的財產收益日益突出,成員身份認定標準是決定所涉人員能否以特定身份在集體經濟組織內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前提和重要依據。因此,制定清晰明了、普遍認可的成員身份認定路徑指引,關乎農民權益保護和農村基層社會穩定。2014年我國推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試點區域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時標準各異,但各地不同規定之中無一例外地以成員戶籍作為重要參照條件甚至是必要條件。《草案二次審議稿》第十一條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定義為:“戶籍在或者曾經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成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財產為基本生活保障的農村居民。”對農村農民土地所有權制度變遷進行回顧,即可得出以下結論:農民帶地入社、帶地進入集體成立集體經濟組織,土地所有權屬于集體中的農民,由集體統一行使所涉土地權利[13]。《民法典》第二百六十一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在《民法典》以前,集體所有權就叫集體所有權,而《民法典》將集體所有權稱為成員集體所有權。在集體所有權之前加上“成員”兩個字,所揭示的內涵很豐富,對下一步農村發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14]。“成員”二字的冠入具有極其豐富的意涵及導向,有強調農村集體中農民主體地位不應虛化及土地所有權屬于農民而由集體行使之意。因此,可印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原始取得抑或自然取得是由新中國成立前及后來的法律歷史所形成或賦予的,即原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成員,戶籍保留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的,皆為該組織成員。《草案二次審議稿》對成員定義引入戶籍前提因素的合法性、正當性、決定性意義即在于此。由戶籍所體現的原始取得的成員身份具有可繼受性、相對封閉性及財產屬性等特點,成員子女如出生落戶該集體即屬于該相對封閉閉環內成員,可繼受集體財產性權利等權利,以此體現原始成員身份的可繼受性,《草案二次審議稿》第十二條對此進行了確認。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特別法人,法律給予其私權上意思自治的作用空間和自由。根據法律和章程規定的程序和條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有權決定某些人員從其他集體經濟組織加入本組織。同時《草案二次審議稿》規定結婚、政策性移民等無特殊情況應必然確認為成員。上述兩種新增成員的情形,無論意思自治的同意抑或法律規定的必然,皆應以戶籍轉入為必要條件。從以戶籍為基礎認定成員身份的積極意義投射到鄉村有效治理的角度而言,傳統上,我國居民的身份所屬地的認知主要來自于戶籍,戶籍決定個體的地域所屬和身份保有,由此帶來一種“主人”“主人翁”“權利人”的主體意識認知,基于此種認知才能在所屬地域以特定身份參與管理、治理、決策,因此凸顯戶籍在促使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的首要作用。縱然戶籍制度改革實現了統一居民戶籍制度,不再區分城市戶口與農業戶口,實行居民戶口制度,但各地區的教育水平、社會保障、生活環境等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短期內仍有較大差距,確定戶籍轉入為必要條件是防止部分村民利益“兩頭占”、維護公平和農村基層社會穩定的有效規定。
(二)成員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成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的不確定性
營利法人股東有決定公司經營方針、選舉和更換董事、監事,審議批準公司年度財務預決算方案,修改公司章程等權利,承擔如實出資、合法經營、損害賠償等義務。非盈利法人出資人、成員、會員有管理組織、決定運作方式等權利,承擔履約出資、遵法守紀、發展公益等義務。以上權利義務基于締約,因而較為穩定,而締約自然人一方的權利義務、年齡已由相關法律規定,因此能形成一種建立在法律獲得性身份之上的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與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不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之間在加入時不存在合同關系[15]。故相較上述兩種法人而言,普遍而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無法在作為特別法人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其成員之間形成。原因如下:其一,部分組織成員是由于出生繼受原因自然獲得身份,此種成員年齡分布廣泛。一方面,基于出生、收養等原因獲得戶籍而成為組織成員的未成年人無法對組織履行成年人應當履行的義務,與組織無法形成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另一方面,對于集體經濟組織內的老病殘等弱勢群體,未對集體經濟組織履行相應義務是因自身條件所限。如果恒以秉持“是否履行村民義務”之標準作為組織成員資格判斷,那么上述人員的成員資格喪失將成為既定風險。中國式鄉村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是維護鄉村社會和諧穩定秩序[16],這一做法于邏輯和價值層面均屬不妥[17],容易累積農村基層矛盾,不利于鄉村善治。其二,自然獲得身份的現實與本人的意愿并非盡然統一,由此會產生成員對組織行使權利的消極和履行義務的懈怠。其三,實踐操作中成員與組織之間并無完整的締約約束,城鄉二元差別導致的成員外出打工、經商現象突出,輔以升學、參軍等人口暫時流出使成員顯現流動性大等特點,在無完整締約約束的情況下流出成員無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的意愿或可能。這是在城鄉梯次發展的時代背景和相對匱乏的鄉村社會資源雙重沖擊下,部分村民不得不從生計和興趣二者之間做出的抉擇,在一定意義上,其作為鄉村自治主體,直接或間接缺席了鄉村治理的政治參與活動[18],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治理過程中,應當尊重村民的主體性地位,結合政府和基層更好地發揮“上下機制”的相互融合[19]。因此,應以相對務實的法律規則賦予村民自治組織在成員認定標準方面的自主和自由,對沖鄉村自治主體淡薄的參與積極性。《草案二次審議稿》第十二條之“成員確認”中,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可“依法確認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制作或者變更成員名冊”。意即在該法律的授權下給予集體組織對于身份認定的自治自主權利,因此,《草案二次審議稿》第十一條之“成員定義”中,就不宜規定成員需“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成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以此來限縮農民集體的自治權能,而應允許農村基層根據所在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治理傳統、文化習俗等制定受到本區域普遍認可的權利義務關系模式,并以此規范治理主體與集體經濟組織以及治理主體相互之間的社會行為。此外,以未對集體履行義務為由否認其成員資格違背比例原則,權利義務要素因違反比例原則,不應納入成員資格要素的評價框架[20]。因此,二者之間實難形成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的特別之一就是部分成員無法與組織形成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特別法人的特別之處應包含成員與組織之間權利義務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應在成員定義中得以寬容理解甚至給予法律認定。應當正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構成及行為現實,擴大該特別法人特別之處的邏輯周延性,壯大組織的實用功效。
綜上,《草案二次審議稿》第十一條組織成員的定義條文中,以成員(農村居民)需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成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為必要條件,實屬不必,缺乏可操作性。
(三)成員以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財產為基本生活保障的非必要性
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是指國家為保障城市居民或農民達到最低生活水平而制定的一種社會救濟標準,各地區標準不同。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針對農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純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而采取的一項兜底保障措施,相關概念源自我國《社會保險法》等法律法規。而“基本生活保障”并非一種法律概念術語,《草案二次審議稿》關于成員定義中含“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財產為基本生活保障的農村居民”相關描述,應將其中的“基本生活保障”理解為一種當地農村普遍基本生活的自我滿足能力。厘清《草案二次審議稿》對成員定義中關于基本生活保障的內涵這一前提之后,可進一步對成員以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財產為基本生活保障作為成員資格認定的必要性進行探討。
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財產為基本生活保障作為前設條件來認定成員身份并不具有必要性。原因如下:
其一,有違現實。法律功能的現實指向之一即為推進社會經濟發展文明進步,為現實的正向現象保駕護航、規范指引。前文已述,經濟高速發展及城鄉二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大量農民進城務工或主工輔農,隨時間推移逐漸實現不再以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為基本生活保障,這是特定歷史發展階段造成的既定事實,部分留守農村的居民繼續種養耕織也并非只為保障基本生活,而是以富裕生活為目的。更何況一部分擁有集體經濟組織戶籍的人非因其本身原因未能實際取得承包地,其根本沒有“以土地為基本生活保障”的土地物質基礎。意即部分戶籍在農村集體的農民除承包地外,都有獲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來源甚至改善性生活來源的辦法。故不宜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財產為基本生活保障作為實質要件來對成員身份獲取進行設限。
其二,限制流動,定義或被架空。強制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的民法規則二分法,是基于法律規則的約束力標準,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確認標準而言,也可以用以上兩種規則予以規定[6]。《草案二次審議稿》出臺的目的,是為了填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空白,成員定義是該法強制性規范約束力的體現,彰顯成員身份認定辦法的法定性質。在此定義框架下的具體認定工作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的任意性規范發揮,體現法定概念下的村民自治空間。以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財產為基本生活保障作為前設條件認定成員身份,必然帶來實踐操作上的困惑,難以對集體成員的生產生活狀況、基本生活保障來源等進行量化界定。如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嚴格按照《草案二次審議稿》定義進行量化,則極有可能產生身份確認糾紛,甚至造成農村人口流動障礙,或使流動人口存在失地失業的雙重風險。省、自治區、直轄市如按《草案二次審議稿》規則框架下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標準及成員確認方式做出具體規定,也很難做到定分止爭。如要避免上述農村基層自治自決中的問題顯現,最終實踐操作結果極有可能是對成員定義的架空。《草案二次審議稿》本就賦予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對村民委員會、集體經濟組織提供資金支持,基本上將其等同于和國家法律地位相近似的行政給付義務主體,這也表明其成員身份具有社會保障功能[21]。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應回歸其兼有的社會保障權屬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土地等財產收益保障成員基本生活應為成員的兜底保障條款,而不宜作為成員身份定義的必要條件。
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喪失標準及權益保留的遺漏與改進
在基于法人章程、成員自愿放棄以及民主決議方式認定成員身份喪失時要注重生存保障價值的考量[22],這是價值導向上的生存保障體現,此種導向可視為防止成員財產權利“兩頭空”的舉措。但作為頂層制度更要考慮設計上的公正與嚴密,如公正欠缺猶如水源污染,引來地方立法的跟從,傷及集體或成員利益,滋生農村基層治理混亂;如嚴密不夠則可能給予部分成員財產權利“兩頭占”的逐利空間。《草案二次審議稿》在成員身份喪失標準及權益保留的設計上,存在些許不足之處。
(一)成員身份喪失標準的涵蓋遺漏
《草案二次審議稿》第十八條采用羅列方式規定了喪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幾種情形,其中第一款第四項規定“已經成為公務員”的成員喪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根據我國《公務員法》的規定,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草案二次審議稿》中,死亡、喪失國籍及已經取得其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者喪失成員身份是基于事實不能、意思自治和身份唯一性特征所導致。而《草案二次審議稿》規定公務員不擁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則是基于其身份特殊性,即“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工資、福利、保險的穩定性。享受國家保障,并不依賴農村土地生產生活,其不應再享有基于成員身份的特殊保障[23]。但《草案二次審議稿》僅羅列公務員因身份特殊而不擁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有涵蓋遺漏之虞。事業單位有參公、全額撥款、差額撥款、自收自支等幾種方式,即事業編制人員的工資福利雖并不一定完全是財政負擔,但絕大部分由財政負擔,同樣具有工作、工資、福利、保險的穩定性,如不作任何區分仍然給予戶籍已遷出集體經濟組織的事業編制人員保留成員身份則有失公允,營造了部分人員兩頭得利擠占集體或其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利益的可能。《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戶籍關系遷出本村或者被注銷的,應當保留社員資格的情形羅列中并不含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江蘇省農村集體資產管理條例》第十八條確認農村居民為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規定中,原戶口在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村(社區)的公務員及事業編制人員也不在其列,不符合確認條件。由此可見,兩地都把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工資、福利、保險具有穩定性的兩類人員同等處理,排除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外。此外,對于戶籍遷出后在民主黨派、群眾團體以及國有企業由財政供養的在編人員是否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問題,《草案二次審議稿》也語焉不詳。
由此可知,采用羅列方式涵蓋喪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情形難免疏漏,對于已經成為公務員等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基于新身份特征需要排除其組織成員身份的群體,可用類型劃分方式使其喪失組織成員身份。類型式排除法最為核心的工作為如何確定喪失成員身份的標準,符合標準的類群即為喪失成員身份群體,不再單獨羅列若干具體行業職業。本文認為喪失條件可設定為“戶籍+財政負擔工資福利”,即本人戶籍已遷出、已由財政負擔其工資福利的原組織成員,喪失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根據前述,以戶籍為核心條件是基于以下的邏輯,即農民集體的原始資產源于農民“帶地入社”,“帶地入社”的土地構建了集體經濟組織的財產權益基礎。如何在法律上認定和固定“帶地入社”的“社”與“員”,以此形成一種相對封閉的對應關系?答案就是戶籍。1958年1月,根據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農村人口按照合作社開始進行戶口登記。至此,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相對應的城鄉分離的農村戶籍制度在我國得到確立。人民公社化后,我國農業人口普遍獲得了與其所在生產隊相對應的農村戶口[24]。1958年底,參加人民公社的農戶達1.2億戶,占總農戶的99%以上[25]。即幾乎全部農戶通過戶籍制度的登記確認了其具體所屬地的社員身份,社員身份證明了其“帶地入社”的事實,“帶地入社”的事實給予其享受土地利益的權利。因此,權利的確認和固定來源于戶籍的證明,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建制經過改革、改造、改組形成如今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如需享有組織權利,需以戶籍加以確認和固定。遷出戶籍由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原成員,可以理解為經過利益權衡后的理性取舍。以上的內在邏輯關聯足以說明戶籍在確認組織成員身份上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因此《草案二次審議稿》在喪失成員身份的規定中宜把“戶籍+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類型劃分方式確定為排除條件之一。
農村基層治理實踐操作中應定期掌握本集體成員的戶籍保有現狀,在成員轉出戶籍時要追隨掌握轉入單位的工資福利給付性質,并請相關單位協助提供給付性質的書面證據,以此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中表決相關人員喪失成員身份的證據,諸如此類法治化鄉村治理措施是減少農村基層矛盾爭議的最為權威有效的方法。
(二)對部分成員身份喪失后保留其財產權益的規定建議
法律條文對法律規制下目標群體核心利益的保留和喪失要明確果斷,免生歧義與爭端,如未有明確指引則不能交由目標群體意思自治,否則恐有花樣百出、矛盾滋生之虞。《草案二次審議稿》規定“已經取得其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已經成為公務員”“自愿退出”三種情形下喪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依據法律法規和章程規定,或者經與集體經濟組織協商,可以在一定期限內保留其已經享有的財產權益。相關規定涉及三類失去成員身份群體的核心權益保留,意義重大、敏感而面廣,但對于“一定期限”及“何種財產權益”均未明了,在此前提下交由基層自治實踐操作容易產生尺度較大的差異和難以調和的矛盾。《草案二次審議稿》第十三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諸多權利,其中最為核心的財產權益包括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權、被征收征用土地補償費分配權、集體經濟組織服務和福利享受權等。對上述核心財產權益的保留時間不宜一概而論,可根據權益性質確定合理的保留期限。
對于土地承包權,《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土地承包權的主體只能是“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亦即只有具備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才能享有土地承包權,專屬地權與成員身份深度綁定[26]。因此,《草案二次審議稿》中三種喪失集體成員身份的群體應從喪失之日起不再保留其土地承包權,削減其在戶內的土地承包份額,基層治理實際操作中可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給予合理補償,如一年生農作物可以待收割之后收回承包地份額或作價補償后及時收回承包地份額,多年生林木等可作價補償后及時收回承包地份額。對于宅基地使用權,由于宅基地是以“戶”為單位分配和使用,連同自建房屋價值巨大、使用壽命長,如因三種情況喪失成員身份后可作價補償由集體經濟組織回收再利用,也可保留其宅基地使用期限至房屋使用壽命終結之時,如喪失身份時該原成員還未“分戶”,可在房屋壽命終結重建或“分戶”時削減該原成員份額面積。對于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權,原成員可保留享有失去成員身份當年會計年度的可分配收益。不宜一次性分配、須分攤到各個受益年度的收益,如一次性或集中收取的集體資產承包、出租等收入,可繼續對原成員進行分配,直至該收入分配完畢。對于被征收征用土地補償費分配權、集體經濟組織服務和福利享受權的處理則相對簡單,失去成員身份前享有,失去身份后即刻失去,不應延續保留。
(三)應對特殊成員的權利進行特別規定
《草案二次審議稿》第十九條“不喪失成員身份的情形”中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因就學、服役、務工、經商、服刑、喪偶、離婚等原因而喪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對務工、經商、服役、服刑、就學等原因“暫時離開”集體經濟組織的可以做如下分類討論。根據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及本《草案二次審議稿》第十一條“成員定義”、第十八條“成員身份喪失”相關規定及實踐,原始組織成員外出務工、經商并不必然喪失成員身份,無論因務工、經商離開組織時間長短。需要注意的是,離開組織進城務工、經商后是否“農轉非”遷出戶籍,戶籍遷出原籍的務工、經商人員本來就是或理應是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不應剝奪其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而應讓其共同享有集體土地保障的托底權益,這既是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防止群體性返貧、維護基層社會穩定、完善基層治理的必要舉措[27]。戶籍遷出本集體經濟組織但還保留有承包土地的人員雖不喪失身份,但應在集體經濟收益分配、分紅上做出一定區分。服役、服刑、就學三類人員離開原籍短則幾年長則十數年或更長,服刑人員、全日制大中專學校在校學生無論時間長短皆應保留成員身份。解放軍、武警部隊的現役士官因特殊身份而具有較長的服役時間和穩定的財政供奉薪資,對于其身份保留與否是否因士官等級而有差異?如《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第十八條明確規定只對“解放軍、武警部隊的現役義務兵和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初級士官保留身份”;《達州市達川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界定的指導意見》規定對“現役士兵,一、二級士官保留身份”;太原市迎澤區《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確認指導意見》對現役軍人的身份保留不包含現役軍官。各地規定各異,需《草案二次審議稿》予以細化統一,否則容易滋生紛爭,陜西退役軍人牛某某訴陜西省西咸新區灃東新城土地儲備中心及咸陽市秦都區灃東街道辦事處一案就極具典型意義。原告牛某某2002年12月入伍,2018年12月被批準退出現役自主就業。2018年10月,陜西省西咸新區灃東新城土地儲備中心(以下簡稱土儲中心)與咸陽市秦都區灃東街道辦事處簽訂《征地拆遷類工作委托協議》,約定對于胡家村搬遷安置項目,由土儲中心負責對灃東街道辦事處進行政策指導,由街道辦事處負責具體實施各項工作。2018年11月,土儲中心印發《胡家村搬遷安置實施方案》第九條第四款規定:“戶口遷出胡家村的在校學生(大中專、本科、連續就讀的碩士研究生)、服役士兵、服刑人員享受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同等待遇。”2018年12月,街道辦事處與牛某某母親李某某簽訂搬遷安置協議書,其中家庭人口情況欄無牛某某名字,由此牛某某未能得到安置補償。2020年9月,牛某某以土儲中心、街道辦事處等為被告,向西安鐵路運輸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獲得征收安置補償。一審法院依據《陜西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辦法》,認定牛某某不屬于胡家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同時也認為牛某某在戶籍認定截止日前為中級士官,有權享受國家安排工作或給予經濟補助,就不應再享受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同等待遇;牛某某在退役時放棄享受國家安排工作或者給予經濟補助的安置待遇,自愿選擇自主就業并領取了國家經濟補助,因此其并不屬于《搬遷安置實施方案》規定的“服役士兵”,不應享受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同等待遇。西安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二審時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其成員身份的確認,是判斷相對人具有適格被征收人資格的認定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按《退役士兵安置條例》規定選擇自主就業即未放棄原集體經濟組織待遇。牛某某戶籍因服兵役遷出集體經濟組織,并不因此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其在退役時選擇自主擇業領取自主擇業費,不是行政機關不履行征收安置職責的法定事由,責令陜西省西咸新區灃東新城管理委員會對牛某某履行征收安置補償法定職責。本案是涉及退役軍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保留及權益保護較為典型的案例,可引發以下思考:部分省市缺乏法規、政策對現役、退役軍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規定,造成基層治理的實踐困惑及法院的裁判不一。某些省市對現役、退役軍人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保留及權益保護的規定也有所不同,使相關群體缺乏一種統一的公平收益結果。因此,《草案二次審議稿》及未來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應對此履行統領作用,解決基層自治紛爭和法院的裁判不一。此外,對于保留資格情形喪失后戶籍遷回原籍進行恢復確認的時限是多久等問題,《草案二次審議稿》都應該給予指引。
五、結" 語
以頂層設計來推動實踐發展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邏輯[28]。《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呼之欲出,該法的出臺會改變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相關規定分散于《民法典》《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及地方性法規規章的現狀,起到統領指導作用。成員身份認定關系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的實現,是完善農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功能作用、拓寬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的前提,是以鄉村治理法治化推進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鄉村是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共同富裕的關鍵展示場域,其治理能力治理體系影響著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的走向與成效[29],擬訂科學化、系統化的成員身份認定規則,有助于鄉村自治法治水平的提高:第一,強化農村居民屬地主人翁意識,提高基層自治積極性,增強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能力,降低農村基層管理成本。第二,保障權益、改善民生,能更好地落實中央關于以保障和改善農村居民民生為優先發展方向的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體系。第三,通過法律權威界定成員身份認定的法治和自治界限,政府行政權和村民自治權界限,消除模糊空間,使基層自治在法律框架下大膽有為。第四,化解矛盾,體現公平,能妥善解決農村基層養老、教育、醫療等以身份為基礎的權益的公平實現。第五,保證宏觀治理不走樣,微觀治理呈多樣,頂層制度設計框架下能使鄉村自治的本地化得以延續,使各地農村基層能根據本地風俗習慣、文化傳統、治理特點探索與本地相適應的鄉村治理體系。《草案二次審議稿》總結試點地區實踐經驗,在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方式上以“法定+自治”的路徑選擇極其科學,既確保了實現成員身份認定標準及權益保留的公平正義,又尊重了農村基層組織及成員的意愿。但要改變地方立法關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標準及權益保護標準紛繁混亂、多樣復雜的局面,《草案二次審議稿》還需做相應的清晰表達和細化規定,立法釋明相關爭議問題。法律規定成員身份認定標準、身份喪失及權益保留要符合我國農村人口流動大、地域發展不平衡等社會現實,科學集成集體成員身份認定標準,建立明確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規則,減少社會管理風險,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壯大,助推鄉村振興共同富裕大戰略。
參考文獻:
[1]" 趙文京,趙海月.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共同富裕三重維度探析[J].學術探索,2024(1):18-25.
[2]"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22-10-26(1).
[3]" 李增元,李艷營.論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區治理的法治歷程與新時代法治需要[J].社會主義研究,2019(3):108-114.
[4]" 嚴聰.論集體經濟組織吸收新成員事項的立法規制——以湖北省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地方實踐為背景[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2):83-93.
[5]" 秦靜云.農村集體成員身份認定標準研究[J].河北法學,2020(7):159-176.
[6]" 肖新喜.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確認標準[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6):51-58.
[7]" 吳昭軍.動態系統論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取得的立法范式轉型[J].中國農村觀察,2022(2):130-143.
[8]" 宋春龍,許禹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派生之訴當事人適格研究——基于78份裁判文書的實證分析[J].南大法學,2022(2):54-73.
[9]" 趙元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司法認定標準研究[J].法制與經濟,2018(10):18-26.
[10]" 房紹坤,任怡多.“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從“外嫁女”現象看特殊農民群體成員資格認定[J].探索與爭鳴,2021(7):106-120.
[11]" 習近平.加快建設農業強國 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J].求是,2023(6):4-17.
[12]" 馬翠萍,郜亮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理論與實踐——以全國首批29個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為例[J].中國農村觀察,2019(3):25-38.
[13]" 劉競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界定的私法規范路徑[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9(6):151-162.
[14]" 孫憲忠.從《民法典》看鄉村治理中急需關注的十個法治問題[J].中州學刊,2021(2):41-48.
[15]" 謝鴻飛.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治理特性——兼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的完善[J].社會科學研究,2023(3):10-21.
[16]" 陸益龍,李光達.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本質要求與路徑選擇[J].江蘇社會科學,2023(2):78-86.
[17]" 張先貴,盛宏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標準:底層邏輯與應然表達——面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背景的深思[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3):114-125.
[18]" 詹國輝.鄉村治理現代化:意涵、困頓與理路[J].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1):66-78.
[19]" 李鋒,王俊夢.中國式現代化視角下鄉村治理框架研究[J].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4):39-53.
[20]" 王義雙.動態體系論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研究[J].甘肅政法大學學報,2023(2):133-145.
[21]" 宋天騏.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內部治理中的“人”與“財”——以治理機構的人員構成與集體資產股權為觀察對象[J].河北法學,2022(4):34-50.
[22]" 管洪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特別性論綱[J].法學家,2023(5):88-102.
[23]" 張兆康,丁關良,朱蕓,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界定上的重大制度創新——以浙江省寧波市江北區為例[J].中國集體經濟,2023(6):1-4.
[24]" 許明月,孫凌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確定的立法路徑與制度安排[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1):245-256.
[25]" 佚名.人民公社[J].中國經濟周刊,2019(18):41.
[26]" 吳俊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準成員制度的立法指向與規范構造——兼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J].中國土地科學,2023(6):12-19.
[27]" 章林曉,徐郁青.“農嫁女”“農轉非”兩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土地托底保障問題初探[J].社會治理,2022(10):74-83.
[28]" 張彩云,張必春.治理視域下的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議題、演進與機理[J].湖南社會科學,2023(5):67-75.
[29]" 王馳,雷震.重塑善治: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建構與實現[J].社會科學家,2023(11):84-89.
An Analysisof Identification Rules for Membership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YANG Lin,YUAN Wenquan
(School of Marxism,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The identification,loss,and retention of rights following the loss of membership i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exer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terests of rural residents.Scientific institutional design is essential for guiding good rural governance,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and achieving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Law 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Second Review Draf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raft”) defines the membership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based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owever,it should not mandate that members' basic livelihood guaranteebe provided solely by collectively owned land or other assets,nor should a stable relationship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the two be a prerequisite for defining membership. Regarding the loss of membership,a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financial burden of wages and benefits” can be employed to exclude groups such as civil servants and public institution staff from organizational membership.For members who are temporarily absent due to reasons such as employment,business,military service,or education,due to reasons such as working,doing business,serving in the military,or studying,the retention period for core property rights like land contract rights and homestead use right should not be uniformly defined but determined reasonably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rights.The “ Draft” can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residents,enhance their enthusiasm for self-management,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by refining and improving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related to membership.
Key words: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member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identification rules;Law 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rural governanc
責任編輯" 韓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