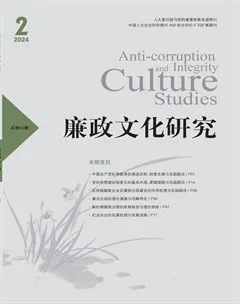廉潔合規的理論溯源與范疇界定
王譯
摘 ? 要:廉潔合規作為企業刑事合規的新生事物,廉潔合規的理論基礎可通過“政治德性”的理論原點、“特別權力關系”的理論依托以及“軟硬共治”的理論進路來尋根溯源。廉潔合規在履職行為層面涵蓋了“為民”“務實”“清廉”的政治本色導向,在政治德性的內在要求層面涵蓋了“忠誠”“干凈”“擔當”的政治品格導向。通過營商環境和政治生態間的互動關系,判斷企業廉潔合規的實施效度需圍繞國家法律、黨內法規來建構企業章程以及內部規章制度。廉潔合規的基本范疇有別于刑事合規、前置于反腐敗合規,融貫于行政合規,其強調單位“出責”的全過程性,還應明確個人“擔責”的階段性。
關鍵詞:廉潔合規;法治反腐;監察體制改革;政治德性;行政合規
中圖分類號:F272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文章編號:1674-9170(2024)02-0036-11
一、問題的提出:何為廉潔合規
隨著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為《刑事訴訟法》)的修訂,企業刑事合規附條件不起訴試點工作的開展使得“合規”成為當前監察法、刑事訴訟法領域的研究熱點。在諸多研究成果中,與合規相關的文章充分梳理了企業刑事合規的制度起源、理論基礎以及現實樣態,并對企業刑事合規的基本制度框架予以學理闡釋和分析。在以檢察起訴裁量主義為理論基礎的制度完善過程中,刑事合規理論的生成拓寬了酌定不起訴乃至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適用場景。在此基礎上,廉潔合規的這一提法反映了當前法治反腐中的新常態,即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前三種情形。從狹義層面解讀,“廉潔合規”應僅在市場經濟語境下,通過法治營商環境實現企業內部治理結構與規章制度的合規,甚至還包括從業人員的業務行為合規。從中義層面解讀,“廉潔合規”還可涉及事業單位在業務行為上關于執業倫理操守的行為合規與業務合規。從廣義層面解讀,“廉潔合規”涵蓋了所有履行職務和業務的行為,其著重指向“職務”或者“業務”行為的公開性和不可收買性。在常見的商業賄賂情形中,多以回扣形式呈現的“內幕交易”行為往往從產生之時不涉及過高的刑法評價。因此,作為新時代法治反腐理論的創新,廉潔合規將原有的企業合規理論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其圍繞全周期法治反腐的階段性,以嶄新的面貌揭示了法治反腐過程中“防微杜漸”的深刻哲理。與合規概念相關聯的是,“廉潔合規”作為企業合規的一個分支或者延展,從狹義層面應局限于企事業單位而非面向機關單位。但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同樣要求公職人員履職行為的廉潔性。盡管“廉政”可被視為“廉潔”在政治場域中的體現,二者之間的關聯仍應從廣義范疇進行解讀,即本文研究的“廉潔合規”不應僅局限于經濟領域,或者經濟行政領域,而應當延展至公權力運行的全部領域。廉潔合規的主體也不必然僅針對企業,而應適當允許其延展至“單位”這一層面,這與我國現實國情中市場競爭主體身份的二元性密切相關,即“合規”一語既可面向國有企業,亦可面向民營企業。在以企業合規整改為路徑的優化營商環境過程中,單位犯罪的“出罪”機制建構必然引發對全流程從寬的制度需求。①“廉潔合規”通過現有企業合規建設的制度創新,可為整體提升單位合規建設形成多維監管的主體推動力。②
圍繞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階段性成果,“廉潔合規”與“反腐敗合規”同為體現監察“全覆蓋”在單位內部治理層面的積極效能。同時,“廉潔合規”應反映公私主體廉潔從政和廉潔從業之間的相互協調性。因此,本文回溯廉潔合規建構的理論基礎,闡明其有別于其他合規制度的價值,在以“出責”為制度運行旨歸的場景中探尋“廉潔”與“合規”這一對概念背后包含的時代意蘊與制度面向。
二、廉潔合規的理論溯源與價值導向
廉潔合規的應運而生回應了法治反腐過程中,對于監督執紀“四種形態”間程序銜接的靈活運用。從程序運行的效果層面,廉潔合規本質上有別于刑事合規。前者旨在實現“未病”的預防效果,而后者則是從“已病”的角度降低刑事責任承擔限度。廉潔合規脫胎于傳統的合規體系,而重點指向企業風險中的“清廉”價值。在非國家工作人員經濟類犯罪中,因“廉潔”問題導致企業破產倒閉的并非罕見。若要厘清廉潔合規的基本范疇,則應在現有的合規制度規范體系中梳理和總結廉潔合規的理論根基與價值導向。
(一)廉潔合規的理論溯源
第一,廉潔合規中“政治德性”的理論原點。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提出,好人的德性有別于好公民的德性。好公民的德性伴隨政體變化,好人的德性即至善的品德具有相對穩定性,而并不跟隨政體發生變化。③因而,政治德性理論肇始于古典“德性論”,好人的德性即“道德”,而好公民的德性反映在“政治德性”層面。“政治德性”又為“政治道德”,集中體現在公職人員的履職行為規范當中。與“政治德性”相對立的是“倫常德性”,用“政治德性”與“倫常德性”的兩分法衡量“公德”與“私德”的差異性,在政治哲學范疇中具有更為適宜的時代價值。①我國古代四書五經中的《尚書》論及“德”,主要指內在的精神品質,而非外在的行為能力,即“在身為德,施之曰行”②。政治德性在“廉潔合規”中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政治德性意味著“廉潔從政”的履職行為應同時被賦予必要的道德屬性。在政治與道德之間,這一理論原點意味著政治德性代表了政府行為的政治追求、政治制約和政治基礎。“廉潔從政”要求黨員干部以及所有公職人員在“明大德、守公德和嚴私德”的履職行為中,通過加以道德層面的義務,穩定國家和社會治理秩序、提升依法執政水平以及強化民眾對于政府的公信力。從政治德性理論的邏輯原點可知,廉潔合規同時具備了政治的道德訴求和道德的政治價值。③
第二,廉潔合規中“特別權力關系”的理論依托。“特別權力關系”理論乃屬傳統行政法的范疇。行政機關與公務員之間,公立學校與學生之間,獄警與囚犯之間乃至社會團體與個人會員之間,存在著“命令”和“服從”之間的特別關系。④在救濟層面,這類關系往往無法通過常規的訴訟方式對權利侵害實現回復效果。因其具備相對的“不可訴”,在該類關系的運行過程中,處分行為一經作出即宣告終局效力。“特別權力關系”理論肇始于德國法上的領主制度,而經由歷史變遷延伸適用于社會團體與成員之間。⑤“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在現代法治語境下的適用場景更為拓展,黨組織與黨員干部之間的關系具備了“特別權利關系”的實質化特征,這包括以“效力性條款”為依據的剛性權力規制與服從義務以及黨紀處分和政務處分的不可訴特征。自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以來,將公職人員“全覆蓋”納入監督執紀執法的對象范圍,其行為規范以黨內法規為依托。黨內法規理論和實踐運行規則的優化完善具備了獨立于國家法律體系的正當性。根據特別權力關系理論,黨員干部擴展至全社會企業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時,廉潔合規的適用主體和范圍亦在“特別關系”范疇中得以證成。相較于傳統特別權力關系理論中行政行為過于內部化的現象,現代特別權力關系理論更為看重超越內部行政關系的不抵觸、法律保留以及正當程序這三大原則性要求。⑥這主要表現在,以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乃至企業法人為分析對象時,廉潔合規均應關注從業者或者執業人員對于“廉潔”的基本認知。在輕微違紀到違法的行為演變過程中,其應承擔的受監督責任應高于一般的普通民眾。該理論較好地回應了不同身份特征下的廉潔“遵從”者,亦在責任實現方式上體現為不同層級的規制路徑。⑦
第三,廉潔合規中“軟硬共治”的理論進路。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的社會契約理論提供了近代法治國家權力生成的專有邏輯,對現代民主法治的推進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并不應然具備我國本土化適用的土壤和環境。以國情為主要因素,法的遷移和發展必須考量特定國情下的社會治理環境。我國的廉潔合規需結合不同權力/權利主體間在社會治理中的現實矛盾從而在動態的治理進程中實現平衡。在廉潔合規的理論溯源過程中,法規范的“軟硬共治”理論進路體現了廉潔合規有別于刑事合規的規制方式。廉潔合規的責任后果脫離于刑事責任,因而在軟法指引和硬法規制的二重邏輯中具備了“共治”的意義。此種“共治”納入了黨務合規的話語體系,其因“廉潔”一語本身屬于軟法指引的領域,帶有鮮明的柔性治理意涵。“柔性治理”與軟法在某種程度上并非同一事物,誠如學者所言,“軟法”概念將剛性的“法”予以改造,可對法學理論與法治實踐帶來困擾和混亂。①但相對于法、國家法、實證法等剛性條款,“軟法”構成社會治理的秩序基礎但不依賴國家規范的立法形式和程序,更無須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②從某種程度上論,基于“廉潔”的柔性治理需要同時倡導政治德性和倫常德性的共同作用,才能將“軟硬共治”融匯于黨規國法的協調銜接治理過程之中。因此,在黨內法規語境下,“廉潔”應重點通過黨的監督保障法規從而達到預期效果。借助批評提醒、談話函詢、問責等方式,軟法和硬法的雙重規制路徑方能得到保障。而在監察法規的語境中,則通過監督檢查、監察建議以及政務處置等方式實現硬法效果。黨規國法的二元共治現實樣態在“軟硬共治”的理論架構中可緩解刑事合規產生的訴訟回轉矛盾。正是紀檢監察二元權力的合署辦公,可幫助廉潔合規在制度構建和規則形成過程中通過“軟硬共治”平衡黨規與國法協調銜接中的沖突。③
(二)廉潔合規的價值導向
廉潔合規在企業刑事合規的全流程從寬發展路徑中,體現為對營商環境優化的價值側重。涉企風險降低不僅通過刑事責任的減輕和免除來提升營商主體承擔經營風險的能力,更表現為通過廉潔規范的價值指引來推動和完善企業合規的體系建構。從“懲治”為目的到以“矯治”為目的之理念轉型,廉潔合規進一步反映了“合規整改”貫徹“紀法銜接,法法貫通”的全過程特性。法定的從寬事由,可保障涉企案件當事人在歷經紀律審查、監察調查和刑事訴訟流程時可自內向外形成“獲得新生”的機會。在經濟發展新格局的新時代中,不斷降低企業治理結構中的犯罪誘因,從而達到違紀違法犯罪的積極預防效果。④“民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一,我國黨和政府旨在構建“民主”“高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在價值導向上,通過“為民務實清廉,忠誠干凈擔當”提升黨員干部的廉潔性。反映在自我主動性與積極性層面,需對該部分價值與廉潔合規之間作進一步解讀。
第一層面:履職行為的具體指向。廉潔合規好比“政治體檢”。在廉潔風險的測量評估中,往往資金密集領域存在資源富集以及靠企吃企謀取私利的現象。以國企腐敗為例,其與我國長期處于轉型期的社會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國企領導、關鍵部門負責人的職務行為利益關聯大、受到的社會誘惑多,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違紀違法和犯罪風險并無本質上的區別。⑤資金越密集,資源越富集,越有可能產生廉潔風險,包括工程承攬、立項放行、撥付回款、物資采購等方面。2015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為《國企改革意見》),2017年3月中組部、國務院國資委黨委《關于扎實推動國有企業黨建工作要求寫入公司章程的通知》(以下簡稱為《國企黨建通知》),2021年5月中辦《關于中央企業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強黨的領導的意見》等黨內法規以及黨的規范性文件賦予了國企在廉潔從業層面的具體內涵。國企領導以及工作人員履職行為的“廉潔”導向不應局限于日常管理中的批評提醒和談話教育,而應立足于從建章立制到內化于心的自我革命。在履職過程中,應以常規巡視為手段,明確外部監督的獨立性與重要性。
在以國企為分析對象的研究場景中,統籌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不腐”一體建設,應重點把握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結合國企領導以及部門負責人的工作性質,在深化整治金融、國有企業等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過程中,筑牢拒腐防變的制度“堤壩”。這其中涉及“為民”“務實”“清廉”三方面的政治本色導向:
第一,“為民”。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論政治品德還是社會公德均將“為民”納入了公職人員履職過程中的重要考察指標,這主要體現在黨的六大紀律中的“群眾紀律”。早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啟動之時,為民即成為群眾教育路線的根本。在此基礎上,廉潔合規更是將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處置效果予以前置,在反腐敗合規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常態監督與履職行為中的規范性。①
第二,“務實”。“務實”這一價值導向體現為對“為民”價值這一根本遵循的具體實現方法,其作為中國共產黨黨風廉政建設的具體指向,事關黨和國家的盛衰存亡。②“務實”體現了廉潔合規必須圍繞廉潔單位建設的具體情況,強調“主體責任”的基礎上明確不同崗位的廉潔風險點。此即說明,廉潔合規在“務實”層面上的要求更為接近以量化的標準來塑造單位與個人的政治形象,以期在參與經濟社會建設以及服務群眾的過程中將黨的宗旨貫徹于一言一行。
第三,“清廉”。“清廉”是對上述兩項價值的基本要求,在親清政商關系層面重在塑造風清氣正的法治營商環境。相較于廉潔合規的自我革命,提升民眾的清廉感知亦是新時代廉政建設的重要目標,也是鞏固黨執政基礎的現實指向。清廉感在反腐信息傳播路徑中存在著多元化與極端化并存、積極性與消極性并存、趨同性與對抗性并存的問題,這具體表現為涉腐敗信息處理的程序框架與傳播環境。③在不當的信息傳輸過程中,“清廉”存在著被誤讀和曲解的風險,包括近年關于廉潔政治建設中的“低級紅”和“高級黑”現象。在新聞宣傳工作中,因思維觀念落后、缺乏輿情風險意識,個別媒體為博取流量創造帶偏節奏的話題從而誤導民眾產生錯誤的廉潔認知。④這些現象雖未形成實然的風險,但在當前的網絡輿情環境中初級信息可產生較強的信息傳輸“次級效應”。在不對稱的信息傳輸過程中,不僅降低了民眾清廉感知,更可導致矯枉過正或者過猶不及的制度實踐弊端。
因此,在“為民”“務實”和“清廉”的價值導向中,三者獨立存在但互為補充,共同為我國推進廉潔政治和貫徹“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貢獻了精神支持。我國反腐敗合規的終極目標亦落腳于此,廉潔政治建設成為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緊迫任務。①
第二層面:政治德性的內在要求。從主體層面來看,我國廉潔合規建設任務主要面向公職人員群體,其以政治德性呈現“秉公用權”“依法履職”的公權力廉潔屬性,因而涉及“忠誠”“干凈”“擔當”這三方面的政治品格導向。
第一,“忠誠”。在該價值層面,集中反映了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干部身份的先鋒模范形象。“對黨忠誠”,既是無產階級政黨黨員的首要政治品格,又是政黨長期執政的重要保障。我國國有企事業單位施行黨委集體領導的運行制度,這實際上在廉潔合規層面即向全體黨員干部提出了“忠誠”的要求。從黨章宣誓制度即已發現,其作為引導和教育黨員干部政治忠誠的有效方式,通過宣誓語言的述行性、宣誓儀式的倫理價值和宣誓行為的共情力達到凝心聚力,強基固本的群體積極影響。②為在黨員“政治生命”全過程中通過廉潔合規強化廉政文化,黨員干部“對黨忠誠”的制度保障離不開對職務行為的根本政治品格,即回歸黨員履職過程中的身份屬性。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在廉潔合規語境下“忠誠”還可體現為針對規范遵守者的合規激勵積極效果,這在刑法學“積極一般預防理論”中可見一斑。“積極一般預防理論”強調,合規的出罪目的并非以刑罰等制裁手段懲治個別規范違反者,而是從社會一般預防視角教導規范的遵守者強調民眾對于合規的“規”產生忠誠的價值信念。③
第二,“干凈”。提倡“干凈”的政治品格,意在說明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無產階級政黨在本質上有別于以財團為支撐的資本主義政黨。在廉潔合規范疇中,“干凈”不僅強調公職人員內化于心的政治品格與道德境界,更對外化于行的行為指向形成明確的指引。例如,公職人員在履職過程中既不能索要又不能收受財物,這從主觀方面的兩端反映了內在品格中的“廉潔”導向,而“干凈”更強調“做事”即履職層面上的行為規范,其意在指出公職人員的正當履職過程因不發生金錢財物或者其他價值的“交易”,即以不按照程序“辦事”甚至不給“好臉色”看作為“回報”,或者通過其他“設卡”等方式刁難群眾。因此,有學者將“干凈”的三層意涵總結為“思想純凈”“做事干凈”和“內心清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④
第三,“擔當”。與西方國家“街頭官僚”的法治體制不同,我國的黨政體制塑造強調條塊模式和政治倫理。⑤“擔當”價值貫徹于政治倫理,而政治倫理反映為社會主義政黨的黨性修養、工作作風、德才素質以及履職能力等方面。在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四風”過程中,“擔當”這一價值尤為體現“廉潔文化”中的對官僚主義這一弊病的重點防范。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我國廉潔政治的實踐探索首先從1932年至1934年蘇維埃中央政府開展的以肅清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為內容的廉政運動開始。而后,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通過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建設,以保持艱苦奮斗的品格來實現共產黨的人理想和擔當。⑥邁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了好干部的五條標準,即“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其中“敢于擔當”便是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得以保障的國家公權力履職落腳點所在。①
三、廉潔合規范疇界定的基本問題
國家在公共利益層面進行決策、分配和實施的總體安排,在公權力廉潔性層面關乎民眾對于民主政治的美好追求,“廉潔合規”在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深入階段亦是體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圍繞反腐敗階段性成果的重點問題上,廉潔合規不僅應有別于刑事合規,更應立足于事前預防和風險化解的視角把握其內在規律的運行邊界。
(一)廉潔合規中的“廉潔”
廉潔合規的范疇界定關乎廉潔政治建設中的長效性機制。王岐山同志曾強調,全面從嚴治黨不等于反腐敗。②通過以辦案為導向的監察調查和職務犯罪偵查并非“廉潔合規”的性質,亦非反腐敗合規的初衷。從源頭上推進廉潔建設和預防腐敗,必須把握“廉潔”的內涵,在現有的規范場域中廉潔合規包含了兩個維度的問題:一是廉潔合規與反腐敗合規中的客體邊界;二是廉潔合規過程中的政治立場。“廉潔”和“反腐敗”同為廉政建設的一體兩面,往往通過政治生態判斷廉政建設的實施效度。政治生態代表了政治體系及其行為同所處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之間的關系。政治生態的核心評價要素即“政治廉潔”。③與“反腐敗”不同的是,“廉潔”更加強調事前預防中的日常工作,這不僅涵蓋了廉政文化的氛圍營造與積極宣傳,還涉及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常態管理、規范指引和監督檢查。在黨內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中,相較于反腐敗合規監督的全周期性,廉潔合規更強調以批評、教育和提醒為處置形態的內部治理,而非動輒上升至政務處分乃至移送司法。“權力尋租”作為違反廉潔性的典型標志,其體現的是公權力的“可收買性”。當公權力被定價之后,在所謂資本主義“黑金”政治場域下,政府或者正當參與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過程變得不再純潔。因此,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從本質上代表了廉潔政治。廉潔政治不僅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務,亦是鞏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④廉潔合規不論面向國有企事業單位還是面向國家機關,都是對中國共產黨基本路線的根本遵循。
(二)廉潔合規中的“規”
在學術話語體系中,廉潔合規作為新生事物尚未從基礎概念上形成共識。因而,本部分著重就學界成果中關于“廉潔合規”的共性認知予以梳理,以期為“合規”中的“規”界定提供學理參考。在筆者看來,廉潔合規中的“規”至少應涵蓋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合乎廣義上的國家法律。廉潔合規的“規”能否直接指向《刑法》《民法》等實體法規范?抑或面向《政務處分法》《監察法》《刑事訴訟法》等程序法規范?筆者對此持肯定態度。從責任兜底的角度來看,《刑法》盡管作為最為嚴厲的實體法規范,但在犯罪形態中存在著不承擔刑事責任的法定情形。此即意味著,即使違反“廉潔”的履職行為,依然存在著不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空間。例如,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多次利用工作場地便利拿走辦公用品共計300余元,并未達到貪污罪立案標準。但是,“侵吞”“竊取”財物的行為實然地存在廣義上的違法性,這個“法”即使不觸及《刑法》,在最低限度上也必然涉及國有企業工作人員的相關執業操守規定。因《刑法》需恪守最大的“謙抑性”,在諸如《民法》等作為調整平等主體人身財產權利的法律規范,亦存在廉潔合規的規制空間,例如存在關聯交易、內幕交易的表見代理或者不當得利等。其次,《政務處分法》出臺以來,內部行政處分并未因此而撤銷。在以內部行政關系的上下級行政管理形態中,違反廉潔要求的小額貪污受賄行為僅在單位內部予以行政處分即為已足。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要求廉潔政治應符合主體多元化、過程復合化、方法法治化和手段多樣化的特點,當此類情形無須升格為政務處分或者黨紀處分形態時,關于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中的復合化合規目標方能得以證成。同時,這也符合廉潔合規實施過程中比例原則的內在要求。①
第二,合乎黨內法規。黨務合規是企業合規體系建設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對傳統刑事合規理論的必要延展。在我國,最大的政治立場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廉潔政治建設必然離不開黨內法規,若刑事合規中偏重于黨的監督保障法規,廉潔合規則更偏向于對黨的自身建設法規進行深度理解和適用。在現代企業治理語境下,黨務合規對于廉潔合規的意義在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根本政治立場。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在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環境下,通過優化法治營商環境推動公平競爭機制和行業標準的完善,以堅定理想信念不斷提高市場主體在“廉潔”層面的業務操守。②作為市場競爭的參與主體,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既以清廉的政治環境為保障,又要以親清的政商關系為橋梁。因此,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黨務合規層面均存在著業務“廉潔”的要求,這在以刑事合規的出罪中表現在國家工作人員和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屬性差別。③
第三,合乎企業章程和其他規章制度。不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企業章程均為現代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憲法”所在。在企業章程中,涉及工作人員的執業操守與行業倫理時,關于“廉潔”執業行為的規范建構必須圍繞上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等制度予以體系設計。同時,“廉潔合規”的“規”還可從非正式的交易習慣或慣例等軟法性規則中得以證成,此屬于“內化于心”的倫理塑造。基于“軟硬共治”的“軟法”屬性,作為“廉潔合規”的重要主體,企業應關注“廉潔”在職業道德層面上的潛在作用。正如前述關于“政治德性”理論的溯源,“廉潔合規”在規章制度之外的柔性引導方面,須強化企業廉潔文化對于員工個人素養的積極影響。這對于公民德性理論在廉潔合規實踐中的拓展運用,具有顯著的指導意義。正如學者指出,現代商業社會的興起導致政治德性與道德德性的內容隨即變化。新的道德原則默認了現代交易語境下對于習慣的遵從,但這種有限的遵從放松了原有習俗對公民行為的道德約束。④在企業規章的制度設計過程中,“廉潔”從業的行為規范亦需通過“合規”的方式得以體現。“外化于行”的具體規則屬于上位法的解釋性規范或者執行性規范,其在原有刑事合規的基礎上重點關注企業生產經營方向以及行業發展目標。以“組織體責任”理論為分析工具,其在“廉潔合規”場域下強調將企業視為獨立的生命體。“廉潔合規”的構建可以反映單位在制度建構與風險預防上區別于工作人員的責任分割,代表的是不同的意志和行為指向。單位通過合規章程、員工合規手冊等靜態的合規管理機制履行“廉潔”注意義務。單位對從業人員的違法犯罪行為提示后,其廉潔合規的具體規則即可形成預防、識別和懲戒的動態管理系統。由此,合乎企業章程和規章制度的“廉潔合規”在追責層面若已盡提示和注意義務,則不存在合規上的管理過錯。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便單位責任可脫離于個人追責,合規整改在刑事合規中對于出罪及輕罰的影響力非常有限。①因此,在合規體系完善過程中,廉潔合規如何在單位層面實現整改、監督效能,其具體措施的展開都應系統評估和謹慎推進。
四、廉潔合規范疇界定的理論向度
如果說刑事合規的目標是為了“出罪”,那么反腐敗合規與行政合規便是面向“出責”這一目標,廉潔合規的目標則是面向工作常態化的“廉政”標準。相比于前二者在辦案程序上的形而下規范設計,廉潔合規更類似于軟法上的思想引領與行為規范,并不以強“效力性規范”作為建章立制的依據。
(一)廉潔合規區別于刑事合規
在現代企業治理路徑中,刑事合規的發展逐步向數據合規邁進,其意味著數據信息亦是廉潔合規的重要方面。在數據合規的場景下,廉潔合規的理論發展主要面向于數據信息傳輸的公開性與程序性。依托全周期數據監管的規律,廉潔合規實質上代表了刑事合規在“出責”上的前端制度設計。通過設定“軟法性條款”,在執業準則或者標準的優化完善過程中降低后續可能的違法犯罪風險。對于后端刑事合規的“出罪”事由,需要以充足的證據線索為基礎。在缺少此部分線索時,“出罪”變為“出責”即已說明程序性質的轉變,從而將刑事合規阻卻在廉潔合規之外。同樣,作為信息獲取、傳輸和使用的各階段責任主體,當數據主體存在過錯導致廉潔風險而不能免責時,這意味著單位與個人在責任上的劃分得以明確。在建章立制和實施合規計劃后,在減免制裁過程中廉潔合規對單位形成了有效激勵。②單位在數據上開展廉潔合規,從程序的后端視角可減少非廉潔行為的負外部性,客觀上有助于全程參與監督的積極效能,更可借助技術手段保障單位和個人以及社會與國家利益的重要措施。③
以數據合規為參照,部分從事數據深度加工、利用并在市場中形成一定壟斷地位的單位,在數據流通的行為控制過程中,其可通過定向數據服務的供給,基于數據黑箱和算法偏見形成的數據壟斷性支配而偏離了算法規制理論中的可解釋性要求。④倘若該部分數據因提供者通過交易而存在傳輸和使用上的程序問題,并不能直接引發刑事犯罪。判斷的界限在于是否從構成要件上滿足,因而從執業人員的業務廉潔性層面可依據單位內部的數據管理規定尋求更為適切與緩和的廉潔合規方式。具體表現為:其一,強調單位“出責”的全過程性。全過程性意味著經濟行政領域的政府監管部門應承擔以企業為主體的單位及其從業人員的廉潔監督。其二,明確個人“擔責”的階段性。在界分單位與個人責任的基礎上,重視以營商環境為保障目標的單位利益。甚至,在數據領域的合規還可能出現輕微違反廉潔行為不承擔民事責任的情形。從性質上,其有別于其他非廉潔行為的“出責”事由,這是因為數據加工和利用過程在廉潔性違反層面并不以權力尋租行為作為媒介,而是出于一種職務或者業務上的便利。
在可責性層面,此類情形或許尚未達到單位內部乃至現有規范的追責評價標準。在責任形態的轉換視角上,防止將符合《民法典》規定但違反廉潔要求的行為按照“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對待乃至按照犯罪處理,為避免責任性質混同導致的雙重責任負擔,此可作為廉潔合規在“出責”形態上的認知判斷標準。①但能否認為,在未被認定為犯罪或是被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時,廉潔合規即已宣告任務完成?筆者對此持否定態度,因刑事責任的不予追究在“酌定不起訴”語境下,仍不能免除對單位和個人的行政處罰或是單位內部的行政處分責任,此二者在相互關系的建構層面應屬遞進而非僅為并列關系。
(二)廉潔合規前置于反腐敗合規
廉潔合規與反腐敗合規的相似點在于,將涉廉潔合規腐敗風險的管理責任由國家部分轉嫁至單位與個人。借用刑法犯罪圈理論擴大規制對象范圍時,廉潔合規并不意味著單位將違反廉潔規定的行為視為涉腐敗合規的“出罪”前置。②基于本土化的“合規管理義務”內涵,在行政法上規制單位違法與犯罪的關鍵路徑在于界分國家監管義務、單位管理上的法定義務以及約定義務。因行政監管過程涉及單位整改時,廉潔合規與反腐敗合規在消除內生性違法犯罪風險以及促進合規經營的目標層面趨于一致。③不論“出罪”還是“出責”,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程序轉換不同階段,廉潔合規都應前置于反腐敗合規。因此,界定廉潔合規與反腐敗合規的主要標識表現在:其一,廉潔合規的實施主體。這主要包括決定主體與參與主體。以跨境單位的廉潔風險防控為例,廉潔合規主要面向單位的經濟內控風險,包括財務會計、審計、風控等腐敗預防機制。即存在資本和數據的跨境業務時,相關單位作為治理主體應建立廉潔合規專門管理機構,實現經營活動和廉潔合規信息的暢通,保障廉潔合規協議的落實。而反腐敗合規主要是針對已有的線索,整合單位內部監督力量實現跨地區、跨部門的前期調查合作。這屬于對廉潔合規實施主體范圍的階段性擴張,因而不純粹局限于單位內部,還有可能涉及行業協會、行政監管部門以及司法機關。其二,廉潔合規追責效果。從追責效果上,廉潔合規引發的責任低于反腐敗合規。又從行為規制層面考量,反腐敗合規的“規”在效力層級上應高于廉潔合規。例如,廉潔合規不涉及對主體資質的否定性評價,反腐敗合規可通過監察機關對違反規定的單位或個人列入腐敗黑名單。通過職業限制、限制從事招投標活動、取消財政補貼資格、強化稅收監控管理、提高貸款利率等懲戒措施實現“硬法”規制效果。④
(三)廉潔合規融通于行政合規
在單位合規體系中,廉潔合規可在單獨制定“企業合規法”中獲得證成。企業合規作為單位合規的主體部分,其案件多表現為企業及其負責人行賄、受賄等腐敗,以及銀行欺詐、逃稅、偽劣產品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從性質上,此類案件多隸屬行政規制范疇,主要表現為證監會、市場監管、稅務、生態環境保護等部門聯合執法事項。整合了原行政監察職能后的監察機關也需要借助行政合規強化對單位廉潔合規內部治理效果的日常監督檢查。①廉潔合規的單位內部治理與行政合規之間存在的共通現象為從事黨務、紀檢監察的專職干部與單位內部人員之間“外行”管理內行的矛盾。對此,廉潔合規在單位內部的具體管理義務上,應體現為執法事項的廉潔性規制。在以財務審計為主導單位內部風險管控行為實施過程中,其與行政法上的義務產生貫通關聯時,廉潔合規的重點在于對行政執法程序啟動前的信息收集與證據固定。這就需要借鑒行政合規的承諾認可制度,主要是指因合規管理而引發違規事件產生時,涉案企業應向業務主管、監管乃至執法部門申請合規整改并提供相應的合規整改方案。由此,在避免進一步的違紀、違法乃至犯罪風險前提下,防止廉潔合規在行政合規場域下因無法整改而流于形式的情形出現。
相較于反腐敗合規這一理念,廉潔合規更看重單位自身監管的常態性,重視單位工作人員從事業務行為的純潔性。在監察全覆蓋的語境下,派駐監督通過發揮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日常監管功能,可有效阻卻違規違法朝著嚴重的職務犯罪行為演變。從“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角度觀察,廉潔合規在我國政治倫理中具備了天然的政黨優勢與制度發展環境。新時代我國廉潔政治發展和廉潔文化的傳播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隨著廉潔合規理念的進一步深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將加快涉企跨境業務的流通。這一過程更加需要借助以數據技術為媒介的合規形式,因而“廉潔”這一價值導向將引領全流程合規理論邁上更為豐富完整的新臺階。
責任編校 ? 王學青
On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Category Definition of
Anti-corruption and Compliance
WANG Yi1, 2(1. Faculty of Law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Hunan, China; 2. Hunan Provincial Procurator Theory Research Base, Xiangtan 411105, Hunan,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entity of enterprise criminal complianc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anti-corruption and compliance can be traced through theoretical origin of “political virtue”,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special power relationship” and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of “soft and hard governance in coordination”. Integrity and compliance cover the political nature orientation of “serving the people”, “being pragmatic” and “being honest” in the performance of duties, and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rientation of “loyalty”, “cleanliness”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political virtue.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ec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nd intern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around state laws and inner-Party regulations to judg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erprise integrity and compliance. The basic category of honesty and compliance is different from criminal compliance, placed before anti-corruption compliance, and integrated into 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 It emphasizes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organizations “responsibility” and should also clarify the stages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integrity compliance; anti-corruption in the rule of law; reform of supervision system; political virtue; 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