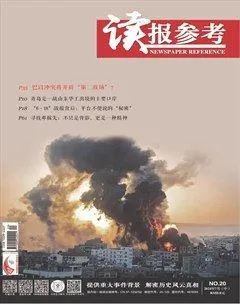古代有哪些傳說中的神秘寶劍
《古今刀劍錄》,據傳是南朝道士陶弘景所著。書中記錄了大量上古帝王的名劍信息,籠罩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但其記述多為孤證,很難考證其真實性。今人能讀到此書,是由于《四庫全書》中有收錄,但連清朝人都質疑其內容的真實性,評注曰:“是書所記帝王刀劍,自夏啟至梁武帝,凡四十事;諸國刀劍,自劉淵至赫連勃勃,凡十八事;吳將刀,周瑜以下凡十事;魏將刀,鐘會以下凡六事……雖文字小有同異,而大略相合。則其來已久,不盡出后人贗造。”
若不當成真實歷史來讀,而是看成古人想象的上古神話,《古今刀劍錄》還是很有閱讀價值的。開篇就說:“夫刀劍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后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湮沒。慨然有想,遂為記云。”我們或許無法確知先秦時代的刀劍模樣,卻可以知道古人眼中先秦時代的刀劍模樣,這正是閱讀此書的趣味所在。
有一則記夏啟鑄銅劍之事:“夏禹子帝啟,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后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為星辰,背記山川日月。”夏啟之后,再無禪讓,開啟了“家天下”的歷史,其歷史知名度確實很高,但至今沒有任何關于夏啟的考古實物出土,自然也無法考證書中的夏啟銅劍的真實性。
另一條關于夏朝的:“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不難看出,這就是后人想象的東西。甲是夏朝后期的王,現今尚未發現夏朝文字,更不可能有什么篆書。這里提到的牛首山,應該不是今天南京附近的牛首山,而是《山海經》里那座神秘的牛首山。孔甲鐵劍之論,應只能算是神話傳說。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采北祇銅,鑄二劍,名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埋在阿房宮閣下,一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秦始皇的寶劍,據說被埋在阿房宮下面,后來也失傳了。
“前漢劉季(劉邦,字季),在位十二年。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此即斬蛇劍也。”劉邦斬白蛇起義,本來就是傳說,很有可能是劉邦集團為了增加自身統治合法性而編造的故事,就類似那些帝王都要給自己編一個很神秘的出身。從考據的角度來看,劉邦斬蛇之劍,也是缺乏信史憑據的。
不過,比陶弘景更早,西漢劉歆在《西京雜記》中,曾記錄過這把寶劍的信息,這讓斬蛇劍有了更多的傳說色彩:“高祖斬白蛇劍,劍上七彩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于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漢代的皇帝基本都有自己的寶劍。比如,漢武帝劉徹,“以元光五年,歲次乙巳,鑄八劍,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恒、霍、華、泰山五岳皆埋之”;漢光武帝劉秀,“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漢末三國名人,也有名劍傍身。曹操有孟德之劍,“以建安二十年,于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如今,曹操高陵已經出土了大量陪葬品,包括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字樣的三塊珍貴石牌,可見曹操生前用大戟、大刀、短矛等武器,可偏偏沒有《古今刀劍錄》里的這把孟德之劍。或許,這把劍只是古人想象的產物,當然,也不排除寶劍早已被盜走的可能性。
劉備則比較特別,“以章武元年,歲次辛丑,采金牛山鐵,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飛,一與趙云”。看來,劉備不像其他帝王那樣高高在上,很有“分享精神”,寶劍也要打造八把,分給孩子和忠臣。
“吳王孫權,以黃武五年,采武昌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銅、越炭作之,文曰‘大吳,小篆書。”《古今刀劍錄》還寫道,孫權得到了韓信當年的寶劍,將它賞賜給了周瑜,“又赤烏年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以賜周瑜”。在此,《古今刀劍錄》作者犯了一個低級的歷史錯誤,孫權使用“赤烏”這個年號,是從238年到251年,而周瑜早在210年就死了。陶弘景距離三國時代不算太遠,學問深厚,不太可能出現這樣的錯誤。這更加說明現存的《古今刀劍錄》有可能是后人假托陶弘景之名所著。
《古今刀劍錄》也有記載,帝王佩劍,將相用刀。比如,魏晉名將鄧艾的寶刀就很傳奇,“年十二,曾讀陳太丘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余。刀上常有氣凄凄然,時人以為神物”。
(摘自《北京晚報》黃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