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漁家傲》中窺別樣清照
姜宜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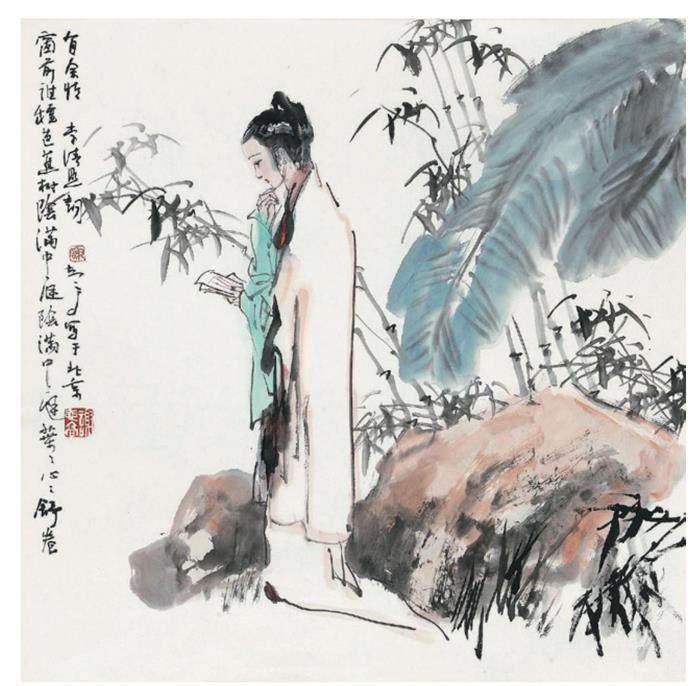
摘 要:文學風格具有穩定性與多樣性等特征,以李清照為例,她是我國婉約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但其文學風格并不局限于此,《漁家傲》是她南渡之后的詞作,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與平日的風格大不相同。作者生活經歷的不同會導致其文學風格發生變化,這為古詩詞鑒賞教學提供了思路。
關鍵詞:文學風格;李清照;《漁家傲》;古詩詞鑒賞教學
一、李清照文學風格概述
(一)文學風格概述
文學風格這一概念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其內涵在歷史長河的變遷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而東西方文人墨客對其的理解,雖然有一定的共通點,但是在某些方面始終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中國關于風格的理論始于魏晉時期,但與我們普遍理解不同的是,當時的“風格”二字并沒有應用于文章的品讀,而是用來評論人的氣度、性格等。《世說新語》一書指出,“風”是風姿、風采,指的是人的外貌,“格”是人格、德行,重點關注人的內心,所以將“風”“格”二字合起來,就意味著在評價他人時要內外兼顧、德行并重。后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風格”便不再專指人的外貌和性格,開始向文學的方向發展。曹丕是將風格理論從品人逐漸過渡到品文的關鍵人物之一,他認為,不僅是外貌與人的性格有關,即相由心生,涉及作家作品的表現形式和思想內容也同樣與寫作者的內在涵養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于是,他在《典論·論文》一書中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風格理論發展至此,首次出現了“氣”的說法,意味著我國文人已經關注到了文學風格與作家個性之間的關聯。此后,文學風格理論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劉勰的貢獻尤為突出。他不僅將“風格”二字引入文藝理論和批評中,更是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將文學風格分為“典雅”“遠奧”等八類。除此之外,劉勰既肯定了文學風格與人的主觀因素有關,又注意到客觀因素的重要性,這為全面分析作家的文學風格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而在之后的發展過程中,我國的文人還是主要圍繞著“氣”的觀點對文學風格理論進行充實和發展。
對西方學界來說,亞里士多德等人是最早將“風格”與語言和修辭技巧等外在形式聯系在一起的,他在《修辭學》中指出“語言的準確性,是優良風格的基礎”[1],在《詩學》里也曾強調“風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明晰的風格是由普通字造成的”[2]。由此可見,在此階段中,西方對“風格”的理解還主要停留在修辭等外在形式階段,而不涉及對文本深層含義的解讀。18世紀,西方文學界對文學風格的解讀開始發生縱向的變化,逐漸關注作家的創作主體性。在這一背景下,布封提出了“風格即人”的觀點,認為作品的文學風格實則是作家內在氣質的表現,這一見解無疑與我國的“氣”說不謀而合。此后在文藝思潮和馬克思文藝理論等的推動下,西方的文學風格理論也逐漸擺脫了形式主義的外殼,進一步達成了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綜上所述,對文學風格的解讀和理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中西方學者對其解讀的發展歷程也并非完全一致,但最終,在前人不斷探索的基礎之上,文學風格形成了一個較為統一的定義:文學風格指的就是作家的創作個性在文學作品的言語結構和有機整體中顯示出來的相對穩定的、獨特鮮明的,并能引起讀者持久審美享受的藝術獨創性。[3]
(二)李清照文學風格概述
李清照是宋代一位著名的女詞人,世人稱其詞為“易安詞”。李清照作為婉約派的代表人物,詞風溫柔細膩、委婉含蓄,處處彰顯了女性細致敏感的內心世界,這體現了作家文學風格的穩定性。風格是作家在數十年如一日的寫作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積累起來的,所以具備較強的穩定性,且往往會體現在作家大部分甚至全部的作品當中。例如,李清照在“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4]“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5]等詞中都將女子的無憂無慮、怡然自得等心態展現得淋漓盡致。
值得注意的是,文學風格的穩定性是相對而言的,并非絕對的一成不變,時代的變遷、個人經歷的改變均會在作品中有所滲透。李清照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的創作風格以南渡為界,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李清照生于士大夫家庭,自小生活條件優越。李清照的家庭氛圍十分寬松民主,父母重視其教育、尊重其喜好,因此李清照可以充分汲取文學領域和古玩字畫帶給她的養分,生活得無憂無慮,其前期的創作風格大多呈現出清麗、明快的特點。除此之外,李清照前期的感情生活也比較順利,經過自由戀愛后,嫁給了情投意合、有著共同志趣愛好的丈夫趙明誠,此后李清照的生活便愈發甜蜜、高雅豁達,詞作題材主要集中于自然風光和閨中生活,即使在《一剪梅》《醉花陰》等詞中會抒發寂寞相思之情,但這種情感也會隨著夫妻二人小別團聚很快消散,且讀者從中更多的是品讀出李清照與丈夫二人的恩愛之情,理解所謂“思念終有安身之所”的含義。
然而,朝廷內部激烈的新舊黨爭把李家卷了進去,李清照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先是父親陷入黨派之爭后被流放,清照上書無果,且差點為自己招來牢獄之災,直至丈夫明誠去世后,其詞作的字里行間便常常流露出寂寥感傷之情,詩詞的選材也轉向懷舊和思鄉。不僅如此,李清照五十歲之時,本來以為自己遇上了人生第二個依靠——第二任丈夫張汝舟,但現實生活卻將她拉進另一個深淵。張汝舟娶她僅僅是為了給自己裝點門面,毫無“理解”二字可言,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之下,李清照最終選擇了狀告張汝舟,最后雖然勝訴了,但宋代“告夫需連坐”的規定也使李清照自己身陷囹圄。杭州的生活讓她苦不堪言,不愿回首,這也就是為什么清照在杭州待了這么多年,卻始終無心描寫西湖的原因之一。在上述一連串打擊之下,李清照從最初衣食無憂的小公主變成了一位飽經風霜的婦人,所以其文學風格也由最初的純粹愉悅轉為沉重滄桑。譬如其經典詞句“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6],《聲聲慢》的開頭僅用14個字就將李清照當時內心的愁苦彰顯得淋漓盡致,營造出清苦無依的心境,與前期“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等詞中傳達出的輕松愉悅之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此可見,詞人在后期創作的詞幾乎都是對不幸人生和苦難時代的高度藝術概括。
文學風格是對作家藝術生命的高度凝練,其軌跡和表現都是作家成長過程的縮影。“從本質上說,它是對一切可能性的最大限度的索取,而不是終止于某個目標或境界之前。”[7]從這些觀點和實例中可以看出,后代學者對文學風格的理解是在一直向前推進的,穩定性是其特性,但并非絕對屬性,作家的藝術生命正是在探索和對抗中不斷得到升華。李清照的詞作也正是因其人生軌跡的改變、經歷的豐富,而變得扎實厚重、耐人尋味。正如仕途不順的柳宗元一樣,有了在永州、柳州受貶十余年的經歷,才創作了閃耀文學史上千年的眾多篇章,在中國文學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品析《漁家傲》的文學風格
(一)《漁家傲》詞作語言賞析
李清照在一次海上航行時,天氣變幻莫測,她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海劫難,劫后余生之時,大筆一揮留下了一首流傳千古的《漁家傲》,全文如下:“天接云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仿佛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8]
通讀全文后不難發現,該詞開篇的意境就十分開闊,天、云、銀河等宏大的意象奠定了本詞豪放的基調,“接”“連”“轉”等動詞的運用又使得這些意象渾然一體,將詞人驚心動魄的感受最大限度地傳遞給讀者。接著,“仿佛”與“夢魂”二詞點明本詞的內容是建立在詞人夢境的基礎之上,這就使《漁家傲》站到了浪漫主義風格的行列,這也是李清照比較少見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該詞擺脫了傳統上片寫景、下片抒情的結構,而是將上下兩片融為一體,上片以天帝的問話為結尾,“殷勤”二字刻畫出了一位關心民眾的統治者形象,這與現實中只顧自己逃亡的南宋高宗皇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寄托了李清照渴望得到關懷與溫暖的愿望。接著,詞人在下片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答,“報”“嗟”二字傳達出作者在經歷了漂泊無依、居無定所的生活后,內心無盡的感慨與嘆息。而詞人所說的“路長”與“日暮”,實則出自屈原的《離騷》:“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9]李清照運用了用典的手法,以簡練的語言傳達出自己“上下求索”的意念與經歷,從而充實詞作意蘊、開闊讀者眼界,達到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緊隨其后的一個“謾”字,有力地道出了詞人懷才不遇、無人問津的心酸與苦悶,這與自己在逆境中仍積極進取的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添幾分落寞與不堪。對天帝提出的“歸何處”這一問題,李清照在下片的末尾給出了回答:“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10]詞人巧借莊子《逍遙游》之力,直言自己想要像大鵬鳥一樣,乘著颶風到達夢想之地——蓬萊、方丈和瀛洲三座仙山,這也從側面反映出,詞人雖在現實生活中飽嘗心酸,但仍對未來心懷期待,對自由和光明充滿渴望,只是苦于在現實中無法實現,便將其寄托于這虛無縹緲的夢境。
(二)《漁家傲》詞作思想感知
《漁家傲》一詞中蘊含著作者復雜深厚而又細膩的情感,最主要的是作者對祖國現狀的惋惜和痛心。李清照是見過繁榮昌盛的大宋的,況且她又是一個能吟唱出“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這種豪情壯志的女子,足以見得其不凡的女性心態,所以在一系列動亂發生之后,她對每況愈下的宋朝社會以及國君的不作為甚感悲痛,她對天帝的形象塑造也正是其對國君及其統治階級的殷切期望,她幻想國君會像天帝一樣,主動而熱情地關心人民動向、體察民間疾苦,雖逢國難,但不可只顧自身周全。
從《漁家傲》的語言、內容和風格中不難推出,該詞創作于李清照南渡之后,屬于詞人創作后期的作品,但這首詞也絕不同于后期常見的寂寥與苦悶的基調,反而極具浪漫主義色彩,言辭豪放,被梁啟超評為“此絕似蘇辛派,不類《漱玉集》中語”[11],這與李清照一貫的婉約風格形成鮮明的對比,體現出文學風格的穩定性也并非一成不變。讀慣了李清照詞作的婉約細膩之后,《漁家傲》這首詞反而給人以別開生面的豁達之感,別有一番風味,詞人的形象也愈發飽滿與生動。
如此筆力豪放、渾然天成的詞作風格,對辛棄疾、陸游等后人都有著較大的影響,也不枉世人稱她的詞為“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12]了。
三、文學風格的穩定與變化對高職語文教學的啟發
對正處于高職階段的學生而言,其語文學習的重點主要有四個方面,分別是文學常識的積累、漢語基礎知識的掌握、古詩和現代文的理解、大小作文的寫作。其中,古詩詞鑒賞一直是學生學習的重難點所在。對學生來講,古詩詞鑒賞的學習難度一直居高不下,對詩詞產生的時代背景的割裂感和對詩人詞人的陌生感成為學生學習時最大的痛點。因此,古詩詞鑒賞的教學要以拉近學生與詩詞的心理距離為重點,通過課內教學與課外延伸相結合的方式讓學生對背景有進一步的了解。
上文對詞人文學風格的分析為語文古詩詞鑒賞教學提供了新的啟發點:本模塊的教與學可以采取分模塊的方式進行,以朝代更迭作為分區學習的依據,在朝代的大背景之下再選取主要詩人詞人的作品進行學習。如此一來,學生可以先了解不同歷史時期的時代背景和主要歷史事件,在此基礎之上再進行具體作品的學習,從而對詩詞本身產生更加強烈的代入感,加深對詩詞含義和情感傾向的體悟,這樣即便是遇到了相對陌生的作者,學生也可以根據所處的歷史時期,進行作品內容和情感的初判,極大提高了學習效率。另外,對核心作家作品進行成體系的學習,有利于學生對文人的文學風格有比較系統的把握,學生可以通過判斷作者所處階段的不同,對作品的情感做出更準確的判斷。在作品的品讀和對比的過程中,學生的詩詞鑒賞能力可以得到很大提高,實現由量到質的飛躍。這一學習模式雖然花費時間較多,但對學生能力的提升是卓有成效的。
古詩詞鑒賞的學習并非一蹴而就的,以李清照等典型詩人詞人為模塊進行學習將是極具系統性和趣味性的一種學習模式。學生對作家的人生軌跡進行了解之后再去解讀詩詞,會與作者本身產生互通和共鳴,拋除答題技巧不言,文意的把握更會提高學習的質量和效率。除此之外,分朝代分詩人學習的教學模式還可以達成語文和歷史兩門學科之間的融通和互動,讓學生的文學素養有進一步的綜合提升。
李清照的詞作就像一面鏡子,照出宋朝的更迭,照出人生的起伏,也照出后人對文學風格的進一步的體悟,無論是從文學理論還是從教學實踐的角度出發,都帶給我們深刻的啟發和別樣的收獲。
(山東中醫藥高等專科學校)
參考文獻
[1] 亞里士多德.修辭學[M].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亞里士多德.詩學[M].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 魯樞元,劉鋒杰,姚鶴鳴.文學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4] 陳祖美.李清照詞新釋輯評[M].北京:中國書店,2003.
[5] 同[4].
[6] 同[4].
[7] 謝凌香.文學風格的發展及審美價值探析[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212-214.
[8] 同[4].
[9] 屈原.離騷[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9.
[10] 同[4].
[11] 同[7].
[12] 李調元.雨村詞話[M].北京:中國書店,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