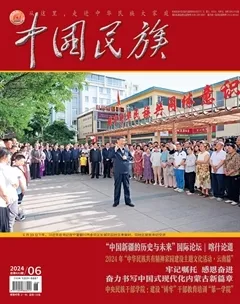拙與巧 骨與筋
拙與巧
目前我國考證發現最早的、具有完整體系的文字,是殷墟甲骨文。
雖處于書法藝術未定型階段,但甲骨文已具備其重要的三要素:筆(刀)法、結構、章法。整體而言,它的布局層次錯落、自然隨性,代表了書法藝術最原始的淳樸之美。而甲骨文的最美之處,在于它帶給人們視覺上的生動形象,體現在對現實世界中各種事物的抽象模仿。這些極富創造力的遠古文字多有簡化,并帶有某些符號象征意蘊,其絕妙之處就在似與不似之間。于龜甲、獸甲上刻字,線條的質感不同于用柔軟的毛筆書寫,甲骨文的線質較為剛硬,筆畫纖細方直,線與線的搭接處多方折、少圓轉,給人以刀刻的鋒利之感。
從夏、商以至西周、春秋、戰國,隨著青銅文化的形成、發展、鼎盛,青銅器的形制、紋樣也越來越豐富,器具上所刻銘文即金文(也稱鐘鼎文)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古代書法的集大成。金文在書風上分為4種類型:齊魯型、中原型、江淮型、秦型,前兩者風格純樸渾厚,江淮型特別是楚金文則更多地傾向“巧”,無論字形還是結構上裝飾意味都更強,更顯精致、靈動。西周早期的金文主要代表有大盂鼎,中期有史墻盤,后期有散氏盤、毛公鼎、虢季子白盤,等等。較于甲骨文時期,此時的書法藝術開始趨于成熟,線條鑄造上更為靈活,個別處做裝飾化處理,如“王”字最后一筆加重。章法上開始出現行列秩序,文字趨于規范化,書風接近于“秦書八體”之一的大篆(即籀文),屬于篆籀系統。
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長達497字的毛公鼎銘文是金文書法的典型代表,其內容為周宣王即位時請叔父毛公為其治理政務的史實。細品毛公鼎銘文,其中篆籀之意散發著早期中國書法未完全成熟時的拙氣,顯示出大篆書體的結字風格,線條圓潤而古拙。如今,我們書寫大篆體時多用毛筆中鋒,逆鋒而入,頗有力度,忌故作顫筆,求自然書寫,以感受彼時書法所特有的韻味和古人心境,追尋穿梭千年的金文古拙之氣。
春秋時期的金文出現了一種特殊的風格,即以“鳥蟲”形式作文字,在春秋中后期至戰國時代盛行于吳、越、蔡、楚、徐等邦國,前文提到的江淮型金文便屬此類。當時,這種裝飾性意味極強的書風在楚文化的繪畫和工藝品制作中達到頂峰,甚至影響到了漢代帛畫。鳥蟲書筆畫作鳥形,即文字與鳥形融為一體,或在字旁與字的上下附加鳥形作裝飾;蟲書則蜿蜒盤疊,精致華麗,后被列為“秦書八體”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文字雖加入裝飾,但基本不破壞字形,只增加了趣味性和工藝美感,代表作有《中山王三器圓壺》《越王勾踐劍》等。相較于西周時將銘文刻于器物內部,春秋時的銘文常出現在器物表面顯眼位置,成為了器物裝飾的一部分。
從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再到春秋鳥蟲篆,由拙走向巧,書法風格的變化反映著中國古人審美的提高以及技術工具的進步,而當今書法藝術創作由巧反向拙,則是書法審美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產物。
品奇書
魏晉南北朝是中華藝術發展的自覺時期,人們普遍開始有了審美意識。早在東漢末年,書法開始從實用轉向藝術層面,誕生了我國最早的書法理論著作《草勢》(崔瑗著)。包括后來索靖著《草書勢》、蔡邕著《九勢》,都是在用藝術的眼光看待書法。直至東漢末年,曹操雖下令禁碑,但卻極其喜愛梁鵠的書法,甚至“釘壁玩之”。這些行為看似矛盾,卻恰恰說明書法開始成為一門賞玩的藝術,有了新的美育功能。
東漢也是隸書發展的巔峰時期,傳世的既有風格秀麗的《曹全碑》又有筆法豪邁的《張遷碑》。這一時期,篆書雖已出現衰落趨勢,但秦篆《嶧山碑》、漢篆《袁安碑》《袁敞碑》等的典型風格仍傳揚后世。篆書慣以中鋒行筆,用筆圓潤,筆畫搭接處圓轉,展現出成熟期篆書原貌,同時又受隸書影響,誕生了別具一格的書法藝術作品——《天發神讖碑》。
建于吳天璽元年的《天發神讖碑》,碑文打破了傳統篆書形式的規范,帶有隸書筆意,起筆方形,轉折處內圓、外方,有趣處在其豎的收筆,如懸針,又有“釘頭鼠尾”之稱。“釘頭鼠尾”是我國古代人物畫像衣服褶紋畫法之一,因其線條起筆、收尾形似釘頭與鼠尾而得名,此形容用于《天發神讖碑》最合適不過。而在字形結構上,如“口”“示”“天”等一些對稱筆畫皆有向背變化。
宋代黃伯思在《東觀余論》中評價此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清代康有為更是驚嘆其為“奇書驚世”,是歷代書家爭相學習模仿的典范,書畫篆刻大家趙之謙就在其篆書中引入了《天發神讖碑》的筆意。古人講究“印從書出”,將書法與篆刻緊密聯系在一起。趙之謙曾主張“印外求印”,他為好友丁文蔚刻的姓名章就很好地印證了這一主張,取此碑筆意入印,單刀直刻,有大刀闊斧之感,頗為爽快。近代書畫篆刻家齊白石受趙之謙和此碑影響,取結構入書、印,將它們完美地展示在了自己的作品中。二位大家皆學此碑,但又從中跳脫而出,也為后人創作啟發了思路。
總之,《天發神讖碑》怪誕、奇特之風格,是篆書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創新,填補了漢之后篆書史的空白,也是吳國書風的典型代表。
骨與筋
“骨”源于中國古代相術,受漢魏品評人物風氣影響,得以入書畫品評之標準。東漢趙壹以人體的筋骨比喻“書之好丑”,衛瓘以筋骨論書,南朝人好用“骨”論書,謝赫在《畫品》中提到“骨法用筆”,張懷瓘《畫斷》提到“像人之美,陸得其骨……”“骨與筋”的概念表現在書論、畫論之文字上,體現在書法藝術結構之中。
“顏筋柳骨”是這一審美概念的典型代表。“顏”指顏真卿,“柳”則為柳公權,二人皆為唐代書法大家,他們的楷書生動地展現出了同一時代、同一書體的不同風格。
顏真卿所處的盛唐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快速發展,深刻影響著此時的藝術創作。顏體楷書以大楷著稱,字如巨石,用筆厚重,結字大度,具有外拓之勢。其字形豐腴之感如周眆所作侍女畫,展現出大唐盛世的氣闊。“顏筋”有含蓄之意,用筆難度大,書品高,藏于線條之內,字字嚴謹,又不缺柔感,頗有廟堂之氣,后被人們用來作為“榜書”的典范,其代表作有《顏勤禮碑》《顏氏家廟碑》。而柳公權為中晚唐時期的書法家,用筆偏重于骨力,起收筆均為方形,轉折頓挫明顯,且一字之中筆畫粗細變化明顯,結字挺拔,給人一種斬釘截鐵之感,非常干練,書體結構傾向于“內斂”,代表作有《玄秘塔碑》。
書法之美,還美在情感。顏真卿的行書作品、被譽為“天下第二行書”的《祭侄文稿》,就是一篇傾注創作者真情實感的傳世之作。《祭侄文稿》寫于安祿山叛亂之際,當時顏真卿的堂侄往返于常山、平原之間傳遞消息,使兩郡聯結,共同效忠王室。其后,常山郡失陷,堂侄橫遭殺戮,歸葬時僅存頭顱。得知消息,顏真卿悲憤交加,不計工拙,所書之字隨其情緒起伏,情感自然流露。
“書無意于佳乃佳耳”,《祭侄文稿》從整篇看來,前半部分較為整齊,大小字分布合理,其中略有涂改,并不是故意為之,可體會作者當時復雜悲痛的思緒。寫到“父險子死”時,筆觸猶如石頭重重地砸到紙面上,進入到作品高潮部分。“念爾遘殘,百身何贖?嗚呼,哀哉!”顏真卿在這種沉重、悲痛中創下了千古永嘆的《祭侄文稿》,書法與情感的結合達到高度統一,雖雜亂無序但未失其法度,足見作者書法技法之高超、功底之深厚。
在整個中國書法史上,像《祭侄文稿》這樣如草稿形式的作品并不多。明末清初書法家王鐸曾作《詩稿墨跡》,記錄了他詩詞創作的過程,行草結合。從中不僅可以看到王鐸作為詩人對于詩句用詞的琢磨,也體悟著一個書法家于“無意”中顯功底的魅力。
我國書法藝術歷經數千年的形成、發展、沉淀,書體風格上所出現的拙與巧、骨與筋,以及作品傳遞出的深層情感,都只不過是書法之美的一個側面。中國古代書法藝術大美無言、大象無形,一直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為中央美術學院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責編/龍慧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