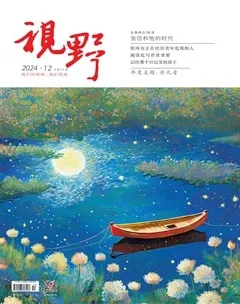明代文人的幽默

自為墓志銘
唐代文人好為別人作墓志銘,原是因為墓志銘的潤筆甚豐,為了銀子的緣故,所作多有褒詞,時人稱之為“諛墓”。明代文人則大不同。明代文人好為自己寫墓志銘,生前就對自己作出評定,多自抑語,甚至出言自毀自賤。而且唐人的墓志銘雖說是一種文體,但終究是要勒石,要留存于墓道中,明代文人則僅僅把墓志銘當作文章做,做成一種傳記小品,他們要的是意味,是可以自己欣賞把玩的情致,不見有誰真的要拿它刻在石碑上,留給后世考證出身。
若說行止怪異,那么歷代文人比較起來,當然首先要算魏晉,但明代文人也自有他們的特別之處。魏晉文人在對待自己的個人價值上,一意往“大”處看,立身處世、飲食男女,在其個人性的背后都有一個“自然之大道”,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不把圣賢放在眼里,就可以傲視天下,做出許多桀驁不馴的狂態(tài)來。明代文人恰恰相反,他們總是把自己往“小”處看,在他們心里,個人是極其渺小的,他們生活在一個無能為力的世界當中,人生貧乏,一切都不值稱道,他們因為找不到有力的庇護之道,所以顯得十分虛弱。于是,明代文人失去了直面世界的信心,失去了一種悲壯之氣,他們開始疏離自己立身的世界,把個人的歷史無奈心情,化為一種詼諧、一種嘲謔、一種游戲聲音、一種末世幽默。
自為墓志銘,就是以“佯死”告退世界的一大幽默。它把明代文人那種歷史無奈心情,渲染得淋漓盡致,同時它也向世人徹底地敞開了生存顛倒的性質(zhì)。徐文長《自為墓志銘》道:“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競系固,允收邕,可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嗤渭;既髡而刺,遲憐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復烝民,愧彼既明。”
在徐文長用來總結一生的這讀起來詰屈聱牙的數(shù)語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他對生與死的勘破和解釋,這里面更多地包含了對棄世的言說。正是這種言說所具有的自我解嘲作用,使他在個人的渺小和虛弱之外,獲得了一種生存的輕松。所以,徐文長可以那樣落寞一笑,瀟瀟然寫下如下一行文字:“葬之所,為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
與徐文長相比,對個人生存無能懷著更加沮喪情緒的,還有晚七十多年的張宗子張岱。張岱處身在明代覆亡之際,他對人生已完全沒有了信心。人在歷史強力面前,是那樣的微不足道,這種人與生存世界之間的巨大反差,張岱在他寫于崇禎五年十二月的《湖心亭看雪》筆記中,比喻得十分清楚。那種借著自然的廣大無垠而把人在其中戲稱為“兩三粒而已”的黯然,正是人生之渺小情態(tài)的流露。所以,看到張岱在他的《自為墓志銘》里,極盡用辭,把自己一生說得一無是處,你就知道他不能不以一種自我笑謔的方式,來化解和代替這無以克服的生存悲愴和遺憾。
不妨多抄一點他的文字:
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shù)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常自評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韋布而上擬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則貴賤紊矣,不可解一;產(chǎn)不及中人,而欲齊驅(qū)金谷,世頗多捷徑,而獨株守於陵,如此則貧富舛矣,不可解二;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悲田院乞兒而不驕,如此則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則唾面而肯自干,強則單騎而能赴敵,如此則寬猛背矣,不可解五;奪利爭名,甘居人后,觀場游戲,肯讓人先,如此則緩急謬矣,不可解六;博弈樗蒱,則不知勝負,啜茶嘗水,則能辨澠、淄,如此則智愚雜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為貧賤人亦可;稱之為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亦可。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jié)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nóng)、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為敗家子、為廢物、為頑民、為鈍秀才、為瞌睡漢、為死老魅而已矣。
在一個眾生顛倒的時代,人對于自己的價值除了“輕視”而外,你還能找到比這更合適的幽默之言嗎?如果你曾經(jīng)有過在這個世界上建功立業(yè)的理想,然而這個世界卻以它的無情剝奪,最終使你一無所有,那么你將會以什么姿勢,來表達這生命中最大也是最后的無聊與失意呢?張岱七十歲了,面對這一切,他已經(jīng)超然于所有的困惑與痛苦之上,成為一個真正的玩世不恭者,一個不再操心是非得失、不再測度自身的老頑童。
可是,讀明代文人的《自為墓志銘》,你又不能不感到,在他們怪異的自嘲自謔中間隱含著一種度量人生的心靈尺度。詬笑也好,自謾也好,似乎一切都可以作游戲觀,然而這背后卻有著他們對生存的深思。那就是,當他們處在世界的渺小位置而孤弱無援時,他們將設法逃避何方?毫無疑問,沉思“死”,并且把“死”看作人的生活的神圣尺度,正是這些設法逃避的明代文人不顧一切逃避的最有力的命定。
謔庵的風格
晚明文人中,王思任大概是可以首稱諧謔大師的。王思任自號謔庵,可見他比別人更要以善于諧謔自許。
山陰真是個古怪的地方,這里總是出一些落拓奇磊的人。別的且不談,就拿文章一道來看,仿佛只要出自山陰文人筆下,就特別有一種傲世的骨氣。這種骨氣之下,他們很容易對世間人事不屑一顧,所以眼睛里常常帶著冷笑,所謂“別有眼睛”,恐怕講的就是他們了。因此,你看到的山陰文人,既與俗絕,同時也與世絕,從而在有明一代尤其在晚明時期,顯示出他們鮮明的風格。
山陰文人最有代表性的三個人,前有徐文長,后有張宗子,王謔庵居其中,但王謔庵可以說是對徐文長的發(fā)揚,而又直接影響了張宗子。“蓋先生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這是張岱對他的評價。有一回,川黔總督蔡敬夫因老同年王思任閑住在家,于是邀他入幕。王思任到之日,蔡敬夫在滕王閣宴請他。當時正是江上日落霞生的時候,王思任對蔡敬夫說,想不到王勃《滕王閣序》今天又一次應驗了。問是什么原因,王思任笑著說道,落霞與孤鶩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目齊飛,大概就是說年兄你呀。這番調(diào)侃說得蔡敬夫臉上極其尷尬難堪,但又不好發(fā)作。王思任知他心里惱恨,行李沒有打開來就掉頭回家了。
按理說,王思任與蔡敬夫是同科朋友,況且蔡敬夫又是好意請他來贊襄帷幄,王思任如此尖刻,似乎有點不近人情。然而,王思任這樣放言無忌,不僅是因為他“眼俊舌尖”,實在也是他心氣太高傲的緣故。他二十歲舉于鄉(xiāng),第二年又中了進士,“房書出,一時紙貴洛陽。士林學究以至村塾頑童,無不口誦先生之文”。如此不世之才士,卻要屈身做幕客,這怎么說都是一件不能叫他心里快活的事,所以要借題惡作劇一回,其實也是為了表明自己的不平之氣。笑人者自笑,王思任自然比別人更加懂得他在滕王閣上的心理。他愿意用這種嘲謔方式求得人生的平衡,想必蔡敬夫不能理解因而也就不能原諒他的了。
的確,有人常責怪王思任嘲謔的處世態(tài)度。但這種責怪大抵出于所謂士風輕薄于世無益的迂腐見識,而看不到在世道不明的情形下,諧謔恰恰是一種有用于世的智略。我們知道,明代中葉以后,宦官專政,吏治松弛,社會腐敗,民生凋敝,天下事已經(jīng)十分難為。清直的人中,若想為老百姓做點事,一種便是像海瑞,不畏權勢,犯顏直上;另一種則是運用他的聰明,機智行事。所謂諧謔就在這時發(fā)揮特殊的作用了,王思任即是。“先生之蒞官行政,摘伏發(fā)奸,……無不以謔用事。”張岱《王謔庵先生傳》中記述了王思任在安徽當涂縣任上的一件事:
中書程守訓奏請開礦,與大珰邢隆同出京,意欲開采,從當涂起難先生。守訓逗留瓜州,而賺珰先至,且勒地方官行屬吏禮,一邑騷動。先生曰:“無患。”馳至池黃,以緋袍投刺稱眷生,珰怒訶,謂縣官不素服。先生曰:“非也,俗禮吊則服素,公此來慶也,故不服素而服緋。”珰意稍解,復詰曰:“令刺稱眷何也?”先生曰:“我固安陽狀元婿也,與公有瓜葛。”珰大笑,亦起更緋,揖先生坐上座,設飲極歡,因言及橫山。先生曰:“橫山為高皇帝鼎湖龍首,樵蘇且不敢,敢問Vg5cTIrdZBJE71NwXLNUjw==開采乎?必須題請下部議方可。”珰曰:“如此利害。我竟入徽矣。”先生耳語曰:“公無輕言入徽也。徽人大無狀,思甘心于公左右者甚眾,我為公多備勁卒,以護公行。”珰大驚曰:“吾原不肯來,皆守訓賺我。”先生曰:“徽人恨守訓切骨,思磔其肉,而以骨飼狗,渠是以觀望瓜州,而賺公先入虎穴也。”珰曰:“公言是,我即回京,以公言復命矣。”當涂、徽州得以安堵如故,皆先生一謔之力也。
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思任的諧謔并非只是徒逞口舌,而是真正的有所為而為。“以謔用事”,作為王思任的個人行為風格,值得稱道之處當在這里。而“一謔之力”竟可以卻走權貴,保土安民,不受騷擾,說到底還是因為當?shù)勒唑湙M卻又十分的愚蠢無能,所以略出數(shù)語,就能調(diào)弄權閹于股掌之間,這又是何其有意味的事。
可以說,在那個時代,凡想有作為的文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是免不了的。越是富有才智,越容易遭到忌恨,這是歷史常情。王思任兩次受人攻訐而受到很重的傷害,“一受創(chuàng)于李三才,再受創(chuàng)于彭瑞吾”。因政見不合被李三才之輩排擠打擊,固然是其中一端,而主要的則是明朝萬歷以后,黨同伐異的權力傾軋非常厲害,卷入黨爭中的士大夫文人往往成為犧牲品,王思任其能幸免乎?于是,這時候諧謔便成了他抗拒傷害的精神武器。
王思任在他的晚年,改號謔庵,并且作《悔謔》一篇。張岱說,“刻《悔謔》以志己過,而逢人仍肆口詼諧,虐毒益甚”,可知他對諧謔精神是堅守到底無悔無棄的了。公元1644年,清兵攻破南京,弘光王朝覆滅,權臣馬士英“稱皇太后制,逃奔浙江”。對于這個只知挾君自重、結黨弄權,以致“乘輿遷播,社稷丘墟”的馬士英,王思任作書一紙,嬉笑怒罵,淋漓盡致,為后世所傳誦的一句話即出自此書信中:“夫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也。”
斯言,諧乎?謔乎?但只一股精神正氣,足以讓那些害國誤民的賊子聞之氣餒色喪。
這一年,謔庵七十整,離他絕食殉國只有兩年。
優(yōu)雅的閑言
袁中郎也算是一個頗喜詼諧的人。
當時有人曾拿他與蘇東坡相比,說他得東坡“滑稽之口”。其實袁中郎是否滑稽如蘇東坡,倒也不一定,只不過明代文人比較佩服東坡,所以常常要去比附他。以幽默滑稽而論,大概文人歷來都有這樣的脾性,從漢代的東方朔往下,到魏晉六朝文人,并不缺少例子,當然因為蘇東坡離明代更近一些,把袁中郎的詼諧看作東坡遺風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東坡行事,多見載于宋人筆記,如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費袞《梁溪漫筆》等,其中常記東坡的幽默滑稽。東坡是一個十分曠達的智人,他那種優(yōu)游人生的智慧風貌,足以讓人傾倒。然而,東坡受人攻訐誣陷而終于罹禍,未必與他對時事以及當事者口無遮攔的譏刺嘲謔無關。東坡貶竄海南后,雖說已歷經(jīng)坎坷,深知世情,他的友人仍不放心,猶寄詩勸誡他說,“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shù)采珠人”。這自然是要他緘默其口,否則還會如同過去那樣很容易就授人以柄。然而東坡個性如此,恐怕到死也不會改。不錯,東坡智慧而曠達,但是他任性于世事的執(zhí)著卻更加使他的智慧曠達富于光彩。
以蘇東坡的生平來看袁中郎,顯而易見袁中郎終究不能是蘇東坡。但我們要說的意思不在這里,他們之間的可比性差別是在另外的方面。同樣是詼諧,是嘲諷,在文字言語上,袁中郎可能非常接近蘇東坡的幽默滑稽風格,然而文字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思想識度和精神境界,拿它來比較,不用說從中所看出來他們幽默個性的不同,才具有實際意義。
與宋代文人相比,明代文人在胸襟氣度上既十分狹隘逼仄,又是十分柔弱孤絕的。這一方面由于明代文人生存處境的困逼比宋代文人要嚴重得多,另一方面則是明代文人在試圖從理學突圍出來的過程中找不到寬闊的出路,于是只能退回到內(nèi)心方寸之地討生活。因此明代文人,在思想識度上往往一味局限在一己性情范圍內(nèi),認識自我生活的自由意義,這樣他們的個性就越來越走向內(nèi)在化、趣味化,他們也可能會曠達,但是這種曠達,不是從更加無所畏懼的精神自由的意義上表現(xiàn)出來的生存境界,而是在拒絕外在拘束的借口下,對身外世界的冷淡和疏離,也就是明代文人所謂的個人身心到了“極無煙火處”。所以,在大多數(shù)明代文人那里,極少看到他們關懷世界的精神大境界,有的只是一種對個人生命趣味的過于珍重。
袁中郎“滑稽之口”的個人特點,及其所代表的明季文人的思想精神內(nèi)涵也就在這里。他的弟弟小修為他的全集作序說,“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執(zhí)縛,故時有游戲語”。用“游戲語”來“破執(zhí)縛”的目的,正是為了躲避世事環(huán)境的糾纏,以求得一種“定”的內(nèi)心滿足。
也許,袁中郎比別人會更加自覺地了解他是從追求人的本真之趣這一點上,使自己回到一種童稚赤子的滑稽狀態(tài)當中。他說:
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逾于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
能得童稚赤子的滑稽之旨,是袁中郎對人生最要緊的發(fā)現(xiàn),同時又是他對人生最大的自慰和滿足。不難想見,在袁中郎那里,文人的諧謔被給予了一種最為徹底的無意義的自然狀態(tài),而照他所想,這是能夠逸脫世界之外保全人生最圓滿的方法。我們不能不說,袁中郎把文人在選擇人生歸宿時的聰明發(fā)揮到了極點。所謂“正等正覺”的“最上乘”之趣,于此便成為“雅謔”這個語詞的又一詮注。
然而我們是否注意到,當“雅謔”充分成為袁中郎及其他明季文人的一種體現(xiàn)人生至趣的形式后,在它背后反映出來的,已經(jīng)不再是智力的優(yōu)越,而是那個時代那些擁有智力的文人們思想能力的削弱,精神視度的退縮。因為像他們那樣越是透徹于人生的“本真”,便越是會放棄對世界的思慮,越是要自我放逐于世界之外而封沉于一己性靈之地。
或許我們不免把問題看得過重了,何況那是數(shù)百年前的袁中郎及其他明代文人的思想和精神缺陷。但是我想,在任何一個時代,尤其是文人的生存特別困頓的時代中,文人們?nèi)羰窃谒鎸κ澜鐣r太聰明了,未必是一件好事情。作為文人,你拿幽默滑稽來做人生的解,從而使你優(yōu)游自得滿有機趣,可是你恰恰想不到,正是你的聰明,使你在你所置身的世界中喪失了你的重量。縱然你有一張“滑稽之口”,可你的種種令人解頤的言說,只不過是一些優(yōu)雅的閑言而已。
那些聰敏透脫的明代文人早已告訴過我們,他們是如何經(jīng)歷了二百余年的空疏無用之患的了。
(阿沁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