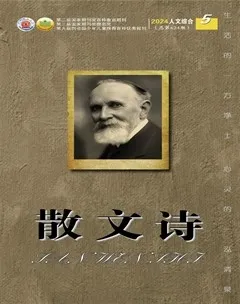一秒鐘之內(nèi)會發(fā)生什么(外一篇)
一秒鐘很短,短到只夠我對著窗外眨一次眼睛。
一秒鐘又很長,它足以放下一個人的生死。
一秒鐘不長不短,它剛好等于一首詩的發(fā)生。
當我寫下一秒鐘之內(nèi)會發(fā)生什么,太陽在東邊的天涯山頂露出了毛絨絨的金黃,那是一只毛絨絨的小雞啄開了蛋殼。
下一秒,一只狗在田野上叫了兩聲,它還在叫……一秒,對一只吠性正濃的狗實在太短。
下一秒,一只麻雀睜開了眼睛,另一只麻雀已張嘴啼叫。會有更多的鳥鳴加入,會有更多的翅膀拍動。
在日影漸高的某一秒,一只鳥的翅膀會經(jīng)過我的書桌。
再一秒,一朵閑云會經(jīng)過打開的書本,一秒鐘,它足以牽起我的手,把我變成一個小女孩。她趴在窗臺,盯著窗外蒙了一層銹跡的鐵皮煙筒,青藍色的煙正裊裊地逸向天空。
當她后來學到“裊裊”這個詞時,她想起的是冬日爐火中冒出的這些煙,她也在這個時候懂得了風。
在水邊,我等候過一些白鷺,它們在遠遠的河冰上立著,像一些白衣道人,凝神冥想,偶爾踱步,偶爾拍打翅膀疾走,偶爾盤旋長空……我在等著它們向我靠近,把我當成它們的岸。可是沒有,它們是深知距離是美的重要參數(shù)嗎?
那個午后,我相信,我一直呆在一秒鐘內(nèi),欣喜,驚嘆,遺憾……
窗外的田埂上,一個女人張開雙臂輕盈地走過,她在這一秒一定擁有了一雙翅膀,生出翅膀,總是發(fā)生在一秒之內(nèi)。
空曠的田野上,一個男人正用鐵鍬揚起塵土。這一鍬土的起落,拉開了一個真正的春天的帷幕。
我站在窗口,一朵潔白肥碩的蒲公英從我面前飛過,我眨了一下眼睛,它就不見了。不見,不見,這是在深夜的某一秒,我對一個人,更是對自己立下的誓言。
不見了,不見了,我在二十三年前,一個秋日午后的某一秒,失去了母親。又在十三年前正午的某一秒,失去了父親。
母親走時,我正在歸家的途中,在午夜,在火車上。母親在夢里告訴我——她走了。
父親走時,我守在身邊,他的眼里滾出了一顆碩大的淚滴,那是他在人世積攢了七十五年的酸澀與晶瑩,在他離開的那一秒,還給了塵世。
一秒是界碑,一邊是生,一邊是死。
一秒是美,是奇跡,是頓悟,是把我的手掌放在你的手心。
一秒,是我對這世界的深情一瞥。
一聲“丫頭”
忘了哪一年、哪一天,是白天還是黑夜,你開始喚她“丫頭”。
丫頭仿佛已在塵世等了許多年,只待你一聲呼喚。
歲月的風輕輕拂過,陽光從樹葉的縫隙里蹦著跳著而來。
她看到自己扎起了羊角辮,穿起了小花裙,脆生生地應(yīng)了一聲“哎!”
身旁是那個虎頭虎腦,撲閃著大花眼,睫毛像兩把小扇子的少年。
帆布帳篷上的雨不停地下,下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
你躺在粉底黃花的被子里聽了三天的雨打芭蕉,聽了三天的緊鑼密鼓。
你連喊了三天的“丫頭”。你不讓她走,你想讓她陪著你。
她舍不得你一個人聽雨,怕你聽出秋意,聽出寂寞。
你是任性的,你想丫頭了,你會一直喊、一直喊,喊得帳篷里都是回聲,喊得驚飛了偶爾落到樹上的鳥兒。
丫頭有時很忙。你說,你不管,就是要她陪。你知道,你喊丫頭,丫頭的心就會軟,一點點地軟下去。
你生病了,住院了,一個人。丫頭一直覺得你是一個人,其實,你有狗,不止一只。
丫頭很著急,她給自己裝上笨拙的翅膀,想飛,還想罩著你,她怕你的天空又落了雨,怕你的笑聲里藏著疼。
你是霸道的,你自說自話,訂了許多條款。
你說,一起出去時,付賬的必須是你,丫頭不許帶錢包。
你說,每晚丫頭必須給你請安,而最后道晚安的那一個必須是你。你說,你喜歡看著丫頭睡,丫頭睡成一只小豬,你就可以放心地帶她回家。
那些日子,丫頭成了你的每個清晨與黃昏。
你成了丫頭枝上的喜鵲,水里的扁舟,扁舟上的竹篙。
丫頭把自己變成樹,變成一泓碧水,變成一圈一圈的岸。
可是,有一天,空氣里,突然沒了傻小子的氣息…一
丫頭天天在等,等那讓雞飛讓狗跳的一聲聲:“丫頭……”
可是,風依然在吹,水依然在流,陽光里,再沒了長長彎彎的睫毛梳理過的日子。
丫頭突然傻了,天天用眼睛思考。眼睛,濕了又干,干了又濕。終于有一天,她的眼睛里畫出一個圓圓的句號,句號里,“丫頭”靜靜地睡著了。
她不知道,一不小心又把自己睡成了小豬的模樣。
今天,她正坐在光影里看紛紛揚揚的塵埃,突然,有人喊“丫頭”。她揉一揉眼睛:唉,又是誰家的丫頭走丟了!
稱呼都是有密碼的,就像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丫頭”和“傻小子”是絕配。
“傻小子”一點兒也不傻。他知道,他走了,丫頭就走了。
丫頭,總是把自己睡成一只小豬,在夢里被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