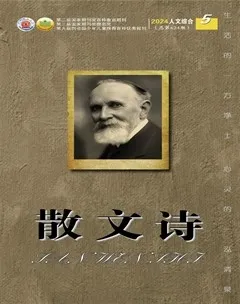生成果肉的愉悅

張悅 文學碩士。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詩作在《星星》《散文詩》等刊物發表,詩歌評論見于《中國藝術報》《星星·詩歌理論》《新文學評論》等刊物。
十篇以現代詩歌為閱讀重心的讀書筆記,十堂詩歌欣賞導引課的講義精華,集中呈現在讀者面前,構成這本整合詩人路也多年讀詩心得的隨筆集《寫在詩頁空白處》。捧讀這十篇長文,不由想到海倫·文德勒依循“打破風格”主線剖析文本游刃有余的“手術刀”,簡·赫斯菲爾德審視“偉大的詩歌如何改變世界”推開的“十扇窗”。當然,路也立足中華文化原生土壤,將文言、網絡用語、英語等同現代漢語書面語、口語相嫁接,在歷史語境與時代語境間靈活切換跳轉的文脈、文風,把“親愛的讀者”視為“朋友”的寫作心境,尤其令以漢語為母語的讀者倍感親切。
路也在前言中特別談到其對“詩頁上的空白”的理解。在她的詩性觀照下,那些后退為詩行背景,貌似無差別的空白區域,成為詩人、詩歌、讀者共生交流的場域,三種生命體“共同的呼吸”。在此,讀者“個人的生命經驗”及能動性得到充分尊重與肯定,讀詩的過程,被視為讀者攜帶生命經驗進入詩人生命經驗,并調動全身心感知力“填補這些詩頁的空白”的過程。“寫在詩頁空白處”的文字,將路也醒目的詩人身份適當后移,或者說,令其讀者身份凸顯為前景。有趣的是,這些屬于讀者的文字,與其所談及的詩歌同樣期待“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最懂它們的讀者”。埃德蒙·雅貝斯說:“一經閱讀,詞語便失去了其透明度。玻璃要成為鏡子,鍍銀是必經之路。”讀者給透明的語句鍍銀,以便照見自身。換個角度來看,讀者對自身的閱讀——作為文本預設動機和寫作策略,借助隨筆文體,得到更大程度的顯露。不妨借用路也在《里爾克宛如果實中的核》一文中對里爾克人生與創作關系的隱喻化理解,來感受詩人路也和讀者路也寫作的聯系、差異。如果說她多年來提煉詩思,凝練出的詩歌語言,如同堅硬果核,這些隨筆文字則像圍繞果核生長成熟的果肉,充盈著生命的汁水,經驗的血流。如果把其詩歌語言視作光源,這些隨筆文字則是被照亮的地帶,使其詩學話語沖動與遼闊而黯淡的語境的關聯性得以顯現。詩人路也在詩歌中止于節制性暗示的省略或沉默,并不妨礙讀者路也在隨筆中亮出張張底牌盡情傾吐的暢快。
隨手寫在詩頁空白處的文字,向讀者敞開個體經驗的姿態與行動,對讀者積極的創造性參與發出了召喚、邀請,路也“獨樂樂不若眾樂樂”的分享,亦可謂用生命喚醒生命。文本對讀者感官感知、經驗背景、意識、無意識的接納,讀者閱讀對文本、對作者經驗的介入,共同點亮意義之光,照亮讀寫互贈共享的愉悅。《寫在詩頁空白處》這本小書,生長出體量龐大的外延,以其不確定的邊界、不可見的果皮,把讀者目光包裹于果肉的瑩潤鮮美之中,并將其引向對果核、對本源的探尋。閱讀活動享受到的愉儻,是雙重的,既有基于路也生命體驗、閱讀經驗、視野、知覺、直覺的獨特口感,也有基于讀者自身背景、趣味、想象力的酸甜度,一種品嘗果肉并生成果肉的愉悅。擁有詩歌、小說、散文、評論、報刊專欄寫作等多種文體創作實踐積累,深入文學教學及理論研究、文化研究、詩歌翻譯、跨文化交流等多領域的路也,無疑是一位以多元目光聚焦詩歌的高段位讀者。詩學、哲學、語言學、歷史、政治、宗教、地理、音樂、美術、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星相學,像她隨身攜帶的各式鏡頭,滿足著一位精神生態攝影師多層次的取景需求,一位知識女性、學者型作家、偏愛文化遠足的背包客動態生成性的讀者期待。面對海量信息持續激增所帶來的經驗纏繞、語境交織,路也一方面善用抽象思維和遠距離觀察保持視野的廣闊、開放性,另一方面,始終不脫離經驗現場,力求深入生存狀態、生命細節的現實性。《寫在詩頁空白處》收錄的任何一篇文章,均未因地理跨度、歷史敘述、形而上學,或是宇宙論的巨大參照物、坐標系,跨越東西方文化的視閾,而放棄對具體事態和細節真實的呈現,而忽視她本人作為經驗主體的在場感,及其道德情感力量的參與性。路也依托發散思維,選擇了文本同語境經緯交錯的織物式敘述策略。
以十二位線索詩人引出五十多位詩人和作家,經過主題化處理的十篇文章,保留著非主題化事態與主題的連續性,以及二者間的可延展空間。《弗羅斯特親自收割》《龐德譯lt;渭城曲gt;》兩文縱橫古今、自如馳騁于中西文化的文思,比較詩學的方法論及范例分析,均給人留下突出印象。涉及相似相關主題的各異文本的比較,譯文和原作的比照,由詩歌題旨、意象、語言層面的異同,牽出有關社會歷史、地理環境、世界格局、文化傳統、文化心理、階層屬性、流派風格、個性因素、兩性關系等一系列復雜問題的深思熟慮。無論“沖著歐洲文學傳統喊話”的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鮮明形象,還是從漢樂府詩到希臘神話,從中西文明史中的愛情觀到當下現實中的婚戀觀,從地理特征到民族性格再到譯詩缺憾的大步跳轉,均展現了路也的越界思維,在不同概念范疇間建立類比,發現隱喻關聯,令人耳目一新。《向T.S.艾略特致敬》《尋找普拉斯,尋找特德·休斯》《里爾克宛如果實中的核》三文中,知人論世的手法,同樣相當醒目。前兩者分別以致敬艾略特的倫敦之旅,拜訪普拉斯墓和休斯故居的具體行程為線索,將對經典詩作的品析與游蹤相穿插,移步換景,觸實景感詩情。身在艾略特的倫敦,路也反思自身創作理念和實踐的變化,藉由艾略特的詩學追求深入思考現代性同古典的關系,進而思索中國當代詩歌發展面臨的問題,進而展開關于滋養現代漢語詩人的傳統“根系”及尋根可能的追問。懷著不同心緒悼念普拉斯和休斯,路也運用精神分析對兩位詩人的悲劇進行追溯,觸及二者的情感糾葛、家庭變故;通過文本細讀歸納二者迥異的詩學觀念、創作風格,她排除道德情感傾向的干擾因素,對二者詩歌的思想內涵、藝術價值作出中肯評價。同樣,里爾克的人格污點,對里爾克價值觀念的不認同,并未影響評論的公允性,她對里爾克將貧窮與恐懼轉化為藝術創造力的肯定,及其隱喻式思考,給人以詩歌的驚異感。
詩學向社會文化諸領域延伸的可能性,似乎具有吸附路也隨筆創作動因的強大磁力。《加里·斯奈德的荒野交談》《騎士洛爾迦奔向死亡》《W.H.奧登的哀悼:動太陽而移群星》《谷川俊太郎的圓白菜,兼及秋刀魚》《阿米亥與空中小姐》,分別側重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死亡、悼亡、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女性意識,均為現代詩歌創作的重要主題。文中介紹的經典詩歌文本,所保持的濃縮為果核的詩性,在隨筆文體中重獲果肉,那些節制、省略、無法言說的語境空白,經讀者路也填補、充實,顯得豐碩誘人。斯奈德詩歌中與寒山詩相呼應的“意象群落”,同友人山中小聚及聚后分別的動人場景:將洛爾迦用以強化死亡來臨時間點的“下午五點鐘”,比作連續敲擊讀者腦袋的“小錘子”的妙喻;由奧登悼念葉芝一詩引發,經布羅茨基、希尼仿作形成的“悼念詩鏈條”;谷川俊太郎顯露疲勞感的圓白菜意象,在考試卷上生成的多種闡釋角度;反抗男性凝視的女性立場、批判意識,及《兩個女子談論法國香水》一詩發表后的讀者反饋等等,無不使人讀來饒有趣味,讀后感慨良多。敘述所透露出的現場感、現時性,將敘述主體鮮活的生命體驗,貫穿于十篇文章構成的有機整體。路也以文思、心路的“阡陌交通”,引領讀者進入其文本構筑的精神生活現場。其間遍布看似瑣碎的細節化經驗,一定程度上,卻承載著超越抽象認知、理性自覺的詩意火花、思想激流、生命活力。
封面中央明亮燈泡同碩大蜜桃相疊的圖案適于隱喻閱讀該書的愉悅。路也信手拈來的諸多方法、路徑,起源于一枚密布溝壑的堅硬桃核,它是詩歌,也是明亮的燈盞,用語言集束的亮度,給隱沒于經驗世界的語境輸送光能。不論你是學生,詩愛者,還是詩人、評論者、譯者,追隨路也,享受填補詩頁空白、生成果肉的愉悅,都有收獲一只繼續生長的蜜桃,一份專屬美味和豐碩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