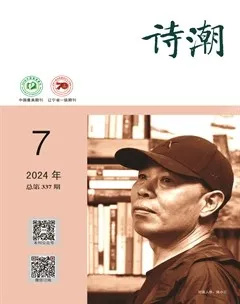李德武隨筆
詩歌從不需要辯護
詩歌從不需要辯護!詩歌也不需要警察一樣的機制來守衛。一個詩人專心于藝術,一種純粹的寫作態度就是對詩歌最好的捍衛!任何栽贓陷害等這些見不得光的手段都對詩歌無可奈何。詩歌是詩人的法身,詩人肉身受到怎樣的侮辱,都不會貶損他詩歌的價值和地位!詩歌也不需要對他的攻擊者予以回擊,詩歌只回擊值得它回擊的東西,比如功利和死亡。可喜的是沒有任何一個詆毀或仇視詩人或詩歌的人,能夠比詩歌活得更為長久!
從面前移開每一面鏡子
寫作的技術問題如果不能轉化為一種存在方式就是對存在的逃避。
這種逃避常常以文化為偽裝。文化是令我們產生告別感的東西,盡管在告別中難免會留戀或依依不舍,就像本雅明指出的“降半旗”的對象。
嘗試處理自己拒絕的或不熟悉的經驗和生活問題。在寫作中把自己壘起的墻推倒。
我們的根本問題不是和文化的沖突問題,而是和存在的沖突問題。當然誰也離不開和文化的糾纏,問題是把文化處理成什么。處理成顯在的存在,還是隱性的存在?處理成要素,還是基因?抑或回溯的界碑或里程表?
我把寫作存在處理成不確定性。要努力直面空白,從面前移開每一面鏡子、偶像和參照系。在技術上,一個詩人要敢于追求德勒茲的尖點,讓心成為光的散射源,不要試圖聚焦和成像。語言本身會有痕跡,所以一種風格不能持續太久,太久了就落自畫像了。
詩當畫(化)大千,畫自己有何益?存在的本質是變。
AI時代,詩人何為?
列夫·馬諾維奇在《新媒體的語言》中談到,在新媒體的術語里,“跨碼”就是將一個事物轉換成另一種格式。文化的計算機化進程也逐漸實現了所有文化范疇和文化概念之間的跨碼,即,在含義和(或)語言層面,文化的范疇和概念可以替換為計算機的本體論、認識論和語用學所衍生的新范疇和新概念。
文化作為一種固化語言或塑性語言,它在轉譯中必然會不斷地被選擇、剪切、粘貼,像歷史的圖像一樣被用來完成新景觀的合成,意味著文化將淪落為機器語言(AI語言),那就留給人機對話吧,我們要說點機器說不出來的語言。
詩人應該關注技術對當下的影響,技術比文化對我們存在的影響更直接,也更迫在眉睫。
當代性!算了吧!
當代性,算了吧,還是不提這個概念為好,免得讓它成為年輕就正確的理由,或者活著就先鋒的理由。我們同時活在古代、當代和未來。誰也不能把古老的發音功能從嗓子里摳出去;誰也不能在他年老時,從骨頭里剝離孩子時就已經鑄就的骨骼。如果那些炫耀當代性的人為了時尚,那就直接說時尚,而不是當代性。時尚是流行的代名詞,如果古典流行,古典也是時尚。詩人不是為他的當代性付出生命代價,而是必須為他的語言付出生命代價。無論他的語言向度如何!
阿甘本談當代性,他在談流行和時尚,這對服裝行業可以,對詩歌不適用了。詩人的存在具有現象學意義以及語言學意義,但不能歸結為當代性問題,當代性有助于對個性的含混概括,無助于對個別特征的細致辨認。時代特征或重大事件如果不是通過詩人個人化呈現,是沒有藝術意義的。就好比不能把杜甫說成是安史之亂詩人一樣。我們需要在藝術中化解時代痕跡,而不是刻錄時代痕跡。伴隨時代出現的應該是新形式、新語言和新理論,而不是泛泛的當代性概述,這在我看來等于什么也沒說,顯示出理論能力的匱乏和羸弱。德勒茲說藝術的創新來自對概念的創新。我們創新概念的意識和能力同樣缺乏。已有的概念,比如口語、民間或先鋒性,都已經代表不了今天更為復雜審美的需求和創作現實了。
要警惕詩歌寫作的知識化傾向
要警惕詩歌寫作的知識化傾向。我不能說這是一個十分糟糕的傾向,但至少這種傾向不該被大力提倡。知識化的寫作(掉書袋或滿身書齋氣或教授口吻)不是把詩歌帶向美,而是帶向學問和對硬知識的販賣。這些東西可能會讓人感到像一絲智慧,其實是學問,拖著閱讀滋生的長長尾巴。
如果我想了解知識,比如植物學、歷史,我就去讀植物學的書或史書,不會選擇詩歌。詩歌里可以有知識,這個知識不是向人指示所是(包括引經據典,我對一首詩下面跟著一長串注解總感到不舒服,就像我在和戀人接吻卻總是被敲門聲打斷),而是顯示所美,暗示不是以及不確定。詩歌不拒絕知識是因為詩人有本事讓死的東西復活。
這方面古代詩人中李商隱可能是做得最好的,“錦瑟無端五十弦”是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無端”這個詞太妙了。詩就應該是“無端”的,而知識是“有端”的。
詩是一種友善的力量
詩是一種友善的力量,一種通過把我們提升到對特別事物的沉思之中的安慰——因何而特別?嗯,因主體性。
——克爾愷郭爾
從主體性出發,詩人也是沉思者,只是,他不是利用邏輯手段沉思,不是基于承認普遍性沉思,他詩性地沉思。詩性意味著他的沉思始終是主體性的。所以,不能把詩人的沉思同哲學和哲學的任務相等同。那些把詩人的沉思與哲學的理性、體系、形式邏輯以及形而上學相等同的人都未真正認識到詩之思的本質與特征。
克爾愷郭爾要比海德格爾更早肯定了詩人之沉思。他把蘇格拉底看作是詩人,因為蘇格拉底的思想沒有體系,沒有結論。他的結論就是一切智者都是值得懷疑的,而我知道的很少。
克爾愷郭爾發現了蘇格拉底的反諷!詩人沉思時不是常用反諷嗎?我記不清楚是誰說的了(需要求證,我可以查查讀書筆記),好像是亞里士多德,他說詩人不是沒有思想,而是掩蓋思想。這話一語道破詩人內心的秘密。
承認詩人沉思的主體性是區別詩人與哲學家的最基本標準。詩人沉思只是作為一個人,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的沉思,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沉思(康德、黑格爾)。
詩的沉思,包括對真理的沉思,都不能當作知識以及真理的依據,如果這些沉思也和真理有瓜葛,也僅僅貌似而已。如果我們還不能接受詩人沉思這一事實,那就請多玩味一下克爾愷郭爾的話:“詩是一種友善的力量,一種通過把我們提升到對特別事物的沉思之中的安慰——因何而特別?嗯,因主體性。”
我們真正應該懷疑的不是詩人的沉思,而是沉思的詩人為什么這樣少?!
任何一成不變的東西都是審美的天敵
我在散步和做飯時腦子里冒出的想法要比我苦思冥想時的想法重要得多。以下就是一些無端的念頭!
a.神是對人能力欠缺的補充!人力所不能及處,神就出現了。
b.一個精選的詞就像一個從未校對過的時鐘,開創一種與常規不同的陳述方式。
c.多產若不與語言和形式的自我革新相伴隨,就是一種簡單的重復勞動。
d.任何一成不變的東西都是審美的天敵!
e.分酒器是把同一事物分給不同人的藝術。一首詩不僅是釀酒,更應該是分酒器。
f.我們從賬目上看到負數也就看到了此生的虧欠!但減少并不都是壞事,我們只有依賴負熵才能久存。
g.在寫作的高級階段,內容幾乎不是興趣點,唯有形式才有考慮的價值。一個詩人越老就越在乎技藝。
為什么要看到世界的無限?
為什么要看到世界的無限?首先,如果諸多事實中,無限也是個事實,那么,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關于世界是不是無限的,目前還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當然,也沒有任何證據予以否定。所以,對世界是否是無限問題仍是一個待定的問題。其次,迄今人類發明或發現的各種規則和規律都是基于世界的有限性而言的,如果世界是無限的,那么,這些規律和規則將被重新定義。再次,人類的求知欲促使人類自身不斷探究世界的奧秘,如果世界是無限的,意味著這種探究也將是無限的,人類不會在探究之路上止步。最后,世界的無限意味著人類生存方式的無限,人類對未來將充滿期待!
江南的刻意
江南的本質就是個性主義,而不是集體主義,或者共同體。如果說才子屬于個性的,那么,江南就是才子。上海算江南嗎?這個地方更適合培養小資,而不適合培養才子。上海的問題在于文化太模式化了。上海人的自負、驕傲都可以找出模板。但江南人的自足是沒有模板的。我把這種個性化特征說成是自私的、排他的。人們常說江南文化精致,精致是因為自私,小才能精致,大的東西都很難精致。大有大的好處,含納、寬廣。大的東西屬于時空,不屬于質料,比如金、玉之類的。在對待大的問題上,越模糊越正確,所以中國哲學都是模糊哲學、趨勢哲學;在對待小的問題上,越具體越正確,比如蘇州園林,一草一木都安放得精確妥帖。當然,小也有小的弊端,就是計較。江南的山水和文化都有些計較,你也可以說過于算計或過于用心。刻意這個詞在北方是一個貶義詞,在江南則是褒義詞。誰要是不懂得刻意,誰就不懂得江南的精髓。
疊 境
江南不是詞語的,而是圖像的。白居易說蘇州“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說的就是圖像。蘇州園林可以看作是蘇州特有的語言密碼,這個密碼核心就是圖像。網師園著名的一景“月到風來亭”也是圖像。
詞語的總有個語序次第,所以,說某個地方是詞語的一定是說某種遠近或主次的存在,比如歷史多么久遠,哪位知名人士在此居住或逗留,什么美味獲得皇帝的寵幸,等等。詞語地理往往是平面的或線性的,頭緒多,扯得遠。蘇州不是詞語的,因為蘇州不僅是圖像的,也是疊影的。相互映襯、呼應虛實、層層遞延、回味纏綿才是蘇州的風格。這樣的氣質在園林里表現得淋漓盡致。
如果說詞語的屬于時間,那么圖像的就屬于空間。蘇州的本質屬于空間。一座古城延續2500年,今天我們和古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2500年的繁華與積淀都沒有超出這座古城之外。每一物都不單是它自己,它本然地疊入到蘇州的背景里。就像我們走在小巷或園林中,我們身邊的圖景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下的,我們因為置身疊境之中而不分古今了。
在蘇州,如果體會不到古今同在就不算得蘇州真神。當然,在蘇州你如果不把自己弄丟了,陷入物我兩忘的境界,就不算入蘇州的疊境。
魔術的秘密
魔術師善于表演,他總是顧左右而言他。他說一套做一套,目的是遮人耳目,制造驚奇。高級魔術師看不出破綻,低級魔術師破綻百出。觀眾喜歡魔術無非是愿意以假為真。批評家是個討嫌的差事,他總是把魔術的秘密說破,壞了觀眾的興致。當然更不受魔術師喜歡。
原則與混沌
馬拉美是一個用頭腦寫作的人,他的過人之處不僅在于他展現出實物無形的美,還在于他有自己鮮明的美學原則,就是不用經驗和第一感官寫作。他的詩不是制造夢幻,而是為思提供了無限可能。這是偉大詩人的標志。學馬拉美的詩人很多,這些詩人中最糟糕的是對哲學思想的轉譯,最不誠實的是拒絕思想。
反對我所反對的
有一種人,他的觀點和態度只有一個,就是反對。你說什么他都反對。但你說他剛剛說過的話時,他也反對。你和他對證,這是你自己說的呀?他說反對我所反對的。西方曾批評中國的中庸文化是轉椅思維,反對我所反對的可見一斑!有人把這種思維提高到辯證法,但尼采批評說,辯證法是頹廢的沒有辦法的辦法。
裝置藝術的啟示
今天,裝置藝術打破了藝術品存在的主體性邊界,在開放和帶入性的藝術場域中,藝術不再謀求對風格的確立,即一種靠自我確立和重復來標定的特性。比如在卡巴科夫《獲得蘋果的20種方法,傾聽莫扎特的音樂》中,每一個空著的椅子都是為觀眾設置的,而可能只有唯一的蘋果屬于卡巴科夫。裝置作品在展示中完全擺脫了藝術家的控制,成為它自己的目的和動力,它拋棄了一切和成功學、功能學上有關的陳詞濫調,使藝術成為無限敞開的領域。這是人在存在的層面日益陷入各種困束后(城市化、現代化、商業化、技術化)眺望無限的一種現實處境。藝術的變化不是作為形式的改頭換面而出現,而是存在的形態和生命的樣態多元化的顯現。這意味著藝術的無限是生命存在對程式化生活的超越和抵抗,意味著對一種被忽略的隱秘的細微現實的洞見,意味著對多樣化個性的凝視和尊重。當然,如果從福柯的角度來看,這也未免不是對語言權力的有效反抗。
開端創建:回到起源
詩歌寫作進入到了一個開端創建階段,即詩人克服譜系的約束,努力從源頭建立自己的詩學。這是有責任感的詩人對寫作的擔當,也是開發語言可能性、拓展漢語的表現力和豐富性的一種冒險。寫作的這一使命性不是今天才有的,這是歷史性形成的詩人認同。相對詩歌在事件上具有的時代特征,詩歌的語言特征更具有時代的標記。同時,由語言和形式構筑的歷史敘事成為宏大敘事的一部分,正如我們今天談論史詩、悲劇一樣,語言和形式從沒有孤立于時代而存在,盡管它是超時代的,但我們總是愿意把它們視為自己的起源,視為與我們生命和靈魂夕夕相伴的東西。
在詩里,哲學不是死的
在詩和藝術的問題上,哲學并不帶來建構,而是洞穿,它相對結構的部分,更是一種離散的力量,通常人們認為哲學顯現的是那核心的東西,比如本質或靈魂,實際上哲學使唯一性瓦解在對藝術的隨想之中。我們并不是帶著要證明什么或者肯定什么的目標進入到對藝術的哲思中,相反,我們一開始就滿懷不確定的興趣和好奇心探究奇跡的存在。馬拉美認為詩歌是偶然性的產物,但在偶然性中包含了無數的思想。這里的思想僅僅是一種思維方式衍生出的語言樣態,與其說它是思維的,不如說它是感覺的、印象的、想象的,甚至無意識的。就像我們朝平靜的湖面丟一塊石子,湖面會呈現出無數擴散的漣漪。哲學的石子是漣漪的制造者,是的,我們如果從古老巫術看待哲學和詩歌的分化,就不難發現詩與哲學擁有同樣的血緣。現在,我們要做的也許不是回到巫術時代,但我們已經找到了將詩和思合而為一的路徑:一種跨界漫游!
語言始終是待解的謎
語言和我們是一種共在,語言并非先在完美(當然,對一個成熟的詩人而言,也絕不是拉康基于嬰兒心理的鏡像存在,以及所謂語言說我們這樣的被動存在),語言是在人的不斷表達中豐富起來的(喬姆斯基認為語言是人的本能,人存在深度和表層的語法結構),從藝術的角度來看,語言是被創造出來的。語法僅僅規定了語言的一般規則,在不可言說層面,語言是非法的。非法不是說不可言說的語言不需要秩序,而是說它需要一種新的秩序,即由它自身構建起的以此為范例的秩序。盡管它由詩人完成,但如果它作為一種新的語言秩序不能成立,比如符合詩意的原則或符合美的原則,那么,這個秩序就不會有語言存在的生命力。正如很多隱秘的事物我們看不到一樣,不可言說的語言依托并揭示的正是這些隱秘事物的存在。
“走路”與“舞蹈”
今天漢語詩歌存在兩個硬傷,一個是白話運動造成的語言標準下移(以大眾語言為尺度),一個是散文化(走路)造成的漢語“舞蹈”(瓦雷里語)詩性的喪失。
今天的詩歌越寫越 唆,語言膚淺臃腫,過分迷戀敘述日常瑣碎事件,這一切都是詩歌散文化的癥結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