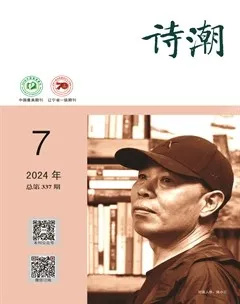詩學隨筆二題

詩,是在行動中“愛這個世界”
1963年7月24日,在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給好友肖萊姆(以色列著名學者,二人都是德國哲學家本雅明的好友)的回信中,她說:“在我至今的人生中,一次也沒有愛過某一集團或某一民族——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工人階級等這類集團,我只愛自己的朋友,我所知道的,而且相信的唯一的愛,是對個人的愛。……正因為我自己是猶太人,所以能夠觀察到某種可疑的東西,我不能愛自己或者所謂自己的人的一部分。……今天這個民族只相信自己,從這出發,還能產生什么樣的善呢?”一個人能說出這樣的話,是多么需要勇氣,尤其是對于一個猶太人來說。當一個人只相信自己,一個民族也如是,怎么能會產生“善”呢?曾經猶太人的敵人也是如此自信。人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堆人在一起,人的有限性(罪性)就消失了。阿倫特的謹慎和特立獨行是基于對人的本性的認識。
阿倫特的“善”,是沒有因為我是猶太人我就只愛猶太人,她“愛這個世界”,要知道,在猶太人眼里,不信耶和華神的人是外邦人,那個“世界”中的人,是污穢的。阿倫特恰恰要去愛這個“世界”中的人,她的言語、行為類似被猶太人厭棄的耶穌(阿倫特確實也引用耶穌的話)。阿倫特對“人”有清醒的認識,她對“愛”也有獨特的認識:這“愛”是愛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無論種族。更重要的是,她的愛,是在世界之中,是知識分子能做到的切實的行動,是從哲學到政治學的轉變。
1964年,在面對德國電視臺記者采訪時,對方堅定地稱阿倫特是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則溫和地拒絕接受這個稱號。阿倫特是哲學家這毫無疑問,她在德國求學,是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卡爾·雅斯貝斯(Carl Jaspers)等哲學巨匠的入室弟子,她寫的每部作品都清晰地顯示出她是哲學家,但她為何拒絕這個很多人企慕的稱號?
在以色列學者沙伊·圖巴利(Shai Tubali)的考察中,阿倫特拒絕的不是哲學家的稱號,她拋棄的是“學界思維”——那種“‘作為純粹活動的思考’——在很多方面是哲學的定義——漸漸地被揭示出與阿倫特自己的思考實踐漸行漸遠。阿倫特經過多年的努力開始具有了與哲學內省的關鍵距離,尤其是與海德格爾的觀點明顯不同。隨著她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她變得越來越擔憂海德格爾關注點在她看來的嚴重缺陷——自我沉迷于遠離真實世界的東西以至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絕對的自我主義,與同胞完全隔離開來’……阿倫特擔憂的是這種思考,不斷只反思自己就像一個封閉的圈子,對世界以及人與世界的關系茫然無知。海德格爾公然卷入納粹活動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尤其是1933年擔任弗萊堡大學的校長,雖然并不是直接的聯系。在這點上,他似乎確認了阿倫特的清醒認識:做哲學研究或許可能很深入,但并不自動導致思想者在世界上的道德參與。”說實話,每次讀到這段話的時候,我在想,在“學界”的我,是否正是阿倫特的擔憂。
學術研究有時可以不依賴人的現實經驗,完全作為純粹的觀念的演繹,這個紙上的世界,它依賴學者強大、縝密的內在的思想能力(“內省”),20世紀恐怕沒有人在這方面能賽過海德格爾,但阿倫特將這種“內省”定義為“返回自身,在靈魂中找到孤獨的客體”。“在她看來,內省是孤獨的:人們不再對世界感興趣,只找到一個有趣的客體,即內在的自我。在這種孤獨中,‘思考變成了無邊界的東西,因為它不再受到任何外在力量的干擾,因為不再有采取行動的要求。’當世界和行動遭到拒絕時,內省也能填滿人的生活……阿倫特覺得,這種內省傾向是她青年時期犯下的錯誤。所以她開始了遠離傳統哲學的旅程。”“通過發生在歐洲的歷史和政治轉變。她的思維類別變得更深入地與世界糾纏在一起,隨著世界的變化而變化。那是積極思考。積極思考是參與程度很高的思維方式,讓人準備好在真實世界里行動。但是此外,積極思考本身是一種行動,因為在思考行動本身,人們意識到他是有責任的世界參與者。雖然思考常常被認為是一種從世界上隱居的方式,即脫離與事件的聯系,轉向沉默的內省,但是,積極思考像承諾負責任地思考:從舒服的旁觀者視角離開,意識到只有通過參與我們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這種“與世界糾纏在一起”的“積極思考”相比,“毫不客氣地說,通常的哲學思維幾乎就像不思考”。
當我思想20世紀這位獨特的女性,讀她的文字,我想,還有什么比這些更接近詩歌呢?還有怎樣的人格比她的品格更接近我們對詩人的期待呢?如果詩不是這樣,那不恰恰應了阿多諾(T.W.Adorno,1903—1969)的話,“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嗎?
思,與詩,是不能分離的人兩種面對世界的方式。當代詩人,如何以這種“積極思考”面對世界?我們如何“與世界糾纏在一起”?幸運的是,我也常常看到一些詩人,積極地借著體察與書寫,以極為簡略、通俗但極具批判性的文字在呈現這個世界上人的真實生存狀態。他們的寫作,不是建構理想之“詩”的“純粹活動”,而是類似阿倫特那“愛這個世界”的“行動”。
注:2012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愛這個世界:阿倫特傳》,伊麗莎白·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著,譯者孫傳釗,也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書的編者。
在點贊的時代,詩是向他者和否定性的敞開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有許多對今日社會的洞見。當今的人,在一種強烈的要做真實的自我的神話之中,“真實意味著自由,不被預設的、被外界事先規定好的表達和行為模式所囿。它強迫人們只像自己,只通過自己來定義自己、書寫自己、創造自己。”“在真實性的強迫下,‘我’不得不去‘生產自己’。”這一點,我們去看看各人的微信朋友圈就知道了,誰不是在拼命地“生產自己”?
但這種“自戀的主體只是在自己的影子中領悟這個世界,由此導致災難性后果:他者消失了”。而事實上,沒有對他者的凝望或者說在他者的凝視之中,人無法認識自我,也無法形成自我。做真實的自我的神話,帶來的結果卻是“同質化的恐怖”——“人們渴望冒險、渴望興奮,而在這冒險與興奮之中,人們自己卻一成不變。人們積累著朋友和粉絲,卻連一個他者都未曾遭遇。社交媒體呈現的恰恰是最低級別的社交。”
“當今社會的特色是消除一切否定性。一切都被磨平了。為了相互逢迎,連交際也被磨平了……人們避免來自他者的任何形式的傷害,但它卻以自我傷害的方式復活。在這里,人們再次印證了這一普遍邏輯:他者否定性的消失引發自我 滅的過程。”韓炳哲引用法國作家米歇爾·布托爾(Michel Butor)的話(“十到二十年來,文學領域幾乎一片荒蕪,寸草未生。出版物如潮水般涌現,精神世界卻一片死寂。其原因就是一場交際危機。”)并認為“文壇危機的源頭乃是他者的消失”,而“藝術和詩歌的職責就在于,為感知去除鏡面屬性,使它向‘相對’、他者、他物開放”(而不是一切的寫作只是如同鏡子,“照出自己”)。

今日的文化是一種“點贊”的文化(想一想我們發圈之后對“朋友”認同的渴望和對否定性意見的惱怒),這種文化“拒絕任何形式的傷害和沖擊。凡是想要完全逃避傷害的人終將一無所獲。任何深刻的經驗、洞見皆存在于傷害的否定性之中。單純地‘點贊’,完全就是經驗的最低等級。”而詩,是對這種文化的反撥。在詩歌寫作中,人當面對他者,無論這他者是形而上學的道還是神學的上帝還是存在主義哲學的“存在”,對他者的凝望與思忖、他者給予的啟示,會給人帶來許多否定性的洞見,人才可能不斷心意更新。這種否定性雖然可能是“傷害”,但會使人更完全。詩作為一種思,因向他者開放而使詩人真實地面對人的問題,詩也唯有如此才能深刻、動人。
“詩歌的職責在于……使感知向他者開放”,這一思想要求今天的詩人不再沉溺于那種尋求某種世俗的認同與收集自我的榮耀的寫作,而是在思忖與寫作中不斷尋求來自他者的“否定性”。詩是“新鮮的荊棘”,是來自他者的對靈魂的不斷沖擊。詩人的生命因此不斷新鮮,雖然這種“開放”會使我們時受“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