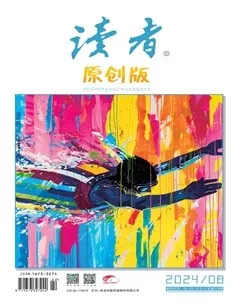我的中學
一
有事去了趟郫都區,路過我的中學西區的初中校園,還是老樣子:橙藍相間的主樓,紅色的跑道,青黃的草坪。幾個男孩正在籃球場上投籃,有人投進一個三分球,激動地吼了一聲,其他人夸完他“牛啊”,也紛紛站到三分線外,試圖證明自己也牛。
“怎么了?”身邊的朋友問我。
我才發現自己不知什么時候停下腳步,扭著頭,目光穿過灌木叢,直愣愣地盯著操場上的學生。
“我看見自己了。”我解釋說,“我在這兒讀的初中,那時也在這個球場上打球。白天打,晚上也打;和同年級的人打,也和高年級的人打。那時候我戴一口鋼牙,打球又猛,她們就給我取了個綽號,叫‘小鋼妹兒’。”
“小鋼妹兒”這綽號我已經很久沒想起過了,如果不是恰好站在母校門外,看見正在打球的中學生,我怕是沒機會再想起了。回憶就像一根掛滿鉤子的漁線,一旦拋進時光長河,相關聯的事便都咬上鉤,成串地跟著上岸了。
第一個“鉤子”可追溯至2006年,那年我12歲,該上初中了,怯生生地站在爸媽身后,等著他們給我報名。因為個頭太矮,老師問:“這個妹妹是天才嗎?看著就八九歲。”爸媽笑開了花,說:“她就是個頭小,歲數是夠的。”我也跟著笑,心情卻很復雜—“天才”聽著多不錯呀,可我并不是。
我甚至感到吃力。剛入學那幾周,我發現很多同學已經提前自學了不少內容,老師說什么他們都懂。而且他們大多是本地人,操一口地道的成都話;我一個山里的孩子,說話有口音,適應得很艱難,夜里熄燈后常躲在被子里哭。
開學兩三周后,一次晚自習,語文老師龍老將我叫到跟前,手上拿著我寫的小故事。她溫柔地夸獎我:“根據我這兩周的觀察,你和某某是班里語文基礎最好的同學,你的故事寫得很好,要繼續加油哦。”我開心地點頭,笑得兩邊的顴骨都頂到眼角了。
從那以后,似乎一切都好起來了,我找到了節奏,上課有勇氣舉手了,也有了一起打鬧的新朋友,晚上不再躲著哭,開始和室友們談天說地。我們是四人寢室,有三個是外地人,她倆對成都,對新學校,有著和我一樣的好奇和緊張。少年時期的我們容易敞開心扉,幾次夜談后,我們將對方的內心看了個遍,開始視彼此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后來呢?”朋友狡黠地笑了,“還是好朋友嗎?”
我答道:“有一個是。”我說的是阿真,我更喜歡叫她“室長”,初中三年我和她一直在一個寢室,我們又是班里僅有的托管女生,一周七天,形影不離。
像我們這樣家在外地、父母不方便每周接送的小孩,學校提供托管服務。每到周末,別的同學都回家和親人團聚、改善伙食了,我們仍然待在學校,繼續吃食堂的飯,睡寢室的床,坐教室的硬板凳。剛開始那幾周覺得委屈,打電話求爸媽來接我,或者找人來接我。不過當我和“室長”交上朋友,回不回家就變得沒那么重要了,何況龍老和Miss Ji會時不時帶我們去校外吃飯。
Miss Ji是我們的英語老師,那時她剛剛大學畢業,和她相處就像和自己的姐姐一樣親近。很多年后,我上了大學,掙了錢,得意揚揚地把Miss Ji叫出來吃飯,她開心得不行,說終于等到我長大的這天了。
說回托管。托管時,我們一般早上自習,下午打球,晚上去大禮堂看專門為托管生放映的電影。看電影得早點去占座,大鐵門一拉,我和其他托管生呼啦啦擁進去,坐一個位置,兩只手占兩個位置。“這里這里,快來!”我咋咋呼呼地朝“室長”揮手叫喊,可她從來不急,步伐穩健,表情淡然,慢悠悠走到我為她占好的最佳觀影位上坐下。
看完電影我們就回宿舍了,周末是洗衣日,“室長”喜歡邊聽歌邊搓衣服。學校那時沒有洗衣機,衣服都得手搓,照室長的慢性子,洗一次衣服至少兩小時。我洗得快,洗完了就站在旁邊和她聊天。我嘴碎,老逗她,她轉身就給我一掌。有一回甩過來一手水,我不甘示弱地回擊,她沒想到我會反抗,瞪大了眼,舀了一瓢水來潑,就這樣,我們瘋了似的開啟了一場夏日水仗。
尖叫、大笑、濕漉漉的頭發、跑落的人字拖……全留在了那個暑氣蒸騰的夜里。
“少年時期交到的朋友最好了。”朋友感嘆。
“對啊,高中時‘室長’還是和我一個班。”我說,“初中班里還有幾個同學也和我們一起升入學校的高中部,到現在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
二
我讀高一那年,到了學校南區的高中部,校服也換了。那時候我經常牛氣沖天地跟外校的朋友炫耀:“你知道嗎,我們的校服是韓劇里的那種,可好看了。”新校服看著漂亮,穿著卻難受,畢竟是小西裝,穿著不便跑不便跳,十幾歲的我覺得靈魂都遭到了束縛。不過,學校對此很人性化,只要求每周一和有重大活動時著正裝,其他時候還是穿那身舒適、寬大的運動裝,我這只小猴得以重獲自由。
“你知道升入高中后我最大的變化是什么嗎?”我問朋友。她搖頭。
“是—”我故意拉長聲音,“我不再搶飯啦!”
朋友一臉不解,我得意極了,說:“這是很重大的事!初中時我打飯在第一梯隊,每天上午最后一節課和下午最后一節課,剛過半節我的心就散了,早早地把腳伸出課桌,只等下課鈴響,瘋牛一樣沖出去,跑到食堂大廳時打飯處還空蕩蕩的,那時我特有成就感。”
初中長身體,容易餓,每頓得吃兩大碗飯;上了高中,生出愛美意識,有了少女的矜持,便不再參與搶飯競賽。唯有周四下午,我和好朋友敏敏會加快去食堂的步伐,因為那天供應餃子和雞腿,同學們都喜歡。不知道是大鍋烹飪的原因,還是學校廚師有什么秘方,畢業后我再未吃過類似的餃子。
“很好吃嗎?”朋友問。
“其實一般。”我說,“那時天天炒菜米飯,只有一天是餃子和雞腿,顯得珍貴。”
同樣珍貴的還有體育課后的煮玉米蘸辣椒、超市“限量銷售”的老壇酸菜牛肉面,以及每周日晚上室友從外面館子里帶回來的“珍饈”。我在高中長高的每一厘米,都有它們的功勞。

個頭在長,心智也在長。上了高中,對于世界和自我的認知開始發展,腦子里全是問題,心中堆滿情緒。父母遠在千里之外,很難及時紓解我的負面情緒,但我還算平穩地度過了那個時期,因為身邊有很多敏敏這樣可愛又靠譜的朋友。
此外,我還擁有一個簡單、團結的班級。官官是我們的英語老師,她性格開朗,教學有方,我們都非常喜歡她。官官的英語課不像上課,像游戲,一場所有人都快樂參與且投入的游戲。你能想象嗎?到了高三,我們還會為爭搶回答問題的機會而“吵翻天”。我記得外號叫“校長”的同學在這頭拍打課桌,聲嘶力竭地吼:“選我!選我!”我的好朋友敏敏在那頭一蹦一跳:“不,不!選我!”其他同學呢,有的笑著看戲,有的加入各自的陣營:“選她!”“選他!”
我們學得熱情,玩得起勁,經常給官官制造一些驚喜(對她來說可能是驚嚇),比如趁她來之前把燈關了,所有人躲到課桌下面,官官開門看不到一個人,就靠在門邊,又好氣又好笑:“你們想咋子嘛?”
“唱歌!唱歌!”小孩們從桌下鉆出來,像調皮的地鼠。
“你們好煩哦。”官官這樣說,但兩分鐘后我們便沉溺在她優美的歌聲中。她很寵我們。后來我們再關燈,其他老師從窗戶外看到我們班漆黑一片,就對官官努努嘴,幸災樂禍地說:“你看,你們班又黑了哦。”
“那你們班英語成績好嗎?”朋友很驚訝,在這樣的班級,學生真的能學習嗎?
“當然!高考英語平均分超過120呢!”我得意地揚了揚下巴。
三
在中學的6年,我很少因為學習的事焦慮,一邊學,一邊玩,成績也還過得去。偶爾考得不好,老師們鼓勵兩句,同學們結對幫扶,沒掉幾滴淚便投入下一輪學習了。到了下回考試,可能考得好,可能不好,都不那么重要,因為我們知道,學習是一條沒有終點的路,能學下去才最重要。很多年后,我意識到,初中時學校“不以成績為唯一評價標準”的學習氛圍對我影響很大,我不僅在西區學到了知識,還學到了獨立、友情、真誠、堅韌,學到了多維度地看待一個人,學著變成一個完整的人。
“你肯定很想念西區。”朋友這次沒用疑問句。
“前兩年我做過一個夢,夢到初中的班主任羅老突然宣布,官官不當我們的英語老師了。實際上官官是高中部的老師,現實中他們沒什么交集。”我說,“但是,我在夢里哭得死去活來,我難過啊—官官不教我們了,我們班就不是我們班了。”
“你害怕失去。”朋友頓了頓,“過了這么多年還在怕。”
我像是被戳破秘密的小孩,癟著嘴,不情愿地承認道:“大一的時候最怕。因為那時,中學時的同學都有了新生活,我也有了。但我還是不愿意也不希望分別來得那么快,即便大家已經完成了物理意義上的分別。”
我記得那時候我找初中語文老師龍老傾訴。她告訴我:“不要把對自己的要求強加到別人身上,你做得到的別人不一定做得到,每個人對彼此間關系的定義不同,處理方式自然也不同,你只要做你自己想做的。”我似懂非懂,但從那以后,我真的不再苦苦等待中學朋友的消息了,不再生她們的悶氣,開始全情投入大學生活。我在心里完成了和中學真正意義上的告別。
“但其實沒有完全告別吧?”朋友突然說,“你仍然和很多老師保持著聯系,當初的朋友大部分如今仍然是好朋友,雖然不能常常見面,但見面時就像在中學時一樣,最丑的樣子可以讓她們看,最深的秘密可以跟她們說。”
我很驚訝:“你怎么知道?”
“因為我就是你。”
我轉頭看向“朋友”,是的,她就是我—扎著馬尾被誤認為是“天才”的我,箍著牙套在球場上橫沖直撞的我,梳著齊劉海能吃兩大碗飯的我,扭捏地穿著西裝裙的我,運動會上大汗淋漓的我,在食堂把一張紙巾分成7份發給朋友的我,把官官背起來在走廊上奔跑的我,和大家一起唱《當》的我,挽著敏敏的手跨過18歲成人之門的我,最后一堂英語課上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我,背著行李和送行的朋友揮手的我……
在中學度過的時間穿過我的身體,覆蓋了我,一束束五顏六色的光,重疊著,閃耀著。
“我好想你啊!”我對身邊的我說,“我好想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