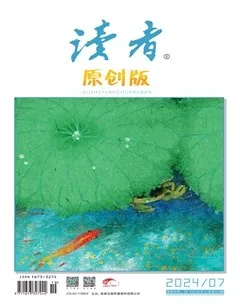“姑姑”是個神奇的詞語

最近在看一些跟自梳女相關的資料。有個觀點是自梳女群體中的姑侄關系往往格外緊密。為什么呢?
自梳女是清末民初出現在嶺南地區的一個特殊女性群體,她們自行束髻以示終身不嫁。之所以在當時的嶺南地區出現,簡單說就是她們有錢,或者說有機會有錢。
在當時,女性不嫁出去就等于要與娘家兄弟爭奪土地,宗族是不會同意的。但有了工商業,她們就可以在不與娘家兄弟爭奪農業資源的情況下,維持自己的生存,甚至幫扶家庭。因此,自梳女才會形成規模。
比如彼時的順德地區,繅絲業發達,需要大量女工,且女工收入很高。繅絲業沒落后,這些女工依然有很好的謀生方法—她們廚藝卓越,很適合下南洋當幫傭。
下南洋當幫傭的女性,多數會加入自梳女群體,而且大多是由姑姑帶著侄女加入,或者姑姑先到南洋,侄女過來投奔。
所以這里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姑姑對侄女的影響。
事實上,并不僅在自梳女群體中如此,普通家庭中,姑姑對侄女也很容易產生影響。有一些文學作品會以這種關系作為主題,比如以寫女性關系為主的加拿大作家艾麗絲·門羅,她起碼有三四篇以姑侄關系作為主題的作品。
比如,《我媽的夢》。
“我”作為一個小女嬰,不接受母親吉爾,卻莫名親近姑姑艾奧娜。“我”不喜歡母親的乳房,反而“艾奧娜和她手里的奶瓶,成為我選中的溫床”。對于這個女嬰,所有的時間分為:“艾奧娜時間”和“非艾奧娜時間”。
艾奧娜本來是這個家庭中的最底層,一個犧牲品,一個傳說中的“扶弟魔”。她為了弟弟喬治(也就是“我”的父親),放棄了自己的學業,一直單身,甚至放棄了整牙,省吃儉用地供喬治讀法學院,結果喬治報名參軍,遠走高飛,在戰場上送了命。
吉爾作為遺孀進入了這個家庭。“我”出生后,艾奧娜被“我”選中,只有她能讓“我”平靜。于是艾奧娜瞬間變了,她“好像終于走出了青春期”,她不再怯懦,不再害怕任何人,她變得強悍,“大權在握的快感以及感激之情讓她心跳加速,快樂得想起舞”。
可以想象艾奧娜有多么愛這個小女嬰—原文中用“迷戀”來形容。
另外一篇姑姑對侄女影響至深的小說是《傳家之物》。
姑姑阿爾菲達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單身女性,雖然長得并不好看,但是她有一種魔力,是傳說中的職場女強人,在報社工作。她坐在餐桌上的興趣在于交談而不是食物,她談論天下大事,談論政治,與父親辯論。對于“我”這個侄女,她則談論她所生活的那個城市的一些名人,講他們舉止失范的野聞逸事。阿爾菲達的牙齒很不好看,但當其他姑姑談及這點時,“我”認為她們總是把阿爾菲達的智慧和風尚棄之不顧,而偏偏盯著她的牙齒。
智慧和風尚,這就是當時的“我”對這位姑姑的印象,包括她住公寓,也意味著一種非常文明的生活。“我”深受她的影響,“幾乎像阿爾菲達一樣自由自在,由著自己的性子盡興發揮”。
但當“我”像阿爾菲達那樣到了城市去讀書生活,便對阿爾菲達的生活袪了魅,甚至覺得那有些潦倒可笑。更重要的是,阿爾菲達不再是單身了,她的房子“散發出遮遮掩掩而揮之不去的氣味,顯露出羞愧而倔強的模樣,與女性領地迥然不同”。
就在這個不再單身的姑姑家里,姑侄之間產生了某種奇怪的敵意。當“我”抽煙時,她說:“看來我帶給你的壞習慣還在。”但“她或許已經想起來,我不再是個小孩子了,我不是非要待在她家里的,以我為敵毫無意義”。
這里有個重要的反轉,姑姑對侄女的榜樣作用失去之后,兩人之間出現了莫名的敵意。姑侄變成一對微妙的敵人。接下去這些反轉還在持續地產生,“我”成為一個小說作家,發表的小說被阿爾菲達讀到,她辨認出自己是那個小說的原型人物,小說中包含一些她帶創傷的隱私和故事。
必須說,這種敵意恰恰正是愛的另一種形態。它依然是姑姑對于侄女的某種作用力,異乎尋常的作用力。有多少敵意,就有多少愛,原文中的描述是:“阿爾菲達的愛,那愛有如雪泥一樣難纏,不合時宜且無可救藥。”
除了愛麗絲·門羅,中國文學史上也有一對著名姑侄,是張愛玲和她姑姑。張愛玲的“姑姑語錄”已成典故,這是很多讀者所熟悉的。
在我看來,姑姑和侄女的結盟,屬于“同類項合并”:
她們同為女性,嫁入夫家后,在夫家始終都是外來者,但在原生家庭中,她們又都是會嫁出去的人,所以也是“外人”。也就是說,不管在將來的家庭還是在原生家庭中,她們都有不安定感。雙重的不安定感,使她們在無意識中惺惺相惜。
甚至姑姑對侄女的影響會比母親更多。因為母親對女兒來說,一開始就是一個已婚婦人的形象,而姑姑則未必。不少文學作品中的侄女能看到姑姑單身時的狀態,同為家庭中的另一個未婚女性,她就很可能成為侄女的榜樣。
姑侄關系不像母女關系和姐妹關系那么多地被關注、被討論,但它有那兩種關系所沒有的一些維度。尤其是未婚姑姑與侄女的關系,往往會以意外的方式讓人意識到,女性關系的復雜和幽深的確難以窮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