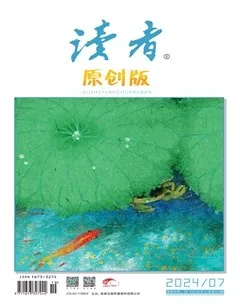皮影守業人:我這輩子都放不下皮影了
2024年1月1日清晨。
陽光穿破云層,灑落在甘肅環縣丁楊渠子村。
連綿起伏的大山包裹著空寂的村莊,泛著白霧的寒氣籠罩在上空,幾縷炊煙裊裊升起。
6點59分,魏宗富隨意套上一件藍色舊毛衣,睡眼惺忪地打開“快手”,開始了新年的第一次直播。美顏功能讓他白得不太真實,但額頭的6道皺紋,仍然深如刀刻斧鑿。
比起安靜的村子,魏宗富的直播間更熱鬧。粉絲似乎聽得懂甘肅方言,對魏宗富說著新一年的祝福。
47分鐘后,魏宗富便匆忙下播,帶著戲班趕往平涼市。他要參加一個樓盤的銷售活動,連續演三天皮影戲。他答應粉絲直播演出現場。
清瘦、黝黑的他看起來與普通莊稼漢并沒有什么不同,尤其那雙粗糙、布滿老繭的手。但村里人知道,魏宗富和他們不一樣。
他參演過紀錄片《大河唱》,曾受邀出國進行交流演出,接受過多家媒體采訪,在“快手”擁有22.4萬粉絲,這些光環承載著他的另一個身份—環縣道情皮影傳承人。
世居黃土高原的他,大半輩子羈絆在皮影里。
時代在發展,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與魏宗富一樣的皮影藝人,仍以守業人的姿態,挺立在西北大地。
一邊是生存壓力,一邊是對皮影戲的深厚情感,他艱難地選擇了皮影戲。他用力地活著,把平凡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以下是魏宗富的自述。

“放了兩年羊,爺爺才叫我演皮影”
咱這兒的農村都說虛歲,我今年57歲了。從12歲動了學皮影的心思,14歲正式學藝,我跟皮影戲糾纏了40多年。
一塊空場地,一口木箱,一塊白色幕布,就是一臺皮影戲。將道情與皮影結合,加上具有地域特色的唱腔,就有了環縣道情皮影。
皮影戲《賣道袍》是由我太爺爺傳下來的,興盛班是我太爺爺創立的老班子,往前追溯有100多年了。
我太爺爺魏國誠,是清末道情皮影大師解長春的四大弟子之一。我爺爺叫魏元壽,也是皮影藝人,環縣的100個皮影藝人中,有70個是我太爺爺和爺爺的徒弟。
我還沒出生時,我的父親就因為一場意外去世了,母親另嫁,從小就是爺爺和奶奶帶著我和兩個哥哥。
第一次看皮影戲,是六七歲的時候。當時演的是《大鬧天宮》,人太多,看不見幕后,只能看見孫悟空動來動去的,覺得特別有意思。看了兩三場后,我才知道是爺爺在幕后操作,我喜歡得不得了。
我該上三年級時,就想跟爺爺學演皮影戲,日思夜想。那時候爺爺的戲班也很知名,邀請他演出的人特別多。
可他說啥也不讓我學,說這個行當太累了。那時候小,爺爺說的話,我一句也聽不進去。
爺爺常年在外面演出,一年四季不停。爺爺不在家,我就逃學,他回來就拿棍子追著打我。我抱著書包往山溝里跑,躲1zFzOaA4J/claTVbyXYi5dqtfa5wrzbs/NUKAg4qRPE=一會兒,再偷偷溜回來。
實在沒辦法,爺爺就買了幾只羊,讓我放羊,其實就是逼著我回去念書。
每次去放羊,我都會背上水壺和嗩吶,羊在旁邊吃草,我就靠在樹旁吹嗩吶。附近參加廟會的人問是哪個娃娃在吹嗩吶,有人便說是魏元壽的孫子,他們就說這小子一定能成為好藝人。
放了兩年羊,我一直沒妥協。奶奶就跟爺爺說:“不要再讓他放羊了,讓他學門手藝吧。”爺爺實在拗不過我,終于同意了。
爺爺看我對皮影戲是真的熱愛,就想把我教好。從漁鼓簡板、甩梆、四弦、竹笛,背戲文,一直學到前臺。學藝的過程是真的苦,也特別枯燥,但我還是硬撐下來了。
后來戲班缺人,爺爺就讓我上前臺。前臺是戲班的靈魂和核心人物,一個人既要演唱、道白,皮影挑線,還要指揮后臺。我的嗓音粗獷,聲音透著滄桑,表現傷音的時候也挺突出,演了幾次后,爺爺就決定讓我帶一個戲班子。
爺爺給我準備了兩個大箱子,一個裝皮影,叫線箱;一個裝樂器,叫角箱。走到山口時,他帶著幾個人去左邊的村子,我帶著幾個人去右邊的村子。
16歲,我成了興盛班的班主。
“我第一次出國演出,太光榮了”
那時候,去村里演出,一般就在窯洞里唱戲。
吃完晚飯,各家各戶就拎著小馬扎,早早來窯洞占位置,生怕來晚了沒地方。唱完一本戲要到天亮,陽光照進窯洞,觀眾才盡興離開。
皮影戲輝煌的時候,一場的觀眾至少兩三千人。那時候沒有車,很多觀眾都是走十幾里路來看戲的。人最多的時候,一場能達到四五千人,感覺附近各個村的人都來了。
每次演出時間都很長,但我一點兒也不覺得累。那么多人喜歡皮影戲,感覺還挺自豪,特別帶勁兒,發揮得也好。
以前的觀眾都很懂皮影戲,一旦唱錯了或者把人物搞錯了,他們會馬上糾正你。

那會兒看皮影戲感覺還挺時髦的,但就算再火,也只是火在家門口。我爺爺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天能去國外演皮影戲。
2003年,我正式成為環縣道情皮影藝術家協會會員。
2006年,道情皮影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我感覺皮影藝人的地位更高了,走出去更受尊重了。
我們興盛班的唱本戲有60多本,《賣道袍》《六合圖》《福壽圖》等都經久不衰。環縣經常組織皮影戲會演、比賽,我們也拿過好幾次大獎。
因為皮影戲,我還認識了音樂人蘇陽。
2008年元宵節,十幾個皮影戲班在環縣縣委門口輪流表演,我演的是興盛班的拿手好戲《賣道袍》,被蘇陽看到了,這讓我有機會參與他主演的大型音樂紀錄電影《大河唱》的拍攝。
拍攝《大河唱》的時候,我們戲班曾受邀去上海演出。那天晚上,我站在黃浦江邊感慨,要不是因為皮影,怎么有機會來上海呢?
后來,我又參加了北京傳統音樂節,在北京音樂廳清唱了道情皮影戲《賣道袍》。
2011年10月,我還受邀去澳大利亞演出。那是悉尼市政府主辦的文化交流活動,由環縣文化館館長王生亮帶隊,一共7名皮影藝人,在悉尼的海關大樓演出,我負責前臺。
我人生第一次出國演皮影戲,簡直是太光榮了。我們穿著西服,領帶一打,顯得特別精神。我還花了220塊錢買了一雙紅皮鞋,當時還是借的錢。
沒想到,演皮影戲還能出國。從我太爺爺開始算起,我是第4代皮影戲傳承人,我在家族里不是演得最好的,可我趕上了好時代,享受到了皮影帶來的榮光。
從來沒想過,皮影戲能讓我的人生這么精彩。
“不能在我這一代斷了命脈”
我們這里的皮影藝人大多還是以種地為主。我家有30畝地,就拿種玉米來說,一畝地也就產1000斤左右。
我是1991年結的婚,一年之后就發現,皮影戲的臺口不如以前了,看戲的人越來越少。人們的娛樂方式變得越來越多以后,鄉村的集體生活就少了,看這些古老的傳統藝術的人也少了。
沒有演出,心里發慌,村里的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我也想過要不要放棄皮影戲,出去打工。可老一輩人交到咱手里的東西,等于把“命根子”給我了,我要是沒有傳承下去,是要遭唾罵的。

小時候,爺爺總跟我說,皮影是個好東西,想方設法都要傳承下去。可爺爺不知道,皮影戲也會經歷沒落啊,我也沒辦法。沒有演出收入,我只好去給人家打零工、干農活,一天賺幾十塊錢。
但是我放不下皮影,去打工也帶著樂器,閑暇時給農民工朋友表演一下,或者清唱一曲,過過癮,就特別開心。
最近幾年看皮影戲的人更少了,一場觀眾就二三十人,大型活動也就100多人去看。觀眾大多是“50后”或者“60后”,年輕的有幾個,也看不太懂,就是湊個熱鬧。過去演一場戲最少5小時,現在演一場也就一小時。時間太長,觀眾就坐不住了。
我陸續收了四五個徒弟,都是因為賺得少,放棄了。這我都能理解,喜歡歸喜歡,但學一門技藝,得先解決生存問題。
我們這些傳承人,都快成“活化石”了。等我們這些傳承人都去世了,這個東西就失傳了。一想起這個我就心急如焚,晚上睡不著覺,終日想,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太幸運了,我又找到了一個新舞臺”
2018年,算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我找到了一個新舞臺。
那段時間演出少,我很郁悶,女兒給我下載了“快手”,讓我直播演皮影戲。我一開始不喜歡,也學不會,可演著演著,竟然上癮了。
差不多每天晚上8點直播,唱折子戲,有時候會唱兩折,一折《賣道袍》,一折《十上香》。
我老婆跟我一起唱,因為皮影唱腔需要女的,也找不到合適的人,她就跟著我學了,也算是對我的一種支持吧。每次直播觀看人數都有兩三千人。
我還跟著《大河唱》的導演楊植淳學會了制作短視頻,加字幕。山里信號不好,有時候時長兩分鐘的視頻,要上傳10多分鐘,但我還是堅持更新。
很多人通過“快手”認識了我,也因此喜歡上了環縣道情皮影,我的粉絲從一開始的幾人、幾十人,一直漲到現在的22.4萬人。
以前我們都是在環縣演出,大多都是在廟會上演。現在我的演出舞臺就不僅限于環縣或者甘肅省了,我有了去北京、新疆、四川等地演出的機會。以前演出只能步行,用驢子馱道具,稍遠一點兒的地方就去不了。后來我們用機動三輪車馱道具,戲班子其他成員騎摩托。現在有了汽車,去平涼也就幾個小時。
2019年,我去河北廣播電視臺做節目;2020年,我參加了央視春晚紀錄片的拍攝;2021年,我接受了《中國青年報》等多家媒體的采訪。
我把這些經歷都整理出來,用A4紙寫了滿滿三大頁。以前我不太會寫字,后來抄戲文,抄了40多本,每本都是3萬字,字也寫得順溜了。
小時候爺爺總跟我說,皮影這個東西能給你帶來好處,你把真本事學會,總有出頭露臉的一天。當時我年紀小,不太懂這些話,近幾年才發現,爺爺早就把皮影的價值看透了。
很多人給我發私信,說看見我的皮影戲就特別想家,想念家里的老父親。他們說我的鄉音味兒正,還有很多人說想來找我,要跟我學皮影。也有人說,這個皮影幾十年沒變,看久了覺得乏味,說這些傳統的東西,也得跟上時代潮流。
只要是關注皮影戲,說啥我都愿意聽。
祖先傳下來的清代皮影箱,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著,尋找傳承人的事我也不敢耽擱,興許通過網絡,能找到真正喜歡皮影戲的人。
擇一事,終一生!反正我這輩子是放不下皮影戲了。
(撰文:魏艷麗,圖片:快手藝術創作者—魏宗富,道情皮影傳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