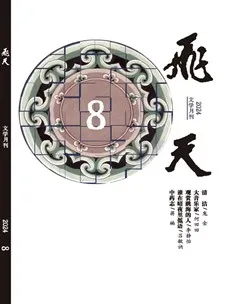暮年辭
溫海宇,1982年生于安徽,居深圳。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小說、散文、書評見于《作品》《廣州文藝》等刊物,有作品入選高中語文考試閱讀題,曾獲第二屆全國青年產業工人文學獎。
一
黃鸝子一叫,麥子即將迎來收割。空氣中有了微微的麥香,孫氏的鼻子捕捉到這麥香,她不由得抬起頭來,眼睛朝當院里那棵枝葉繁茂的梧桐樹頂端尋覓著,她覺得黃鸝子就應該藏在那里,她斷定黃鸝子的聲音是從那里傳來的。她瞅了半天,脖子都酸了,也沒有發現黃鸝子的蹤影。孫氏雖然八十三歲了,身體卻好得很,眼不花,耳不聾。她能睡,也能吃,一日三餐頓頓都不落。年前,孫女出嫁,她給孫女縫棉被做嫁妝時還能穿針引線,這就足以說明她具有良好的視力。此刻,她對自己的眼睛足夠自信,既然沒有看見黃鸝子,它們一定不在當院里的梧桐樹上,肯定是飛到其他的樹上去了,而且那樹離她也不會太遠,否則她不可能聽得如此真切,猶在耳邊。
孫氏說:“真能,你這個小舅子藏得怪嚴謹。”這個“小舅子”不是指別人,指的當然是黃鸝子。
村里年輕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沒有什么人可開口交流的。孫氏就經常自己跟自己說話。
燒鍋時,她跟鍋說話,她說:“你這口笨鍋,讓我說你什么好呢,怎么老也燒不開呀,太費我的柴。”
她鉤香椿芽時,跟香椿樹說話,她說:“香椿樹,你又發芽了,我原本也不想鉤你,可孩子們嘴饞,怎么辦呢,你多擔待吧。”
連陰雨時,她跟雨水說話,她說:“我的老天爺,咱可不能再下了,你看看現在都溝滿壕平了,再下,咱這地方準要鬧災荒,你開開眼吧。”當然,她也跟鳥說話。
細究起來,孫氏是有確切名字的。她身份證上寫的是孫素貞,實際上沒有多少人知道她叫這個名字。村里人稱呼上了年紀的女人,都是誰誰家的,誰誰的娘,誰誰的奶奶等,不常用的真名反倒生疏了。名字對孫氏來說似乎并不重要,她一輩子都沒有出過遠門,去得最遠的地方是二十公里之外的縣城,是大孫子開車接她過去的。大孫子的家安在了縣城。她總共在大孫子家沒住幾天,覺得一切都不習慣,就嚷嚷著要回來。她老惦記著家里的那條黃狗、六只母雞和兩只鵝。盡管她走時將它們委托給鄉鄰,可她對鄉鄰是一百個不放心。不是自家的東西,沒有人會盡心盡力照管的,她總是這樣想。大孫子受不了她無休止的絮叨,只好開車將她送了回來。回了家,住進了她那三間破舊的紅磚瓦房,見到了她的狗、雞和鵝,她心里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
大孫子調侃奶奶,說她沒有享福的命。大孫子認為,接奶奶到縣城來,不讓她干活,也不讓她出力,孫媳婦還主動為她洗澡擦背,衣服也給她常換勤洗,好吃好喝侍奉她,這難道還不舒坦嗎?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縣城的條件都優于鄉下。他實在想不通奶奶為何在縣城總是待不住,總想著要回鄉下的那個家,而且態度決絕,不容商量。
孫氏倒有自嘲的勇氣,她對大孫子說:“你說得對,你奶奶原本就沒有享福的命,一輩子都在鄉下生活,習慣了。我不認為縣城有多好。再說,你們還要上班、養娃、還房貸,辛辛苦苦夠不容易了,我可不能再給你們添麻煩。”大孫子聽后,嘆氣無語。
孫氏的老伴兒幾年前患癌癥去世了。起初,兒孫們很擔心她的情緒,怕她孤單,更怕她想不開,出什么亂子。在農村有太多這樣的例子,通常是老伴兒走后,另一個老人不多久也會跟著去了,這幾乎成了一個規律。孫氏卻是個例外,對于老伴的病故,她曾傷心過好一陣子,大概一年多吧,她就從消沉的情緒中走了出來。
此后,孫氏竟然還種了兩年的地。在外打工的兒子兒媳實在看不過去了,跟她商量,希望把耕地轉租出去,她卻舍不得。
孫氏說:“咱家的耕地每年能收一萬多斤小麥呢,還不算秋季的收成。瞧瞧,這多喜人!”
兒子說:“俺娘,您也不看看您多大年紀了,咱得服老不是嘛。這兩年咱家的耕地是您守著不假,逢著收莊稼的季節,還不是全家都從外地趕回來?挺折騰人的。我們在外打工的打工,干生意的干生意,也不比收種莊稼掙得少嘛。再說,您這么大歲數,還在家守地、種地,萬一有了閃失,我的脊梁溝子會被人戳破的,丟不起那人。”總之,兒子頗費了一番說詞,孫氏才勉強同意答應不種地了。
孫氏身體還不錯,她留在鄉下,全家人似乎也放心。
二
今年的麥子長勢喜人,豐收在望。麥子開鐮收割的時候,孫氏喜歡去看大型聯合收割機橫掃麥田的壯觀景象。她第一次見到這景象的時候,簡直驚呆了。大型聯合收割機像只巨獸,“食量”大得驚人,所到之處,成片焦黃的麥子被它卷入“嘴里”,同時麥粒就像下雨一樣從另一個方向噴射出來,匯聚在一起,呈現出顆粒歸倉的喜悅。這喜悅不僅關聯著豐收,還有對科技的感激,對大型聯合收割機的感激。早些年,收割麥子是件繁重的體力活,一場收麥季忙下來,人會瘦下幾斤肉。磨鐮刀、割麥子、裝麥子、拉麥子、造場地、壓麥子、起場、揚場、晾曬……每次想到這些,孫氏就生出無限感慨。到底是時代不同了,莊稼人不再受累,個個成了享福者。就這,大家還是不愿意種地,她是百思不得其解。
孫氏在深夜跟老伴兒絮叨,老伴兒雖然到了另一個世界,她卻堅信他一定能聽到。她也覺得自己的絮叨討人嫌,但就是忍不住。她對老伴兒的絮叨從她嫁過來那一天就開始了,她絮叨他抽煙、喝酒沒個節制。絮叨他講話沖、不懂人情世故。絮叨他不拘小節、邋里邋遢……老伴去世時,孫氏倒也哭過,但她的哭里悲傷的成分少,抱怨批判的成分大。她邊哭邊訴,老伴兒的一件又一件糗事就被她重新數落一遍。
“年輕時不讓你喝多你偏要喝多,這回喝出毛病了吧,喝死了吧。”孫氏哭道,“醫生老早就叫你戒煙,你不聽,偏偏還要吸,一天一盒,一天一盒,任誰都勸不住,你是一點都不虧,該這樣。”說完,又哭了一會兒,慢慢就從抱怨變成無盡的惋惜。“早些年,家里窮,人家看不起咱,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也舍不得穿,現在子孫滿堂,孩子們的日子都過好了,按說你也該享享福,可你的身體偏偏不爭氣,你的心就恁狠,撇下我就走了。”她繼續啜泣,“你這個沒心沒肺的家伙,人家咽氣時總要交代交代后輩,安排安排后事,你倒好,金口難開,你是一句話也沒留下呀,你怎么能這樣呢?”……
孫氏沒完沒了地哭訴,一旁的兒子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兒。他理解娘,知道娘對爹的感情都藏在那一句一句的抱怨里了,這也許是上輩人表達情感的方式,娘的抱怨何嘗不是對爹的另一種愛呢?他不打算安慰哭天搶地的老娘,任由她無休止地哭著,哭多久都成。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排解她內心的苦楚。
孫氏只有一個兒子。兒子成家后,兒媳為她家生了兩個孫子,一個孫女。起初,兒子兒媳在深圳工廠打工,頭兩個孩子就成了留守兒童,那時的孫氏夫婦還算年輕,他們有精力帶娃,能照顧得來。后來,兒子兒媳離開工廠,他們在深圳開了一家廢品收購站,遠比打工強多了。他們憑著這個外人看來毫不起眼的營生,竟然在深圳買了一套一百多平米村委統建的樓房,總算在城市扎了根。就在這時,他們生下了小兒子,回老家辦了一場風風光光的滿月酒。孫氏夫婦高興得很,特別是老伴,逢人就說他家的喜事。家中添了男孩,說明家族人丁興旺,他樂得嘴都合不攏了。滿月酒辦完,老伴一個人又獨自喝了三天的大酒,孫氏有些不悅。酒沒有這么喝的,無奈怎么勸他都不聽,他理由十足:“我又得了個孫子,這是多大的福氣呀!你可別煞風景,我必須慶祝,我也必須要喝。”兩個必須,說得斬釘截鐵,不容商量。孫氏無奈地搖搖頭,只好任他喝去。兒子兒媳商量后準備把小孫子帶回深圳撫養。他們之前的一雙兒女已是留守兒童,現在他們條件好很多,也在那邊安了家,不能再走老路,他們要把小兒子帶在身邊,要參與他的成長。對此,孫氏夫婦并不反對。
大孫子和孫女對爺爺奶奶的感情很深,對父母的感情卻很淡漠。特別是他們的弟弟出生之后,父母回家的次數越來越稀少了,有時連著幾年才回來一次,他們對父母不可能產生多少感情。他們覺得被父母忽視了,那種感覺一直伴隨著他們的童年、少年。孫氏記得,大孫子有段時間對母愛流露出異乎尋常的渴求,有一天,他竟然幼稚地對孫氏說:“人家都有媽媽,為啥我沒有?以后我不想喊你奶奶了,我要喊你媽媽。”大孫子的這句話,讓孫氏感到可笑,同時心里又生出一陣辛酸。她緊緊地抱住大孫子,哽咽著說不出話來。
大孫子和孫女雖說是留守兒童,孫氏夫婦對他們的愛是無微不至的,甚至超越他們的父母,生活上從未讓他們受過委屈。大孫子讀的是大專,物流專業,畢業后在縣城一家快遞公司上班,已經結婚生子。孫女呢,從小文靜聽話,很愛學習,考上了本省的一所師范大學。畢業后留在了本市學校教書,年前剛剛嫁人。她丈夫也是個教書的,大高個頭,面相白凈,愛說笑,脾氣挺好。他們郎才女貌,挺般配的。他們在市里買了婚房。孫氏常想,假如老伴兒還活著,看到這一切,他該有多開心呢?這兩個他們帶大的孩子,都受到了高等教育,且具備很好的品行,這一切得益于他們的悉心養育,得益于他們的言傳身教。這挺了不起的,孫氏為此感到欣慰和自豪。
近些年,孫輩們陸續成了家,回來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了。孫氏的情緒有些低落,她覺得自己越活越沒有出息。很奇怪,她不大想遠在深圳的小孫子,卻對從自己身邊出去的兩個孩子牽腸掛肚,總盼著他們能常回家看看。
盼著盼著,他們果真回來了。雖然相聚短暫,她已是很滿足了。他們離開時,孫氏給他們準備的薺菜、蒜苗、椿芽、槐花等一股腦兒被他們打包帶去城里。這是孫氏最快樂的時候,是她滿足了娃子們“嘗鮮”的愿望。再說,他們愛吃這些,至少說明他們沒有忘本,心里還惦記著這個家。
又到了收麥子的農忙季,她的兒孫們也該回來了。她一直認為這兩者有著必然的聯系,她的思維還停留在早些年家人趕回來收麥子的階段。后來,在大型聯合收割機的轟鳴聲里,她才慢慢想明白了,他們家的地都租給了種糧大戶,他們家早就沒地了,收不收麥子跟他們家再也沒有啥關系。當孫氏意識到這些時,她的心里突然涌起一陣莫名的失落。
三
黃鸝子的叫聲婉轉悠揚,那聲音如高山流水般清亮。空氣中成熟的莊稼味道讓孫氏沉醉。東南風一陣一陣裹挾著麥香,拂過她的臉頰,有些酥癢,也有些撩人。這些風呀,還是太調皮了,它所到之處皆是溫柔,皆有暖意。那些長出新綠枝葉的樹木發出沙沙的聲響,似輕言細語。孫氏的耳朵聽得真切,卻又懵懵懂懂,她有些走神。
孫氏正安坐在院子里給自己梳頭。她的頭發幾乎全白了,也略顯稀疏,梳起來并不費勁。那把大如巴掌的桃木梳是老伴送給她的,那年,老伴去北鄉販賣糧食,在一個廟會上看見有山東人在賣桃木梳,那些桃木梳看上去既細密又精致,很有質感,一看就是用老木制作的。他就給孫氏買了一把,告訴她這梳子不僅結實耐用,還能辟邪氣。孫氏接在手里,掂量掂量,果然很喜歡,她還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壓手的桃木梳。這把梳子是老伴這一生送她的唯一禮物,她當然金貴得不行。用了幾十年,它保存完好,梳齒沒有絲毫殘缺,脊背上早就光滑油亮,顯然是有了包漿。每次拿出這把木梳,孫氏心里就會生出只屬于她自己的那份淡淡的喜悅,用它梳頭時,一根根光滑的梳齒劃過頭皮的感覺仿佛老伴年輕時的手指,柔韌又有溫度。老伴年輕時沒少給她洗頭,她那時的頭發烏黑油亮,特別的多,多到一個人都不太好打理,老伴就給她洗頭、梳頭,這使得孫氏的妯娌們異常羨慕,她們的男人何曾給她們洗過頭?這讓孫氏心里很受用。不知從何時起,她的頭發漸漸失去了光澤,隨后一根又一根的白發接踵而至,慢慢黑少白多,也稀疏了許多。她也許就是這樣老去的,伴隨著她老去的還有這把桃木梳。
孫氏緊緊地攥著桃木梳,猶如握著老伴寬大的手。她跟老伴真是好久沒有說過話了,她多想跟他再絮叨絮叨。她知道老伴一定是厭煩了她的絮叨,但她不管,她就要跟他絮叨。這會兒,她像個任性的小丫頭,一會兒噘起嘴,一會兒又咧嘴笑。她知道老伴不愛聽,那可不行,不愛聽她也要說,她偏要說。
“老頭子呀,你這個沒良心的家伙,本來說好我要走在你前面的,你倒好,跑得比我還快,你為啥不能等等我?你走后,冬天,再也沒人給我洗腳、暖被窩了。夏天,再也沒人給我搖蒲扇、趕蚊子了。現在一年四季,都是我自己做飯自己吃,再也沒有人給我燒鍋了,你還別說,你這一輩子雖說不會來事,認死理,但你的鍋燒得可是不賴,既省柴又省時。你說你,干嗎要走那么快,干嗎要走那么快。
“都說養兒防老,老頭子,你說說看,咱兒子給咱養老了嗎?他走得那么遠,每天又那么忙著收廢品,還不是小孫子沒有成家?他們著急,所以一年也難得回來一次,我就不計較了,畢竟他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他倒是給我錢,給錢就算給我養老嗎?那是兩碼事。他們比我更需要錢,我不需要他們的錢。
“去年過年,他們全都回來了,咱們這一大家人總算過了個團圓年。特別是兒子,竟然變得那么瘦,兩只眼睛塌陷著,頭發也白了很多,看著讓人心疼。小孫子呢,我們幾乎沒有帶過他,總覺得有些虧欠他。我想把最好吃的留給他,沒想到人家不買賬,統統拒絕了。我多想跟他說說話呀,比如剛參加工作適應不適應?比如什么時候找女朋友?但人家不給機會,整天對著手機,按個不停,他爸說這孩子一直沉迷游戲,都參加工作了,還是這樣。唉,你說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讓人看不懂了。
“還有大孫子,每次打電話總說要接我去縣城,接我去縣城,我可不想去,我哪兒都不去,我有自知之明,我可不想討人嫌。我去他那里住過幾天,天天給我洗衣服、洗澡,我就那么臟嗎?我看他們的衣服不是穿壞的,都是給洗壞的。還有咱那個孫媳婦,咋看都不像個會過日子的人。他們家的飯菜吃不完就直接倒掉,好可惜,這是多大的浪費。還有一次,他們小兩口從縣城回來,竟然把家里冰箱里的肉呀,排骨呀全給我清空了。給我氣得牙癢癢。還叫我以后不許在吃席結束時打包,不許吃剩菜剩飯。小兩口竟然對我下達起命令來了,簡直無法無天了。這就是咱們一把屎一把尿養大的孫子,你說我能說啥呢。
“孫女小時候倒是乖巧聽話。沒想到大學畢業,工作了,也當上了老師,卻一直拖著不結婚,也不怕人家笑話。不過大家好勸歹勸,終于結了婚,孫女婿這人也倒是齊整,看著也面善。可是,兩口子竟然商量好,說是不生孩子,真是邪門了,不生孩子你們結什么婚?給我氣得夠嗆。還有,咱孫女本來人也不胖,現在嚷嚷著還要減肥,依我看,再減就成了紙人了,一陣風就能刮走。
“老頭子,現在又收麥子了。我看著人家種糧大戶收麥子,一車一車地往家拉,心里特別羨慕。你說說,現在收種莊稼全是大型機械,多省事呀。咱家的十五畝多地要是不租出去,不也是一車一車的糧食往家拉嗎。真不知孩子們是怎么想的。一個個的說到底還是懶。
“你說說看,咱家這都是什么事?我老了,不中用了,再也不想瞎操心。這些話我不想跟他們說,只想跟你說,跟你說說我心里暢快多了……”
四
喧鬧的收麥季剛過去,雨就開始頻繁地下起來。稀里嘩啦的雨聲里飄蕩著鄉下泥土的腥氣,屋頂上泛起一陣白霧。入夜時分,青蛙咯咯哇哇地叫著,那陣仗簡直像交響樂一樣氣勢恢宏。
下雨的日子,孫氏不能坐在院子里梳頭了。她只好待在堂屋里不出來,那只黃狗就趴在她的床底下,跟她作伴。這條黃狗孫氏養了兩年多,當初還是大孫子給她買的,那時老伴剛去世沒多久,大孫子也是怕奶奶孤獨悲傷,身邊養只小狗,也許會有所緩解。不得不承認,大孫子想得周到,就是這只小狗,撫慰了孫氏。那時,她常常跟小狗說話,小狗似乎也很有靈性,總是搖著尾巴眼巴巴望著她,這讓她異常感動。
晚上,雨沒有停。她不是很餓。黃狗卻哼哼唧唧叫喚著,孫氏知道它餓了。孫氏來到廚房,下了一大碗掛面,比平時要多一些,里頭還打了兩個荷包蛋,原來她是把狗的飯也做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只幸福的狗,它遇上了孫氏,孫氏待它不薄。飯做好后,孫氏吃得極少,兩只荷包蛋和大部分的面條都被黃狗吃完了。只要它吃得飽,孫氏就放心。她對黃狗說:“小狗子,你就知足吧,要是在過去困難時期,別說跟主家一起吃面條,連窩頭也沒有你的份兒。”黃狗似乎聽懂了她的話,支棱著耳朵,用水汪汪的眼睛望著孫氏,繼而用頭在她的褲腳處磨蹭著,嘴里發出嗚嗚的聲音,尾巴也搖得更歡了。孫氏知道這是它在撒嬌,它能撒嬌的人也只有孫氏。“好了,好了,趕快睡吧。”孫氏向床底下的狗箱子指了指說。黃狗果然聽話地臥在了箱子里。孫氏打了個哈欠,自言自語道:“天爺,你這一天都沒住點地下,是誰惹你生氣啦,可不能這樣的呀。”
窗外的雨聲淹沒了蛙聲,似乎又刮起了狂風,雷聲隱隱傳來,孫氏面帶憂慮地嘆了口氣。老伴的那塊墳地地勢較低,這會兒也許會存下不少的水,形成內澇也說不定。那邊的老伴該怎么過呢?他今晚一定是沒法睡了。孫氏摸摸索索地走到西屋里,那里靠后墻有個小窗戶,她把那窗戶打開了一條縫兒。
“老頭子呀,外面不方便了,要不今晚你還是回家住吧,我給你留個道兒。”孫氏喃喃地說。
孫氏總是這樣,年前的時候,下了兩三天的鵝毛大雪,她也開了這個窗子,弄得西屋靠墻的地面上聚集了一層雪。大孫子兩口子帶著孩子回來時,見到屋里有雪,有些吃驚,他們的奶奶雖然是很老的人了,也不至于如此糊涂健忘,以至于一個冬季北窗都敞開著。
大孫子問孫氏:“天氣那么冷,奶奶為啥不關窗戶?弄得一地的雪。”
孫氏頗為不悅地說:“大臘月天,你也知道冷,我也知道冷,誰都知道冷,你們的爺爺他一輩子都是怕冷的,我這是給他留個回家的門道。”一番話說得大孫子百感交集,眼睛有些濕。爺爺在世時,奶奶總是對爺爺指手畫腳,似乎很不待見他。沒想到爺爺去世后,他才發現原來奶奶對爺爺的感情是那么深。
晚上睡覺時,大孫子突然心血來潮,對他媳婦說:“百年以后,假如我先‘走’了,你會給我預留回家的門道嗎?”孫媳婦被孫子問得莫名其妙,欲問何出此言,大孫子不言聲了。大半夜的,大孫子可不想讓媳婦害怕,然后失眠。
連著幾天的陰雨讓孫氏的睡眠大打折扣。她自己也想趕緊睡著呀,可就是睡不著,翻來覆去地睡不著。好在終于放晴了,陽光從梧桐樹的枝葉間斑斑駁駁地漏下來,精神頹唐的孫氏瞇縫著眼坐在院子里,她感到頭皮刺癢,還有些黏滯感。她這才想到是好久沒有梳頭了,趁著好天氣,她也許應該好好梳梳頭。奇怪的是,她怎么也找不到那把烏亮的桃木梳了。抽屜里、針線盒里、大柜小柜里,甚至床鋪上、席子底下,都找了,還是沒有。孫氏就有些生氣:“老頭子呀,你這個搗蛋鬼,我知道是你拿的,我一猜就是你,少裝蒜。”孫氏期待一覺醒來,老伴會把梳子還回來,然而沒有。事情就有些復雜,老伴拿走她的桃木梳想告訴她什么呢?他是想她早點過去陪他,還是他在那頭有了心上人?孫氏郁郁寡歡,獨坐在院子里發呆,她很想開口罵他一頓,終于還是沉默了。
村子里升騰起一縷縷炊煙,母雞咯噠咯噠地叫著。太陽已近正午,孫氏不覺得餓,她的心思被一把梳子給弄亂了。然而,黃狗咕咕唧唧叫了起來,同時叫起來的還有她飼養的兩只白鵝。這一切都提醒著孫氏,它們餓了,需要吃的。孫氏只好起身去做飯。她家的屋后有條并不太深的溝渠,孫氏的柴垛在那條溝渠的邊上。正當她準備抱柴回來做飯時,她竟然發現了她的桃木梳,它不知被誰丟在了水渠里,讓她驚詫。她放下手里的柴火,趕緊去打撈。她忘了腳下是剛下過雨的陡坡,也忘記了幾天的雨量足以讓這條不起眼的溝渠將她淹沒。那所謂的“梳子”并不成立,那是水邊一只寬大的蛤蜊所造成的假象。孫氏一頭栽了下去,再也沒有爬上來……
孫氏被發現已經是三天后的事了。人們從她單薄的衣兜里發現了那把桃木梳,它越發油光锃亮,鐫刻著歲月的光澤。
責任編輯 晨 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