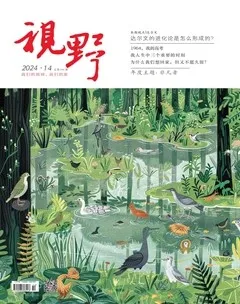進化論不能解釋的十個問題
進化論不僅成為生物學家的核心,還登上了其他學科的舞臺。物理學家根據達爾文觀點,建立了“宇宙哲學的自然選擇論”,認為存在“多元宇宙”,它是從一個簡單的宇宙“進化”成不同的多個宇宙的;計算機科學家借鑒進化的概念和原理,創造出“遺傳編程”并廣泛應用于尋找復雜問題的最優解答,包括預報天氣、優化藥物組合等;新興的進化醫學從進化的角度來理解我們對疾病的易感性,以增進我們的健康;進化發育生物學為研究物種變異帶來了曙光。
在社會科學領域,進化論被用來解釋人類的政治和消費習慣;經濟學家最近認為,從進化的觀點來看,個體的合作有利于群體的發展;文學評論家也會借用達爾文的觀點來分析小說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心理學專家根據進化論觀點,提出人類具有的認知能力和情感源于祖先對古老環境的適應。
盡管進化論幫助我們完成了這么多的認識上的飛躍,但仍然還有許多問題是進化論所不能解釋的。
一、生命是如何以及在哪里起源的?
科學家已經發現了距今34億年前的微生物化石,在更古老的巖石上也找到了生物光合作用的痕跡。不過科學家還是沒弄明白:蛋白質和DNA這兩大生命支柱究竟哪一個先出現在地球上?抑或它們是一起出現的?有科學家認為,RNA不僅可以編碼遺傳信息,還能起到部分類似于蛋白質的作用,因此RNA有可能是最早的生命起源。那么生命是在什么樣的環境下起源的?有假說認為,生命最早起源于海底的沸水中,可是脆弱的RNA怎么可能在沸水中存活呢?這就自相矛盾了。生命的起源問題至今沒有定論。如今,科學家一方面在實驗室里探尋有機物從簡單到可以自我復制的發展過程,另一方面在研究彗星和火星,希望從中獲得重要啟示。
二、是什么決定了物種多樣性?
數不清的動物、植物、微生物居住在地球上,但它們的分布密度卻有很大差別。為什么熱帶比寒帶擁有更多樣的物種?僅僅是因為熱帶比寒帶更熱嗎?科學家認為,人類的分布、生物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多樣性起到關鍵的作用,可是多樣性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即使是最時髦的基因技術也還不能回答。更讓人懊惱的是,我們掌握的資料太少,我們甚至連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種物種都還不知道。直到今天,新的物種還在被陸續發現。也許研究滅絕物種有利于我們了解新物種產生的機制。實際上,進化科學家對物種的分類研究才剛剛開始。
三、為什么人類的基因這么少?
2003年,就在人類基因組序列即將破解的時候,生物學家驚奇地發現:人類的基因數量并沒有先前預計的那么多,它與物種的復雜性并不成正比。一些植物的基因數量反而比人類稍多,而水稻的基因數量則比人類多一倍。更讓科學家們感到驚奇的是,基因組的運作方式非常靈活復雜,一個基因有時能夠“身兼數職”。這些“懷揣絕技”的基因究竟是怎么聚在了一起,又是怎樣形成了我和你?科學家們還在不停地探尋答案。
四、一個體細胞是如何變成整株植物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植物在生存和繁衍上比動物有更大的靈活性,植物的某些特征堪稱“絕活”。比如,對于大多數的柑橘屬植物,它們的體細胞不需要繁瑣的體細胞核移植技術,就能重新變成植物胚胎細胞。又如,只通過一小塊植物組織,在實驗室里就能培養出可以供一片森林使用的幼苗。這樣的本領讓所有的動物都望塵莫及。科學家早已發現并一直在利用植物的這種特性,但他們至今還是不能回答為什么植物細胞具有這種靈活性,而動物卻不具有。
五、皮膚細胞如何變成神經細胞?
近年來,科學家打算將普通的皮膚細胞轉變成寶貴的干細胞,再將這些干細胞制造成各種各樣的人類體細胞,比如神經細胞、成骨細胞、心肌細胞等,這樣也就繞過了倫理學上的禁區。可是,盡管科學家已經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進展,也不乏成功克隆動物的例子,但皮膚細胞轉化成其他細胞的機制究竟是什么,我們所知甚少。
六、是什么遺傳差異導致我們成為獨特的人類?
這是每一代人類學家都在試圖解答的問題。當然,擁有一顆大大的大腦是我們最為獨特的地方。科學家發現我們與黑猩猩之間的DNA差異大約是1.2%,這是一個很小的數字,但從絕對數量上來看,這種差異意味著近4000萬個堿基的不同。那么,到底是其中的哪些基因讓我們在與黑猩猩“分家”之后變得如此獨特?科學家認為人類的文化、語言等因素可能超過了基因的作用,但這些都還不是定論。
七、記憶是如何存取的?
所有記憶都儲存在我們的大腦中,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和所學到的一切都通過記憶促進了人類的進化。自上世紀50年代,神經科學家紛紛發現大腦中的海馬區對存儲信息至關重要,他們還能找到各種不同的記憶在大腦中的定位。可是,海馬區的神經細胞如何把信息固定下來?記憶又是怎么恢復的?這方面的研究還只是冰山一角。
八、為什么人不能像動物那樣長出新的器官?
被切斷的蚯蚓可以重新長出一半身體,蠑螈可以重建受損的四肢。在這一點上,人類顯得非常失敗,沒有人可以重新長出手指,就算傷口能夠愈合,也會留下不美觀的疤痕。人類聊以自慰的是,被部分切除的肝臟可以恢復到原來的狀態。科學家發現,那些動物的器官之所以能夠再生,是因為重新啟動了胚胎時期的某些程序。那么到底是什么程序使再生的器官保持正常的形狀和大小呢?這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回答。
九、人類合作的行為是進化而來的嗎?
早在150年前,達爾文就發現蜜蜂和螞蟻具有利他行為。人類和其他靈長類動物的社會也充滿了合作,人類甚至還會冒死去營救陌生的落水者。達爾文認為合作現象實際上會促進整個族群的繁殖,似乎是生物生存的一種高明計策。但合作行為是怎么進化的?科學家正在探尋合作行為的遺傳學基礎。而一種關于競爭、合作和游戲規則的數學理論——博弈論,也有助于科學家理解合作行為是如何運作的。不過這些解釋都不夠深入,其中的細節還有待深化。
十、還會出現生命大滅絕嗎?
1798年,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增長總是遠超過食品供應的增長,只有災難才能阻止人口增長。所幸人類懂得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開發更為廉價、環保的能源,200年過去了,地球總人口增長到了60億,是馬爾薩斯生活時代的6倍,而他所預言的大災難并沒有發生。但是,人類對這個星球的消耗仍然在高速地增長著,生態環境也大不如以前了,氣候異常與饑荒都是不爭的事實。那么,以目前的人口增長速度,如何保證大災難不會在未來發生呢?可以說,這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已經超出了科學界。
( 摘自“網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