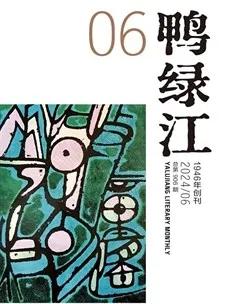其畫其文其人:汪曾祺與豐子愷
運河藝術家
楊早:
最近去了一趟桐鄉,自然參觀了緣緣堂豐子愷紀念館。站在石門灣那塊“古吳越疆界”的石碑前,我突然想到了汪曾祺。高郵咱們都熟悉的,古郵驛,運河邊。明清時高郵隔不幾年就會被大水淹沒一次。但托賴運河的交通運輸,高郵的物產、資訊、風俗乃至人文,都有它獨特的地方。
而豐子愷的故鄉崇德縣石門灣(今屬桐鄉),“它位于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杭州和嘉興的中間,而離開滬杭鐵路三十里。這三十里有小輪船可通。每天早晨從石門灣搭輪船,溯運河走兩小時,便到了滬杭鐵路上的長安車站。由此搭車,南行一小時到杭州;北行一小時到嘉興、三小時到上海。到嘉興或杭州的人,倘有余閑與逸興,可摒除這些近代式的交通工具,而雇客船走運河。這條運河南達杭州,北通嘉興、上海、蘇州、南京,直至河北。”在現代之前,托賴大運河,也能與杭州、嘉興、上海連成網絡。豐子愷甚至認為于石門灣而言,運河比火車更便利:“靠近火車站地方的人,乘車太便;即使另有水路可通,沒有人肯走,因而沒有客船的供應。只有石門灣,火車不即不離,而運河躺在身邊,方始有這種特殊的旅行法。”
桐鄉和高郵,豐子愷與汪曾祺,比較一下是不是挺有意思?順便說一句,豐子愷生于1898年,比汪曾祺大22歲,可算是差了一代。但二人都是77歲去世。兩人除了比較,是不是可以互補,而照見20世紀的文化側影?這也是有意思的話題。
徐強:
20世紀80年代中前期,中央電視臺先后播出兩部轟動一時的大型專題片——《話說長江》《話說運河》。1986年的《話說運河》的解說詞作者很有意思,一共32集,一大半交由運河沿岸出生的知名作家撰寫,例如汪浙成、溫小鈺、田本相、陸文夫、高曉聲、韓少華、汪曾祺、李存葆、蔣子龍、馮驥才、劉紹棠。這大概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文壇唯一一次以如此豪華的陣營集體“觸電”。其中韓少華、劉紹棠為北京人,田本相、馮驥才、蔣子龍為天津人,李存葆為山東人,汪曾祺、陸文夫、高曉聲分別為江蘇高郵、泰興、武進人,汪浙成、溫小鈺為浙江杭州人。這是一群大運河哺育出來的作家,他們所書寫的是他們真正意義上的“母親河”。不過汪曾祺作為高郵作家,擔任的卻是淮安一集的撰稿;有一集是關于“里下河”的,里面涉及高郵的篇幅很大,卻由北京作家韓少華撰稿。我感覺主創方是有意錯位分工。除了這兩位的錯位外,又比如田本相是天津籍的,寫的卻是江蘇盛澤、常州、揚州、山東濟寧;蘇州作家陸文夫寫的是無錫;常州武進人高曉聲寫的是鎮江、蘇北。他們自己的“地盤”本來都有專集,卻交給其他作家去寫。
從作家地理的角度來看,這個電視片可能第一次讓“運河沿岸作家”這個潛在的群體浮現出來。近年來,運河申遺成功,有關運河的文學作品出過不少,有關部門也多次組織運河文化行動,但迄今為止還鮮有人從文化地理角度對現代運河作家群體進行集中而系統的考察研究。如果把目光進一步擴展到運河藝術家群體,實際上也是很值得專題考察一番的。運河影響及于人的文化性格,一是影響人的生活軌跡、生活視野的流動性、外向性。豐子愷在《辭緣緣堂》中說:“石門灣水路四通八達,我們無需用腳走路。倘使你‘走’到了城里,旁人都得驚訝,家人怕你傷筋,你自己也覺得吃力。唉!我的故鄉真是安樂之鄉!”充滿著對于發達水路交通的自豪感。汪曾祺的幼年、童年生涯、少年求學,乃至大學畢業回鄉,都有很多水路旅行的記憶,一定意義上,運河的存在決定了他的一些軌跡,決定了他的空間閱歷。二是養成一地文化的開放性、交流性、包容性。以汪曾祺的高郵來說,從物質到精神構成,都有五方雜處、融匯南北的特征。南面的吳越文化,西來的荊楚文化,北面的齊魯乃至燕趙文化,都因為流動的運河以及與之交匯的長江而在此地交融化合。一般人的印象中,揚州周邊的文化形態與江南這種開放性,一方面與運河本身有關,另一方面也很值得注意:豐子愷的石門灣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汪曾祺的故鄉高郵屬于江淮平原。放眼看去,凡運河流經之處,都是平原地帶。平原沒有山巒屏障,沒有阻隔,一馬平川,廣闊無垠,這種地理特征也有助于養成開闊的胸襟、開放的人生態度和開通、開明的性格。
李建新:
汪先生的文章里,經常會以“我們那地方”指代故鄉。好像只有明確定位“我們那地方”才能把好多事情說清楚,才能說得合情合理。有人說,他像孩子熟悉母親一樣了解故鄉的土地和人,以帶著深情的筆墨去寫故鄉。我倒是覺得,“我們那地方”客觀上也在強調故鄉的一點特殊性。一方面是覺得小地方很多讀者未必了解;另一方面,高郵是南方中的北方,運河又造成各地人往來雜處,和典型的北方、典型的南方都不一樣。小說《榆樹》里寫到一位侉奶奶,“這地方把徐州以北說話帶山東口音的人都叫做侉子”“這縣里有不少侉子”“他們大都住在運河堤下”,賣苦力為生,拉纖,推獨輪車運貨,碾石頭粉,烙鍋盔,賣牛雜碎湯……
楊早:
徐強兄論述運河沿岸的開放性固然準確,不過高郵與嘉興相比,高郵所在的里下河地區受運河之害,幾不下于運河之利。因此在汪曾祺筆下,水可以是溫柔的,也可以是暴戾的。豐子愷筆下的“水”卻幾乎是溫馴的。而相比于杭嘉湖來說,高郵的地域邊緣性也更為強烈。有一個說法叫“現代作家看浙江,當代作家看江蘇”。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一種巧合,但地域的影響亦不可低估。
我們都知道近代江南文化的中心是在上海。有意思的是,上海地處江蘇,但它的“后花園”被公認為是杭州。豐子愷畢生的三個中心分別是桐鄉、杭州與上海。這里有一條文化地理的脈絡可尋。而汪曾祺最重要的三個中心城市無疑是高郵、昆明與北京。這里同樣有現代文化內蘊的地理邏輯。從這個角度來說,豐子愷、汪曾祺都堪稱貫穿中國現當代文化的標志性人物。
藝與文通
楊早:
故里依托運河的交通,自然只是兩人成長的相似性之一。除此之外,豐子愷與汪曾祺可以比較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他倆都是少以畫名,只是豐子愷考上浙江第一師范后,師從李叔同習音樂和繪畫,算是走上了專業繪畫之路,成為中國現代漫畫的鼻祖。而汪曾祺去昆明考大學,西南聯大之外的第二選擇是國立藝專,若是考聯大失利,他可能也就成了一位插畫師。雖然兩人的人生道路有所不同,但從“藝與文通”的角度說,兩人又頗有可比較之處。汪曾祺的小說散文自不必說,豐子愷的散文,我認為在現代文學里也可以排進前五。他們的畫作與文章的關系為何,這也是可以比較一下的。
徐強:
藝與文通,說到底還是“風格即人”“人如其文”“人如其藝”。這里面有幾個層次的問題:藝術家的人格、文藝觀、風格。在這幾個方面上,豐子愷和汪曾祺都可堪比擬。
汪曾祺應該沒見過豐子愷,但他對豐子愷的欣賞是毫無疑問的。他在1957年的散文《竹殼熱水瓶》(寫一位街頭擺攤的鞋匠)中曾提及,豐子愷先生曾經畫過一幅畫,畫的正是這樣一個鞋匠,挑了一副擔子,擔子的一頭是一個鳥籠,題目是《他的家屬》。這是一幅人道主義的、看了使人悲哀的畫。
這里面,欣賞的不僅是畫作的藝術構思,更是對人、對下層民眾、對普通民眾的同情態度。豐子愷繪畫題材多為小人物,汪曾祺的小說也全是普通人,他們都是“底層寫作”。這本身都是仁愛精神、人道主義的表現。
在藝術才具上,豐子愷和汪曾祺同為修養全面的藝術家。除了書畫之外,汪曾祺是戲劇戲曲行家里手,當中當然包含唱念部分,也就是戲曲音樂成分,這方面他是有唱曲表演實踐的,也包括吹笛。汪曾祺不僅在唱詞寫作中充分考慮音樂性,他的文學寫作里也處處顧及聲音效果。他重視文氣說,強調“氣盛言宜”。豐子愷的藝術世界幾乎也是三分天下:繪畫、散文、音樂。相對汪曾祺來說,豐子愷對西洋音樂更側重一些。李叔同的歌多用西方樂曲配新詞,在豐子愷為其編著的《中文名歌五十首》中體現得很明顯,豐子愷大概也受其影響。我以前非常欣賞豐子愷為復旦大學作詞作曲的校歌,推為當代大學校歌中的佳品。最近全面看了些材料,驚訝于豐子愷做過那么多的校歌。例如,他在桂林短短的時間里就做過好幾首。這些歌詞,全部積極向上、奮勉激勵,體現了他的“藝術辦學”“禮樂治校”的一貫主張。“五四”那一代人,音樂是他們的教育方式,也是一種日常交往方式,“唱游”是他們的日常教學交往中常見的場景,對比現在“作為特長”的藝術教育,那時的音樂教育方式更加值得追懷。可惜豐子愷有些校歌只保留了歌詞,曲譜無傳了。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搜集研究。
藝術態度上的非功利性,往往是衡量純粹藝術家境界的標志。汪曾祺自然是鄙視銅臭藝術家的,有一次溫州永嘉為了開發楠溪江請京城藝術家去采風宣傳,汪曾祺為人寫字有求必應,但看到有的大牌書法家寫一兩幅后就開始擺架子,他曾以尖刻口氣表達過自己的不屑。這與豐子愷非常相像。豐子愷日記中經常有隨手贈畫的記載,甚至主動畫了送人。在桂林有次看到鄰居夫妻在院子里種菜勞動的場景動人,可堪入畫,于是進屋取畫筆在對方不注意時悄悄畫下,認為“這是最好的寫生方式”,晚間又重新以大幅正式畫下,題句贈給這對夫婦。當天他在日記里寫道:“近索畫者甚眾,積紙盈筐,每苦無力應囑,李君并不索吾畫,更不送紙來,而吾自動寫贈。故畫不可索,須作者自贈方佳。”他的女兒豐一吟曾經說到,“文革”前,不認識的人寫信來向豐子愷索畫,說自己是個工人或者是個職員,很喜歡你的畫,能不能送我幅畫,他不出一個禮拜就把畫畫出來寄給人家了,也不收錢。他在世的時候,除了到香港辦展覽那次,從來沒有賣過畫。
至于藝術風格,豐子愷和汪曾祺最接近的一點是善用“側筆”、善于布白表現。豐子愷漫畫中很多人物沒有面部表情,甚至很多人物只寫背影,這也是側筆的表現。汪曾祺的小說和繪畫也往往如此。中國現代短篇小說,從魯迅開始,幾代作家都不乏善于側面表現的高手,從情節到人物表現,這是藝術民族風格的表現。汪曾祺是這個鏈條上很突出的一個。
李建新:
豐子愷和汪曾祺都很接近我們前幾期討論過的“文人”。比如在某些行為方式上對傳統文人趣味的繼承。汪先生沒有正兒八經使用過堂號,也許是他看不上附庸風雅的做派,但他在上海致遠中學教書時,因為住在學校的宿舍里,不時會聽到樓上住戶潑水的聲音,就戲謔地把自己的居所命名為“聽水齋”。豐子愷先生的緣緣堂則很有名。無論是否使用堂號,他們對文人的那套程式性的東西是很熟悉的。另外兩人都是既能為文,也擅長書畫。汪先生的畫,是傳統文人畫的花鳥畫,寫意,雖非專業畫家,但格并不低。豐子愷先生要算是職業畫家了,而且另辟新路。據說近代中國的“漫畫”一詞就從豐先Sf9s+6HE5bYRCx28i1bVAg==生開始。后來絕大多數漫畫家的作品多著力于諷刺與幽默,豐先生的不少作品應該叫作抒情漫畫,像那些畫古詩意境的,畫面簡單而情感豐富,能夠調動觀畫者的情感和文化積累,是很動人的。這樣的畫在別的漫畫家那里很少見。漫畫在大多數情況下被作為一種工具,比較直接,功能性過分突出,藝術性也就相應降低了。
汪曾祺的畫體現的還是傳統文人畫的特征,含蓄,講究筆墨。豐子愷先生的許多畫,意境近似文人畫,但是更外露,注重線條而不太看重筆墨。單從開創性上講,汪先生只是文人畫的票友,豐子愷是開辟了新路的畫家,且幾乎是獨一無二。
楊早:
汪朗老師曾說汪曾祺不會畫人,故筆下以草木鳥獸蟲魚為主。豐子愷肯定是會畫人的,但他后來的漫畫,尤其是《護生畫集》,也刻意將人物的五官抹去。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種深意在?豐子愷的成名作《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恰恰反映的是人去后器具景物的自然寂寥,汪曾祺更是通過題畫將“人”與“物”作有機結合,比如那幅也很有名的“下面等水未開”的蜻蜓畫,又如“時女兒汪明在旁瞎出主意”,我認為都是欲狀人而無人之妙。他們二位都很難完全從技法、風格去考量其畫作,而是要結合其文其人來討論其畫。我這里也只能虛點一下,深入探討有俟異日異人。
師徒與儒道
楊早:
我在桐鄉曾說:有三對師徒構成了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輪廓:魯迅與蕭紅,李叔同與豐子愷,沈從文與汪曾祺。此前也曾倡言三篇最好的憶師文分別是豐子愷的《念李叔同先生》,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和汪曾祺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贊同者不乏其人。從師弟朋友交游來說,兩人的際遇也很有意思,可以串起20世紀中國文化的好幾條脈絡。
李建新:
豐子愷16歲時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成為李叔同的學生;20歲時,李叔同出家,表面上二人師生關系已了,事實上,在精神世界里,李叔同是他一生的老師。說佛教思想深刻影響了豐子愷的創作,毋庸置疑。豐子愷晚年談自己的創作,賦詩云:“泥龍竹馬眼前情,瑣屑平凡總不論。最喜小中能見大,但求弦外有余音。”其中提到的對生活的“感悟”,于瑣細中見藝術,求弦外之音,都與佛理相通。
豐子愷還更明確地說過:“藝術家看見花笑,聽見鳥語,舉杯邀明月,開門迎白云,能把自然當作人看,能化無情為有情,這便是‘物我一體’的境界。更進一步,便是‘萬法從心’‘諸相非相’的佛教真諦了。故藝術的最高點與宗教相通。最高的藝術家有言:‘無聲之詩無一字,無形之畫無一筆。’可知吟詩描畫,平平仄仄,紅紅綠綠,原不過是雕蟲小技,藝術的皮毛而已,藝術的精神,正是宗教的。”
汪先生對自己的評價,我們都比較熟悉,他認為自己是儒家,“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因此我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他小時候也接觸過佛門弟子,有一些淵源,但南方世俗化的佛教給他的不是對信仰的敬畏,而是熱熱鬧鬧的世俗人情,他感受到的是審美意義上的宗教。
楊早:
這兩對師徒最大的相似性,我以為是對世俗的“拒而復返”。我的意思是他們都是有意識地拒絕主流秩序。比如沈從文不肯在湘西當一個小官僚,或是一個放浪至死的軍官;而豐子愷也記錄過,他的商人親戚看了李叔同的各時期相片,聽了他的事跡,反應大抵是:“這人是無所不為的,將來一定要還俗!”“他可賺二百塊錢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而豐子愷與汪曾祺雖然沒有他們老師那樣的驚世駭俗,但他倆各守其業(豐子愷是美術、教育,汪曾祺的編輯、編劇),一直與文藝界的主流保持著距離。然而,這四個人都與俗世界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當中最給人高冷印象的,要算李叔同。但弘一法師后來在泉州十四年,留下許多傳說,守正持世,溫文待人,與在東京、在杭州時給人的印象大不相同。其實四人年輕時都可以說是“憤青”,但終于都能達到和光同塵的境界。所以我說他們幾個都是對世俗“拒而復返”。
徐強:
江浙閩越佛教氣氛濃厚,這一點我有直覺印象。作為山東人,在江南一帶看到那么多的寺廟感到不可思議。后來在有關資料中得到驗證:江浙各省佛教場所數量,十數倍于作為儒家文化發源地的山東。李、沈、豐、汪兩對師生中,江浙人居其三,都有很深的佛學因緣,都不脫離世俗性。李叔同皈依佛門之前,也曾研習道家,或許是因為他在現代文化史上的多方面的建樹,尤其是與世俗文界的牽連不斷的聯系,弘一法師給人的印象并非森嚴肅穆、孤絕人間、不問世事,相反,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形象。豐子愷接觸佛學較晚,應該是李叔同出家之后,受乃師影響而較深入地接觸。但從他作品里時時閃現的因緣妙悟,可見他是極有慧根的,他和弘一法師弟子、身在南洋的廣洽法師幾十年的交往,留下大量書信,他晚年在極不相宜的社會環境中還翻譯《大乘起信論新釋》交廣洽法師在新加坡出版,都證明他與佛教的聯系。他對世俗入得深,佛學沒有成為他全身皈依的信仰。有人直言不喜歡汪曾祺《受戒》中寫的世俗化佛教徒生活,認為失真,但我十幾年前第一次去高郵,在街巷見到微型寺廟與市井雜處的景觀讓我一下子就相信了,汪曾祺自小接觸的就是這樣不失人間煙火氣的佛教氛圍。沈從文似乎沒有專門研究佛學,但他作品里寫過佛教故事,對于佛教文化的了解是少不了的。也有研究者指出,他的平等慈悲觀念與佛教有一定聯系。總而言之,從思想意識上來說,這兩對師生,尤其是豐子愷和汪曾祺,是受到佛家的重要影響,而又在儒釋道的重疊區域,其泛愛眾生、慈悲為懷,既是佛教的主張,也是儒家思想的精華。他們的人格魅力和藝術魅力,恐怕很大一部分就在于這種宗教的純潔和世俗的寬容的結合。
李建新:
想到豐子愷和汪曾祺的兩部繪畫作品,在某種意義上有象征意味。最初是為了給弘一法師祝壽,豐子愷動筆畫《護生畫集》第一部,后來堅持十年一部的約定,前后花了46年時間,完成了450幅圖文并茂的《護生畫集》。這部畫集立足于宣傳仁愛護生的思想,是通俗的有價值的深深打上佛教印痕的藝術品。
汪曾祺也畫過一部《馬鈴薯圖譜》,那是他在張家口下放勞動結束之后,單位派下來的任務。他很認真又很有興趣地去做這件事,孤身一人,“坐對一叢花,眸子炯如虎”。那段時間,精神放松,面對無須防備的植物作畫,充滿了生之喜悅。可惜這部圖譜最終毀掉沒有留下來。
豐子愷的畫從內心出發,有一種宗教的莊嚴,雖然漫畫的表現形式很大眾。汪曾祺面對的是他傾心的人間,他的寫作和繪畫都是在表達“活著多好啊”。
旅行與生活
楊早:
同時,我也關注豐汪二位的抗戰內地之旅。豐子愷1937年11月率全家從石門灣出發逃難,經江西、湖南、廣西、貴州而至重慶,1945年抗戰勝利后才回杭州定居。而汪曾祺1939年從高郵經上海、香港、河內而至昆明,在昆明度過七載云煙,咱們此前也討論過昆明對于汪曾祺成長的意義。此二人對于抗戰大后方文化都具有切片性的意義。
徐強:
生活熱情,藝術的發現和會心。汪曾祺對生活的流連屬情,我們前面幾期涉及不少了。而豐子愷對基層生活的關注,也是隨處可見。我還是僅以他的抗戰日記來說。1937年的八一三事變后,上海淪陷,江南也連連遭受轟炸。11月15日,時年40歲的豐子愷,戀戀不舍地作別浙江桐鄉石門鎮的緣緣堂,攜帶家眷,踏上西行避難之路。先后經江西上饒、萍鄉,湖南醴陵、湘潭、長沙,湖北漢口,再經長沙,于1938年6月24日抵達桂林,先為廣西藝術教師暑期訓練班授課,旋受聘桂林師范學校(居兩江鎮),教授美術與國文課程,后受聘內遷廣西宜山的浙江大學,離別兩江,經陽朔、修江,于1939年4月8日抵達宜山,任教浙江大學(后隨浙大遷貴州遵義)。1942年秋轉赴重慶,任教于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次年辭職專事創作,直到抗戰勝利,東返杭州。在整個抗戰期間,豐子愷以日記形式書寫經歷,日記在各報刊發表,后來先后結集出版。作為熱愛生活、敏于藝術的作家和畫家,豐子愷在異地他鄉處處抱有好奇心,隨時觀察各地鄉俗、物產、民間藝術,以文字記錄,以繪畫速寫,因此他的日記,實際是在一種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的自覺意識引導下的采風與寫生成果,很多篇目本身就是很好的風物散文,而更多的素材則無形中化入了他后來的散文與繪畫創作。豐子愷日記,可以作為我們今日采風的范例來看。例如1938年11月23日日記,就是這樣一個范例。當時他客居桂林,在桂林師范學校任教美術、國文,這里的生活處處顯示出新鮮感。他在這篇日記中記錄了此地吃食、鄉俗,描述了鄉間工藝品,并用畫筆畫下竹籃、竹匣與竹碗及用吉祥文字圖樣構成的窗欞。他還對鄉民家里一種蘊含奇巧、令人贊嘆的門閂加以研究,推測出了其可能的內部結構,并畫出了解剖圖。這種圖文并茂的記錄,顯示了他敏銳的發現、援筆立就的速寫能力、對民眾智慧的崇敬。今年我們東北師大創意寫作采風營編印參考資料,就把這篇日記作為范例編了進去。
和汪曾祺一樣,豐子愷也頗有自由散漫之風。1938年11月,桂林師范有遷校之議,豐表示:但愿桂林無恙,桂師不遷。萬一不幸而要實行這一步,他恕不奉陪。因為他未學“軍旅之事”,不能參加游擊隊,只有“明日遂行”了。他一度辭職專事創作,也是這一風氣的表現。而且豐子愷好交游,逃難桂林期間,與一般文人一樣,日與友朋晤面暢聊:“鄉村究竟太寂寥,太沉悶。我覺得鄉村不可不來游或小住,但不可久居。今不得已也。”
抗戰以前,豐子愷深居簡出,好靜惡動。經過一年多的顛沛流離之后,雖然吃盡苦頭,但觀念大變,“每思遍游天下,到處為家”。豐子愷的顛沛流離還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扶老攜幼,全家走時是十口人,六個孩子都沒成年,途中又添新丁,成了十一口——豐子愷說這話的時候,幼子新枚尚不足一歲。老友傅彬然見狀,稱贊他說是“偉大的旅行”,而豐子愷表示要使它成為“更偉大的旅行”。“但有旅行,決不吝惜。與其積鈔票于篋,不如積閱歷于身。”豐子愷雖已兒女成行,但計歲僅四十而已,拿今天的眼光看,還是青年人。可見,國難流離、旅途顛躓的經歷,也豐富了他的閱歷,促進了心智的成熟,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是大有益處的。
楊早:
我們幾乎可以說,豐子愷與汪曾祺都是“被旅行成就的作家”。這一點咱們在“汪曾祺與旅行”的主題里聊過。其實我也一直關注“旅行與作家”這個課題,蓋近代以來,“旅行”才真正成為中國文學里反復詠唱的主旋律。這當然是一個大題目,一下子說不清楚。但是正如王德威用“旅行者敘事”來闡述《老殘游記》等晚清旅行小說,豐子愷、汪曾祺的小說與散文,也正可以如是觀之。豐氏有名篇《藝術的逃難》,或許是對近現代尤其是抗戰時期諸多旅行敘事最好的概括。即作家們將不得已的逃難藝術化,從而為中國文學留下一幅又一幅畫像。像《馬伯樂》《圍城》《八十一夢》《寒夜》《傾城之戀》這些40年代的名rsEP+c2fs9rRKX12kIHjwO7nMh7tL8NE7rIPhSn+7m4=作,都可以歸入這個類別。
兒童的發現
李建新:
關于兩人對兒童的看重,我也想到了豐子愷的那句話,“我的心為四事所占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
在生活中,汪先生對待子女和孫輩,都是平視甚至到溺愛的地步,貫徹了他轉述自己父親的話,“多年父子成兄弟”。在他的作品中,也時常可見兒童的影響。他很認真地關注孩子們傳唱的兒歌,留心童言稚語。他在散文里寫苦瓜,小標題“苦瓜是瓜么”,就是從三歲小孫女對瓜的認知而來。
豐子愷先生最著名的畫,就是畫孩童充滿童趣、充滿想象力的行為,畫面無須刻意的“藝術表現”,寫實地畫下來,就特別打動人。他的文章也有很多寫兒童的,豐先生甚至有些“崇拜”兒童。他筆下的成人世界充滿愚蠢、虛偽、不合理,但兒童的世界是單純、誠摯、自然的。和汪先生相似的一點是,豐子愷也不是哲學家,他傾心于現象,迷戀人類童年時代的純真,也清醒地認識到,兒童總要長大,純潔總要失去。為此甚至有些頹廢和痛苦,于是更要努力地用文字和線條留住這些美好。
法國作家圣埃克絮佩里在他著名童話《小王子》的獻辭中說:“這本書是獻給長成了大人的從前那個孩子。”有些杰出作家是一生保留了赤子之心的人,比如豐子愷和汪曾祺,他們內心深處都藏著不愿長大的自己。
楊早:
我曾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博士生面試時,回答孫玉石先生“現代文學的作家里,你喜歡哪幾位”的問題,也是在魯迅、沈從文后,列出了豐子愷的名字。理由呢,也是建新兄提到的,豐子愷被感動的“四樣事物”,他和李叔同代表著中國現代“美的教育”的實踐……近代中國“兒童的發現”也是一個大題目。要言之,啟蒙者認識到兒童并非“未長成的成人”或“殘缺的人”,他們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思想。魯迅、胡適均多有論述。不過,像豐子愷這樣盡全身心力量去謳歌兒童的作家還真不多見。他宣稱:“我企慕這種孩子們的生活的天真,艷羨這種孩子們的世界的廣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練的孩子們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烏托邦,以為逃避現實之所;但我也可笑他們屈服于現實,忘卻人類的本性。我想,假如人類沒有這種孩子們的空想的欲望,世間一定不會有建筑、交通、醫藥、機械等種種抵抗自然的建設,恐怕人類到今日還在茹毛飲血呢。”豐子愷還托人將八指頭陀的詩用細字刻在自己用的煙嘴上:“吾愛童子身,蓮花不染塵。罵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對境心常定,逢人語自新。堪嗟年既長,物欲蔽天真。”
我們拿豐子愷這種觀念來衡量汪曾祺的名篇《多年父子成兄弟》,當可以見出二者的相似性,如汪曾祺那膾炙人口的結尾:
我的孩子有時叫我“爸”,有時叫我“老頭子!”連我的孫女也跟著叫。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一個現代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于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這種寬容并非后設,早在1956年,汪曾祺就寫過:“我的孩子跟我說了不止一次了:‘我長大了開公共汽車!’我想了一想,我沒有意見。”所以說,從“兒童的發現”角度來看,從魯迅、豐子愷直至汪曾祺,同樣也在為中國“寫孩子的文學”貢獻著極大的力量——開句玩笑,拙著《早生貴子》,引用最多的“育兒經”,也是來自這三位作家哩。
徐強:
關于子女,1938年10月豐子愷的日記中有個細節,讓人樂不可支。這個月24日,豐子愷剛就職于桂林師范學校,這是他作別教師生涯十余年后重登講臺的日子,所以他開始寫作《教師日記》,這一天的事情極多,但恰恰在這一天,他的距預產期還有三星期的夫人徐力民經檢查患子癇,醫生決定緊急剖宮產。所以這一天豐子愷又擠車去桂林探視。次日,夫人產下嬰兒,母子基本平安,但夫人昏迷狀態持續一段時間,直到26日醒來,“她不相信已生下一個孩子,更不相信孩子是男”,直到護師抱來,她才相信。而豐子愷也直到此時方知嬰孩兒是男。而此前一日,馬一孚道賀時還曾問過孩子是男是女,豐子愷沒回答上來,只說“是一個‘人’”。這最小的孩子就是豐子愷的幼子豐新枚。我們現在可能難以想象,作為父親的豐子愷如此不關心孩子的性別,一個原因是40歲的豐子愷此前已有六個孩子,兩兒四女,這最小的一個是男是女不那么重要了;其次也顯示了豐子愷對男女沒有輕重之分,他是在“人”的意義上看待孩子,“人”最重要。
作者簡介>>>>
楊早,文學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閱讀鄰居讀書會聯合創始人。著有《清末民初北京輿論環境與新文化的登場》《傳媒時代的文學重生》《拾讀汪曾祺》《民國了》《元周記》《野史記》《說史記》《城史記》《早讀過了》《早生貴子》等著作,主編《話題》系列(2005—2014年)、《沈從文集》、《汪曾祺集》、《六十年與六十部——共和國文學檔案》、《汪曾祺別集》、《寧作我:汪曾祺文學自傳》、《汪曾祺文庫本》(十卷)。譯著有《合肥四姊妹》。合著有《汪曾祺1000事》《墻書·中國通史》《小說現代中國》等書。
李建新,畢業于鄭州大學新聞系,曾任《尋根》《中學生閱讀》雜志編輯,2016年參與創建中原出版傳媒集團北京分公司出版品牌“星漢文章”,現任職于河南文藝出版社。編選有《食豆飲水齋閑筆》《汪曾祺書信集》,編訂有《汪曾祺集》(十種),策劃《汪曾祺別集》(二十種)并擔任分卷主編,為《汪曾祺全集》中后期小說、書信分卷主編。
徐強,文學博士,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創意寫作研究中心、新文學手稿文獻研究中心主任。系中國翻譯協會專家會員,中國敘事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近現代文學史料學會理事,世界華文創意寫作協會副會長,中國寫作學會理事,吉林省寫作學會會長。從事文學理論、敘事學、新文學文獻、語文教育、寫作教育等領域的研究。著、譯、編有《汪曾祺年譜》《小說與電影中的敘事》《故事與話語》《長向文壇瞻背影——朱自清憶念七十年》及《汪曾祺全集》(散文、詩歌、雜著諸卷)等。
[責任編輯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