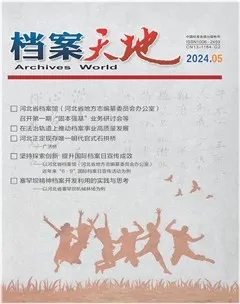數字人文視域下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研究
紅色檔案資源作為中國共產黨誕生、成長、奮斗光輝歷程的真實見證,作為紅色歷史、革命傳統與精神內涵的真實縮影,蘊藏豐厚的政治內涵、文化底蘊和精神財富,具有重要的歷史憑證、文化教育和產業經濟價值。在大數據和數智化快速發展的新時代,對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的深度、廣度、形式和途徑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進一步做好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工作具有必要性、重要性及緊迫性。目前來看,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在組織模式、資源結構、技術應用、呈現形式、傳播手段等方面尚存在一系列問題。在數字化轉型、技術更新迭代的背景下,數字人文理念和技術的引入給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貫穿紅色檔案開發與利用的全過程,為紅色檔案資源收集、整理、利用和保護提供了新視角、新思路、新方法、新契機。
一、數字人文視域下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的現實邏輯
紅色檔案資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文本、圖表、聲像、實物、遺址和精神資源[1],具有原始記錄性,客觀真實地記錄著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具有重要的歷史憑證價值、學術價值、教育價值和經濟價值,是服務黨史教育、傳承紅色基因、激發愛黨愛國熱情的重要素材。同時,紅色檔案資源的內容、類型和載體豐富多樣,且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下形成,具有明顯的時間和地域特征,時間跨度長、地域分布廣、來源渠道多、珍貴且稀缺。
國內利用數字人文技術開展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的項目案例較少,廣西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數字人文項目、山東沂蒙紅嫂精神數字項目、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成都市紅色檔案編研專題數據庫、南京地區侵華日軍慰安所AR故事地圖、遵義習水縣四渡赤水實景VR體驗園區、貴州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化展示、江西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數字展館云平臺等項目雖然是在數字人文視角下進行的有益嘗試,但都僅將技術應用于某一方面,呈現出以下若干問題。
(一)開發主體單一
開發主體多為某地方檔案部門的“單打獨斗”,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信息孤島”現象存在,缺乏同其他地域檔案部門或黨史館、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高校、企業、社會公眾的合作,跨地域、跨學科和跨領域協同開發的成果不多,分散、無序、自主、同質現象嚴重[2]。
(二)開發客體異化
紅色檔案資源的數據多以非結構化或半結構化方式存在,大多數元數據的著錄方式不統一、描述顆粒度粗放,難以實現紅色檔案資源的整合、兼容和互聯,難以深層次地揭示檔案數據的層次關系,導致對紅色檔案資源的脈絡梳理不清,內涵價值挖掘不足,紅色精神提煉不夠。
(三)技術應用薄弱
數字人文技術應用仍處于初級階段,數字化掃描、數據庫建設、音視頻技術、圖像技術應用較多[3],而利用數據分析、挖掘和關聯技術提煉各元數據間內在聯系,將信息從離散分布向聚合協同轉換應用的較少。同時,人工智能、云計算、元宇宙、虛擬現實、GIS等新興數字人文技術應用有待升級。
(四)表現形式匱乏
表現形式多為文字、圖片、音像、實物等一維、二維形式,缺乏3D展館、VR和AR體驗、互動游戲、影視作品等交互能力強、體驗沉浸感好的呈現手法,沒有整合人、地、時、事、物等紅色檔案因素進行敘事化開發,紅色檔案內在的革命精神和歷史價值與意義沒有被公眾感同身受、內化于心。
(五)傳播手段傳統
傳播手段多為主題展覽、成果匯編、書籍出版、專題講座、廣播電視及主題活動等線下形式,傳播的時效、程度和受眾有限。滿足個性化、交互性、快節奏、碎片化信息傳輸需求的傳播手段應用較少,削弱了紅色檔案資源開發利用成果的傳播力與影響力。
在數字轉型、技術更新迭代與社會個體文化需求轉型的背景下,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與利用需要在數字人文理念與技術的雙重革新下,解決主客體、應用技術、表現形式、傳播手段等方面問題,更好地傳播紅色文化,賡續紅色血脈,發揮紅色檔案資源影響人、教育人、感召人的重要作用。
二、數字人文視域下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的價值闡釋
早在2009年王曉光將“數字人文”概念引入我國的圖情檔領域,2017年以來圖情檔學界迎來了數字人文研究的“熱浪潮”,目前將數字人文應用于檔案研究領域仍然方興未艾。盡管目前學界對數字人文的概念和定義并未達成共識,但普遍認為它是一種集資源、技術、服務于一體的新型的、跨學科的學術模式和組織形式[4]。其實質是計算機技術與人文學科的雙向融合,利用計算機和數字技術對人文知識要素進行數字化采集、加工標注、組織集成、關聯分析和可視展示,實現人文研究的多重知識表達和可視化呈現,挖掘傳統人文難以發現的線索與問題。數字人文以學科融合為理念,以數據和技術作為兩大支撐點[5],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堅持問題導向,基于主題資源,多依托項目制進行具體開展。
隨著視覺傳播圖像時代的到來,數字人文理念及技術應用于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將在組織形態、整合分析、展現方式和效果分析等方面對其產生積極作用。
(一)數字人文提供一種“跨界合作”理念
在數字人文理念下,開發主體打破層級限制、地域限制和學科壁壘,跨學科、跨領域、跨地域組建團隊,圍繞共同的主題展開合作研究,實現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的共建、共有、共管、共享,擴大檔案征集范圍,充實檔案資源內容,優化檔案資源結構。
(二)數字人文提供一種“全過程化”技術
運用數字化加工、數據管理、數據分析、數據關聯和可視化等數字人文技術,挖掘各要素間深層次的潛在關聯,動態呈現紅色檔案資源的歷史背景、形成過程和演變進程[6],為紅色檔案資源“數字化聚合—知識化開發—可視化展示—智能化服務”的全生命周期提供技術支撐[7]。
(三)數字人文提供一種“立體可視”效果
數字人文知識體系中的3D建模、GIS、可視化技術、VR、AR、MR等技術作為多樣化呈現的有效開發工具,通過營造三維立體的仿真環境,把紅色檔案資源加工為可看、可觸、可說、可演、可學的全息景觀,使之真正“活起來、動起來”。
(四)數字人文提供一種“智慧服務”平臺
數字人文應用對用戶體驗感與參與度要求較高。在數字人文技術支持下搭建主題數字平臺和全媒體傳播矩陣,能夠為紅色檔案資源的知識展示、數據分析、智慧服務、互動參與和協同傳播提供一站式、便捷性、時效性平臺。
三、數字人文視域下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的運行機制
以項目式為驅動,構建由資源層、知識層、應用層、交互層組成的數字人文運行架構,實現“數字化整合—知識化開發—可視化展示—智能化服務”遞進循環、相互作用的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運行機制。
(一)資源層——建立基礎數據庫
數字人文要求檔案資源實現從“實體”向“數字化”再向“數據化”轉變。首先,利用文字掃描、文本/光學/語音識別、圖像處理、三維建模等技術對非數字化資源進行數字化處理。此后,按照元數據格式,對于結構化數據進行細粒度描述與統一著錄標引,對于非結構化數據采用視覺技術將其提取為結構化數據,完成數據化處理。最后,通過語義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知識圖譜、文本挖掘、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對資源進行精準描述、聚類分析、挖掘提取、關聯分析和組織融合[8],構建類別清晰、主題鮮明的紅色檔案資源主題數據庫,為整體運行機制提供基礎數據。
(二)知識層——完成知識化開發
知識層是進一步對資源層成果進行挖掘、分析與關聯等知識化開發。利用數據分析技術對數據進行內容挖掘、時序分析、社會關系以及歷史地理空間分析等,重構紅色檔案資源的社會網絡和歷史軌跡。利用數據關聯技術,梳理紅色檔案的事實、因果、繼承等關系網絡和知識體系,勾勒出紅色檔案資源的完整全貌,挖掘傳統人文難以發現的深層次線索,實現對紅色檔案資源中人文內涵的深入挖掘。知識層也為應用層的可視化開發提供資源與技術支持。
(三)應用層——進行可視化展示
運用可視化技術將隱性的數據轉換成顯性的圖形或圖像,體現社會關系、地理空間、時間序列和文本特征等多維度的視覺表征,增加紅色檔案的可視化、立體化與體驗式展示效果。包括利用VR、AR、MR等技術,打造環幕投影、空氣成像、體感互動項目[9],營造“視聽說感”仿真體驗場景;借助3D建模、Unity場景搭建技術實現紅色場景再現;運用GIS、RS技術進行紅色地理數據標注,重現氣候、地貌、環境等原貌。
(四)交互層——明晰利用需求
“用戶生成內容”是數字人文研究的主要需求。在數字人文平臺上利用網絡爬蟲技術、知識圖譜、精準畫像等技術,對用戶基本信息、瀏覽痕跡、互動信息、反饋信息等進行收集、分析、建模、預測,以辨析現有成效,預測潛在需求,催生新的、更符合需求的開發與利用主題方向,同時形成反哺資源層、知識層及應用層的循環上升模式。
四、數字人文視域下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的優化路徑
(一)基于制度維度,確立“跨界合作”開發機制
各級各類檔案部門要摒棄“各搞一攤”思維,加強頂層設計和宏觀規劃,制定共建共享的紅色檔案開發與利用機制,積極主動謀求跨地域、跨層級的協同與聯動。同時推進與公共文化事業機構、科研院所、高校、信息技術公司和民間組織、社會公眾的廣泛合作,依托各自的資源優勢、專業特長或技術優勢,基于某一專題項目,組建多方團隊,加強在數據收集、技術整合、宣傳推廣的協同創新與開放共享,實現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主體跨學科、跨領域、跨館際的合作。
(二)基于載體維度,搭建紅色檔案“數字平臺”
建設集“知識展示、數據分析、智慧服務、互動參與”于一體的主題數字平臺。第一,平臺上承載內容豐富、分類清晰的多個主體數據庫,用戶點擊智能化檢索模塊,平臺將通過篩選、過濾和推薦,為其提供多維度、可視化的知識聚合、關聯分析和知識圖譜。第二,平臺運用GIS、RS、AR或VR技術,將紅色歷史場景搬上“云端”,增強沉浸感與體驗感;增加“在線朗讀”“智慧書房”“云端課堂”“黨史微課”等智能工具,為用戶提供多角度、個性化服務模式。第三,設置反饋留言、標注標引、參與眾籌等互動模塊,提高用戶參與的歸屬感與主動性,擴大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的征集范圍和選題范圍,有益于更好地提供精準化和全面化服務。
(三)基于傳播維度,形成“互動融合”全媒局面
傳播方面應形成線上線下結合、多方聯動互補的全媒體傳播局面,實現分眾化與差異化推廣,擴大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成果的傳播范圍和疊加效應。首先,線下可以利用數字人文可視化技術將紅色檔案資源串點成線、由線成面,加工成內涵豐富、形式多樣、喜聞樂見的文創產品,激活紅色檔案資源在文化旅游、影視傳媒、藝術表演、文博產業、工藝美術、互動游戲等文化產業領域的經濟價值[10],發展紅色文化產業,打造文化品牌IP。其次,線上可以打造網上虛擬紅色檔案館或在線專題展覽,將紅色檔案資源拍攝成短視頻、微電影等,利用“兩微一端”、學習強國、QQ、抖音、Bilibili、直播等新興傳播媒介進行傳播。
(四)基于人才維度,打造“一專多能”復合人才
數字人文視域下的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工作涉及計算機科學、信息技術、歷史學、檔案學、傳播學、統計學、藝術學等多學科內容,因此僅依靠檔案工作人員的單方力量,難以完成難度較高、效果明顯的數字人文項目,需要組建以某一數字人文項目為研究對象的,涵蓋檔案工作人員、圖情領域專家、高校研究學者、科研機構專家、信息技術人員及社會公眾為主的數字人文團隊。同時,引進富有多元化知識結構和業務素質的檔案研究復合型人才,培養新型“數字人文檔案館員”,優化檔案管理隊伍結構。
(五)基于設施維度,完善“軟硬結合”基礎設施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應完善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硬件和軟件的“雙建設”“雙提升”。硬件方面,建設以檔案機構為主體的數字人文工作室、研究所等實體中心,以保障項目的運行管理職責清晰、分工明確,同時具有獨立的空間、人員和經費,如上海圖書館數字人文、武漢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北京研究中心[11]、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KVision實驗室、山西數字人文研究院等數字人文研究機構。軟件方面,包括建立數字人文語料數據庫和網絡智能平臺終端,開發優質的軟件工具和服務器,構建檔案安全技術體系,提升基礎設施的網絡化、自動化及智能化程度。
紅色檔案資源為數字人文研究提供了不可比擬的基礎資源,數字人文又為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和方法技術,兩者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在新時代將數字人文應用于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實現對紅色檔案資源的重組與再造,增強紅色檔案資源利用價值,傳承好紅色基因,留存好紅色記憶,服務于時代發展需要和人民群眾需要,既是適應數字化環境與數字化進程的嬗變之舉,也是實現檔案事業高質量發展的創新之舉。
參考文獻:
[1] 溫兆光. 數字人文視域下江西紅色檔案資源建設研究[D]. 南昌: 南昌大學, 2022: 23.
[2] 薛文萍, 周昊, 王昊, 等. 數字人文視角下的紅色檔案資源建設:以沂蒙紅嫂檔案為例[J]. 山西檔案, 2020(2): 85-91.
[3] 龍家慶. 基于數字敘事理論的紅色檔案開發策略研究[J]. 檔案管理, 2023(4): 66-68, 72.
[4] 司靜輝. 數字人文視角下紅色檔案資源開發途徑思考[J]. 辦公室業務, 2023(8): 169-171.
[5] 翟樂, 李金格. 數字人文視閾下紅色檔案資源的遴選、組織與開發策略研究[J]. 情報科學, 2021, 39(12): 174-178, 186.
[6] 周林興, 崔云萍. 區域性紅色檔案資源的協同開發利用探析: 以長三角區域為分析對象[J]. 檔案學通訊, 2021(5): 4-13.
[7] 趙紅穎, 張衛東. 數字人文視角下的紅色檔案資源組織: 數據化、情境化與故事化[J]. (下轉49頁)(上接40頁)檔案與建設, 2021(7): 33-36.
[8] 陳艷紅, 陳晶晶. 數字人文視域下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開發的時代價值與路徑選擇[J]. 檔案學研究, 2022(3): 68-75.
[9] 邊媛. 面向數字人文的中央蘇區檔案數據多源整合的動因、條件與路徑研究[J]. 檔案學研究, 2022(5): 102-108.
[10] 陳海玉, 向前, 萬小玥. 數字人文視域下抗戰檔案資源的開發策略與路徑研究[J]. 山西檔案, 2021(3): 71-80.
[11] 靳文君. 基于數字人文的檔案資源開發利用研究[J]. 檔案與建設, 2021(4): 12-16, 11.
基金項目:2023年度秦皇島市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數字人文視域下地方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與利用研究”(2023LX020)
作者單位:燕山大學檔案館(校史館) 秦皇島市衛生健康綜合監督執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