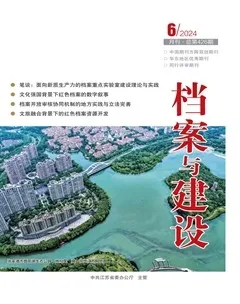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策略研究
摘 要: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是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珍貴原始資料,是共產黨人“為理想獻身”的生動見證。用好用活雨花英烈紅色檔案資源,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有助于賡續紅色基因的精神血脈、彰顯紅色基因的政治底色、賦能紅色基因的精神涵育。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推進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應聯動多元主體,促進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開發協同化;深挖內容元素,實現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開發情境化;活用數字媒體,推動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開發多維化;注重敘事轉向,助力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開發新穎化。
關鍵詞:紅色基因傳承;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
Research on the Narr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Red Archives of Yuhua Hero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d Gene Inheritance
Zhao Yangjuan1, Zheng Kaili1, Ma Hongrui2
[1. Nanjing Yuhuatai Martyrs Cemetery Administration (Nanjing Yuhuatai Cadre College), Nanjing , Jiangsu 210012; 2.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 Jiangsu 211166]
Abstract: Yuhua heroic red archives are the precious original materials cast by revolutionary martyrs with blood and life, and the vivid witness of the Communists’ dedication to their ideas and cause. The good use of Yuhua heroic red archival resources and the narrative development of Yuhua heroic red archives are helpful to continue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highlight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red gene, and enable the spiritual cultivation of red gene. Under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red gene inheritance,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narrative development of Yuhua heroic red archives. First, multiple subjects should be linked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Yuhua heroic red archives narrative development. Seco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dig deep content elements to realize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Yuhua heroic red archives narrative development. Third, digital media should be used properly to promote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Yuhua heroic red archives narrative. Fourth, efforts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narrative turn to support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Yuhua heroic red archives narrative.
Keywords: Red Gene Inheritance; Yuhua Heroic Red Archives; Narrative Development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1]紅色檔案蘊含具有天然歷史聯系的故事元素,是構建中國話語和敘事體系的重要資源。敘事化開發紅色檔案資源,讓檔案發聲,講好紅色故事,有助于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近年來,學術界對紅色檔案敘事研究的熱度有所攀升,主要集中于紅色檔案敘事的應用與實踐。從研究內容看,包括紅色檔案敘事開發維度及路徑[2]、紅色檔案敘事解構與重構[3]、檔案宣傳中的敘事表達[4]、紅色檔案數字敘事研究[5]等,通過檔案敘事激活檔案價值,弘揚紅色精神;從研究視角看,有學者從數字人文[6]、場景理論[7]、跨媒體敘事[8]、視聽傳達理論[9]、心流理論[10]等視角切入,系統闡述紅色檔案敘事的優化路徑。整體而言,現有研究缺乏從“紅色基因傳承”的視角對紅色檔案進行敘事化開發研究,且對敘事化開發的構成要素及內在邏輯缺少關注,未立足于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的整體視域及敘事邏輯來闡述多角度、多層面、多元化的開發策略。
雨花臺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和愛國志士的集中殉難地,是雨花英烈紅色檔案形成、保存、展示的空間場域。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承載了雨花英烈“為理想獻身”的紅色記憶,是激活中國共產黨人紅色基因的初心密碼。本文基于“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以“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為切入點,引入敘事思維,提出敘事要素,把握敘事邏輯,全面系統探索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的優化策略,以期充分激發紅色檔案的敘事潛力,推動紅色檔案敘事向縱深發展,助力紅色基因在檔案敘事中深化傳承。
1 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的基本認知
1.1 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的概念界定
紅色檔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形成的文字、數據、照片、圖片、影像等展現共產黨人精神氣質的重要原始記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犧牲在雨花臺及周邊的革命先烈們所留下的家書、日記、詩詞、物件等珍貴資料,是他們在革命年代奮斗歷程的真實憑證,凝聚融匯成獨具特色、內涵豐富的雨花英烈紅色檔案。基于雨花英烈紅色檔案記載的歷史事實進行敘事化開發,通過可理解、可表達的話語模式或呈現方式,將檔案中多維關聯的敘事元素以特定的序列或體系進行建構、展演和深化并賦予其意義,“再現發生在特定時空中的事件”[11],立體活態地建構了革命先烈的成長軌跡、奮斗歷程及崇高品質,進而感知檔案敘事背后的深層隱喻,感悟紅色檔案所承載的紅色基因。
1.2 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的關鍵要素及構成邏輯
敘事要素是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基本元素,將紅色檔案中的各組成部分鏈接成有機整體。構建完整的敘事鏈條,通常包含“人、事、物、魂”等要素,基于此,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的要素包含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敘事主體為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人”,即傳承紅色基因的責任主體。敘事主體對雨花英烈紅色檔案內容進行整合、編排并復現,活化雨花英烈紅色記憶,激發受眾產生思想共振、情感共鳴并達成行動共識。一般情況下為雨花英烈故事的講述者、雨花英烈課程的講授者、雨花英烈相關展覽或視頻的創作者等。
第二,敘事內容為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事”,即傳承紅色基因的事件本體。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是對雨花英烈事跡及精神的真實記錄,因此敘事內容可以理解為紅色檔案所要表達的對象,即紅色檔案本身,涵蓋雨花英烈史料、遺物及衍生的英烈精神等多重內容,為敘事化開發提供素材和腳本,并以“敘事”的方式傳達其所映射的紅色基因。
第三,敘事媒介為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物”,即傳承紅色基因的物質載體。敘事媒介是敘事內容的呈現方式,為雨花英烈紅色檔案開發提供方式或工具。隨著時代的發展,敘事媒介從傳統的雨花英烈卷宗、書籍、展覽等靜態媒介,發展到新媒體時代雨花英烈相關的影視作品、線上展覽等動態影像,使受眾在檔案敘事中強化紅色基因傳承。
第四,敘事組織為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魂”,即傳承紅色基因的靈魂紐帶。“敘事表達是一系列事件和內容序化的過程。”[12]檔案敘事絕不是語言、文字、圖片等的簡單排列組合,而是通過一定的設計、整合等將紅色檔案內容進行組織聯合與邏輯接洽,串聯成連續完整的雨花英烈紅色事跡,進而促進紅色基因傳承。
2 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的價值意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檔案工作存史資政育人,是一項利國利民、惠及千秋萬代的崇高事業。”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充分發揮紅色檔案的存史、資政和育人價值,使其蘊含的深層意蘊與受眾的內心精神同頻共振,實現紅色基因的浸潤、感染和熏陶。
2.1 紅色檔案構筑雨花英烈歷史印記,賡續紅色基因的精神血脈
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凝聚在珍貴的紅色檔案中,成為詮釋中國共產黨人精神特質和精神信仰最真實、最直接、最權威的原始憑證,蘊含天然的紅色基因。雨花英烈紅色檔案作為共產黨人在革命年代為實現救國救民理想慷慨就義的歷史見證,有著真實生動的故事背景、有血有肉的故事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這些都是構成檔案敘事的重要因素和生動素材。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有機整合雨花英烈紅色故事,則能構筑完整的雨花英烈堅定理想信念、堅貞革命氣節和堅守為民情懷的歷史印記,映射出深植于中國共產黨精神血脈的紅色基因,從而深刻感悟共產黨人用鮮血和生命踐行理想信念、鑄就革命精神的崇高氣節和人格魅力,為弘揚黨的光榮傳統、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精神血脈提供檔案遵循、貢獻檔案力量。
2.2 紅色檔案熔鑄共產黨人初心使命,彰顯紅色基因的政治底色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國家內外交困、民族危難之際,歷經百年滄桑依然風華正茂,飽經風霜依舊不改本色,其原因之一就是堅守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與使命。雨花英烈中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其所展現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為民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正是共產黨人初心與使命的深刻詮釋,深深熔鑄在雨花英烈紅色檔案中,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奉獻犧牲的歷史縮影。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記載的歷史人物、英烈事跡等,進行深層次解讀和講述,對于新時代共產黨人傳承紅色基因、強化政治建設具有重要的引領和示范作用。通過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傳遞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通過講好雨花英烈紅色故事彰顯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從而汲取政治智慧、凝練政治共識、彰顯政治底色。
2.3 紅色檔案助力筑牢理想信念教育,賦能紅色基因的精神涵育
習近平總書記對檔案工作的重要批示強調,“要把蘊含黨的初心使命的紅色檔案保管好、利用好”。紅色檔案凝結著共產黨人在艱苦卓絕革命歷程中堅守信仰、矢志奮斗、不畏犧牲的革命精神,是堅定理想信念、實現鑄魂育人的生動教材,為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鮮活的“精神養料”。以雨花英烈紅色檔案中英烈人物的家書信件、重要物件及記載的歷史事件等元素為基礎,通過優化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的史實梳理、內容結構、話語表達、場景建構等,打造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時空,多維敘述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內涵意蘊,用心用情講好雨花英烈的感人故事,挖掘闡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所承載的紅色基因的歷史成因、生成邏輯、鮮明特征及時代價值等,從而深度用好用活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為紅色基因的傳承奠定生動鮮活的史料、史識和史論,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社會群眾等從雨花英烈紅色檔案中汲取精神養料,全方位、立體化地感悟雨花英烈信仰的力量,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的影響力和感染力,涵養共產黨人的“紅色氣質”,為紅色基因傳承賦能。
3 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的優化策略
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提及紅色基因傳承的必要性,明確要講好黨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據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把紅色基因傳承好,確保紅色江山不變色。[13]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闡明了新時代檔案敘事的努力方向,要用檔案資源講好紅色故事,讓檔案“發聲”,傳承紅色基因。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講好雨花英烈故事,需要從敘事要素著手,多主體、多途徑、多樣化、多角度推進開發工作,為傳承紅色基因貢獻檔案力量。
3.1 聯動多元主體,促進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開發協同化
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敘事化開發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敘事主體應積極尋求合作,打造協同敘事的全新體系,共同講好雨花英烈紅色故事,為傳承紅色基因提供人力、場域及技術支持。
第一,人際聯動,構建通力協作的社會協同體系。在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社會化參與”成為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的重要表征,為紅色基因的“大眾化”傳承提供重要支持。一是深度聯動主流敘事群體。雨花臺烈士紀念館講解員、雨花臺干部學院教師、雨花英烈研究會研究人員等作為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的主流敘事群體,應強化破界思維,進行“一體化”聯動協作,實現紅色資源融合、檔案故事共享,增強紅色檔案的敘事深度。二是積極聯動潛在敘事群體。邀請與雨花英烈紅色檔案征集、展陳、傳播有密切關系的親歷者、參與者等,從不同角度切入,共同講述雨花英烈紅色檔案背后的故事,突破已有人員的認知局限,增強檔案敘事的多面性。三是廣泛聯動社會敘事群體。聯系企事業單位、街道社區、大中小學等的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為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敘事化開發尋求“大眾”支持,構建多主體協調開發、公眾共同參與的社會協同格局。
第二,場域聯動,搭建內引外聯的館際協作體系。紅色基因作為紅色文化的內核與精髓,其傳承的本質在于紅色基因的累積和裂變,使文化具有延續性和再生性,推動各行各業進行紅色檔案的橫向整合與縱向重塑。雨花英烈紅色檔案集中保管于雨花臺烈士紀念館,其敘事化開發更多立足于本館領域。雨花臺應打破現有局面,加強內外聯通融合,構建“內引外聯”的館際協作體系,催動行業領域深度聯動。在內引方面,雨花臺烈士紀念館應承擔好場域聯動、館際協作的橋梁紐帶作用,上承中央、省、市檔案館,下啟省內外其他展陳雨花英烈人物事跡的紀念館,如惲代英紀念館、羅登賢紀念館等,形成“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聯盟”,開創檔案敘事協同聯動的新格局。在外聯方面,積極與博物館、圖書館、高校、黨史辦、報業集團等單位配合協作,整合館際力量,持續拓展檔案敘事范圍,實現良性循環的場域聯動,為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敘事化開發提供有力保障,共同講好雨花英烈紅色故事,傳承好共產黨人的紅色基因。
第三,技術聯動,創建縱橫交織的網絡協同體系。《“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強調要推動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發展檔案事業,創新公共文化管理機制和服務方式,推進文化惠民工程互聯互通、一體化發展。[14]注重數字化建設,創新打造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網絡平臺,為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開辟新路徑,能夠打破時空限制,全方位、多角度傳承弘揚雨花英烈事跡與精神。一方面,建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數據共享平臺。各單位對館藏的雨花英烈紅色檔案進行數字化建設,將紅色檔案數字資源上傳至“云”平臺,建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數據庫,促進紅色檔案應收盡收、共享共用,最大限度實現紅色檔案效能,為敘事化開發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提供強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建設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展示平臺。將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成果,如編研出版物、展陳展覽、影視作品等,同步上傳至“云”平臺,將“互聯網”作為敘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虛擬主體”,憑借互聯網高度的開放性,拓展受眾群體,講述紅色故事,提升紅色基因傳承的輻射面和影響力。
3.2 深挖內容元素,實現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開發情境化
檔案敘事強調以講述故事的方式組織和呈現檔案內容,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敘事化開發是“講好紅色故事、傳承紅色基因”的生動實踐。多向度、多層次、多模態挖掘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打造立體鮮活的敘事情境,使紅色基因深入人心。
第一,多向度線索挖掘,建構雨花英烈敘事情境。檔案蘊含人物、事件、主題等敘事線索,圍繞各敘事線索深入挖掘闡釋,推動檔案敘事向不同向度延伸,塑造多元的敘事情境,有助于提升紅色檔案敘事力,推動紅色基因傳承。一是“人物”線索。“雨花英烈”是構成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關鍵核心。挖掘“人物”線索,既要深挖烈士的成長軌跡及革命事跡,探索其映射的精神啟示及時代價值,又要細掘雨花英烈群體特征,將其與其他烈士群體進行比較,闡釋雨花英烈的偉大人格魅力。二是“實物”線索。雨花英烈留下的信件、物件等實物,作為“文物”收藏于雨花臺烈士紀念館,充分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及承載的紅色基因,讓文物釋放紅色力量。例如,館藏一級文物《死前日記》是賀瑞麟的獄中絕筆,從《死前日記》著手,講述獄中黑暗生活和被捕人員表現,能夠感悟烈士的信仰和忠誠。三是“事件”線索。事件由若干存在因果關系或前后接續的片段構成,對雨花英烈參與的歷史事件進行系統性敘事開發,如雨花英烈獄中斗爭、南京地下黨組織八挫八起等,從雨花英烈事跡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深化紅色基因傳承。
第二,多層次關聯挖掘,拓展雨花英烈敘事情境。檔案作為一種資源,匯聚著大量要素,各要素之間由于存在時間、空間等多層次關聯,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從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多層次關聯中深挖各要素的映射關系,有助于放大記憶細節,充實并完善烈士全宗,為傳承紅色基因提供史料支撐。一方面,挖掘“時間關聯”,縱深雨花英烈敘事情境。以“時間軸”的方式敘述,可以清晰展示檔案的時間敘事跨度。挖掘“時間關聯”,既要挖掘與某位烈士同一時間發生的事件或該時間活動人物的共時性內容,又要挖掘與該名烈士前后接續活動的歷時性內容,準確把握雨花英烈紅色基因的歷史演進,為傳承紅色基因理清脈絡。另一方面,挖掘“空間關聯”,橫拓雨花英烈敘事情境。空間是雨花英烈開展革命活動的重要載體,承載了雨花英烈開展革命活動所需要的信息資源。在挖掘“空間關聯”時,不僅要挖掘該空間的雨花英烈及其活動等,更要與“時間關聯”建立聯系,衍射與之相關的不同人物在不同時空的活動,多層次盤活“紅色家底”,延伸雨花英烈敘事情境的廣度和深度,強化大眾對紅色基因傳承的情感認同。
第三,多模態融合挖掘,深化雨花英烈敘事情境。檔案敘事中的多模態主要指多元形態的敘事資源,涵蓋文本、圖像、實物等多樣化類型,呈現“多模態”特征。將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不同模態有機“融合”進行敘事化開發,豐富檔案敘事的表現維度,是深化檔案敘事情境的新思路。一是融合顯性與隱性模態。將紅色檔案顯性模態的外化表征與隱性模態的內生特性深度融合,形成有情境、有情感的紅色檔案敘事。如史硯芬寫給弟弟妹妹的訣別信,“血跡斑斑”是訣別信的顯性模態,從紅色檔案的表層感受深化到背后的信仰和擔當,感悟雨花英烈的家國情懷。二是融合具象與抽象模態。具象模態往往表現為紅色檔案的外在物化形態,如雨花英烈革命文物等,抽象模態主要為“具象物體”所傳達的思想或精神方面的深層意蘊,如雨花英烈斗爭精神、犧牲精神等,基于“具象”模態,分析內在“抽象”語義,釋放紅色檔案的獨特魅力和精神力量。三是融合宏大與微觀模態。將雨花英烈故事置于大歷史背景下加以審視,實現歷史事件與現實空間的相融相合,提升檔案敘事的共情能力,打造共同記憶,更加深刻、長效地傳承紅色基因。
3.3 活用數字媒體,推動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開發多維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并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檔案工作要緊跟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步伐,全面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15]推進紅色檔案敘事化開發的“現代化”,數字技術潛力巨大,能夠多維呈現紅色檔案,讓紅色基因深植人心。
第一,數字化與人文化敘事結合。5G時代的媒介變革,揭開了“萬物皆媒”的新生態,在滿足紅色檔案人文情懷的基礎上,“加快檔案資源數字轉型”[16],兩者相互結合,深化紅色基因傳承。一方面,推進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的“數字化”,需要“人文支持”。毋庸置疑,新技術為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敘事化開發提供新方式,但技術由人的認知決定,不僅需要人的支持,更需要為人服務。以“人文”的方式賦予技術“檔案敘事思維”,使紅色檔案成為有溫度的情感記憶,在立體多維的檔案敘事中傳承紅色基因。另一方面,推進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的“數字化”,要注入“人文關懷”。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不斷深化,人們的精神文化追求邁向更高境界,相應地,對檔案敘事也提出新要求。打造“人性化”“個性化”的雨花英烈故事,可以借助數字技術生成大眾理解的檔案信息,如為青少年開發雨花英烈動畫,通過數字動畫、手繪技術等展現有血有肉的英烈形象,將紅色基因滲透到日常生活。
第二,矩陣式與沉浸式敘事并舉。《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3年)》指出:未來10—15年,數字技術的變革將席卷全球。[17]充分利用數字技術激活紅色檔案生命力,打造矩陣式、沉浸式展示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廣闊空間,實現紅色基因的深層浸潤。一方面,打造全媒體矩陣平臺,實現紅色檔案多渠道敘事。既要建設全媒體平臺的橫向矩陣,通過微信、微博、抖音、視頻號等多媒體平臺展示雨花英烈紅色檔案,促進紅色檔案多途徑滲透,又要建設全媒體平臺的縱向矩陣,使雨花英烈紅色檔案實現縱深布局,如深挖訂閱號、服務號、小程序等微信平臺的傳播特性,對雨花英烈紅色檔案進行差異化解讀,增強紅色檔案的精神感染力,有效傳承紅色基因。另一方面,提升全方位沉浸體驗,實現紅色檔案全景式敘事。沉浸式體驗多以場景模擬的方式實現,通過VR、AR、360°全景展示等技術復現雨花英烈紅色檔案,以劇本殺、網游等“二次元”的敘事方式,讓受眾在立體視覺特效與真實感官體驗中沉浸式感受雨花英烈的紅色歲月,為紅色基因傳承提供獨特的實踐路徑。
第三,虛擬化與可視化敘事交融。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紅色檔案的敘事形式迎來全新轉變,新興敘事媒介蓬勃發展并不斷升級,催生了虛擬化和可視化敘事技術,兩者交叉相融,為檔案敘事進行包裝和加工,助力紅色基因傳承。一方面,虛擬敘事可視化。“虛擬”并不是“虛構”,而是將雨花英烈真實題材通過虛擬技術“再現”并使其擁有自身特質,在此基礎上融入可視化技術,進一步增強視覺體驗。比如,虛擬建構雨花英烈所處年代的社會背景及斗爭場景,結合GIS歷史地理等可視化技術或繪制可視化圖譜,視覺展示雨花英烈的革命動向,再現先烈的奮斗歷程。另一方面,可視敘事虛擬化。可視化技術為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塑造了多維展示空間,將圖片、影像等可視化檔案通過虛擬技術動態呈現,借助VR眼鏡、裸眼3D等“虛擬”進入雨花英烈敘事時空,在“時光穿越”中真切多維地感受雨花英烈的信仰與人生,增強對紅色檔案深厚意蘊的理解與傳承。
3.4 注重敘事轉向,助力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敘事開發新穎化
米歇爾·福柯曾說:在語言和視覺是否相融的問題上,存在著各種可能世界。[18]轉變傳統的敘事組織,創新檔案敘事的想象空間,能夠為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紅色檔案的敘事“轉向”開發提供思路指引。
第一,創新敘事結構,從“線性”敘事轉向“非線性”敘事。傳統的檔案敘事注重時間脈絡或因果關系的“線性”架構,結構明晰卻較為封閉。在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從傳統的“線性”結構抽離,充分激活檔案能動性,“非線性”敘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使檔案從“封閉”走向“開放”,展現鮮活立體的烈士形象,再現雨花英烈紅色記憶。一方面,從時間敘事轉向空間敘事。與時間相比,“空間具有更強聯系與結合的力量”[19],與主體的情感聯系更為直接和深刻。善用紀念館內的展陳布局、展覽設計等空間場域,走進烈士的內心世界,深入解讀雨花英烈紅色檔案,有助于實現受眾與烈士的共通共鳴。另一方面,從順向敘事轉向逆向敘事。采用倒敘、時間交替、提前敘述未來等方式建立雨花英烈故事線,增強敘事層次。比如以雨花英烈鄧中夏生命的最后時刻為主線,選取鄧中夏領導五四運動、發動省港大罷工、被捕入獄等重要歷史時刻,感受在那個動蕩不安卻又熱血激昂的年代里革命烈士的赤誠之心,使受眾獲得更具沖擊力的情感觸動,促進紅色基因內化于心。
第二,創新敘事視角,從“外視角”敘事轉向“內視角”敘事。傳統的檔案敘事關注重大歷史事件、意識形態等主流與官方確定的宏大敘事,即“外視角”,與個人生活相去甚遠。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檔案敘事更注重從敘事主體出發,轉向“內視角”敘事,將“大寫”的“宏大歷史”轉變為“小寫”的“人的歷史”,使紅色檔案真正走進大眾內心。一是側重微觀視角。從雨花英烈的物件、話語等著手,講述雨花英烈的感人故事,比如從母親為冷少農親手縫制的棉衣入手,講述棉衣背后共產黨人的忠與孝,拉近受眾和檔案的距離。二是關注人物細節。借助一定的言語,描述雨花英烈在面臨公與私、國與家、生與死選擇時的外在表現、心理狀態等,講述革命者也有普通人的愛情與親情,激發受眾理解并認同雨花英烈的人生選擇。三是注重情感共鳴。雨花英烈與受眾在年齡、籍貫、職業等方面有著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兩者在心理特征、價值選擇方面存在著共通性。通過尋找情感共性,連接雙方的情感紐帶,激發受眾的情感共鳴,深刻感受雨花英烈犧牲精神的偉大。
第三,創新敘事樣態,從“單向”敘事轉向“交互”敘事。隨著公眾檔案意識的提高,他們更渴望在檔案敘事中由“被動參與”走向“主動感知”。紅色基因傳承視閾下,雨花英烈紅色檔案與受眾之間不再是“單向”流程,而是一種“交互”的動態關系,在“交互”中加深對紅色檔案的理解與體悟,深入傳承紅色基因。一是體驗式交互。展陳改造雨花英烈紅色檔案的物理空間,將紅色檔案的精神實質反映為空間表情,通過拍照打卡、獻花留言、電子沙盤等生成對紅色檔案的全息體驗,塑造敘事雨花英烈“信仰的力量”的空間情境。二是感官式交互。多感官組合在檔案敘事中日益突顯出重要作用,對受眾的知情意行產生潛在影響。通過選取部分特色性雨花英烈紅色檔案進行同比復刻,讓檔案走到大眾空間,轉化為具體可感的紅色記憶,引導大眾傳承紅色基因。三是人際式交互。信息流動存在于人與人之間,因此人際互動是促進紅色檔案“交互”敘事的重要方式。通過推出“沉浸式”講解,敘事主體化身歷史引領者串聯全程,利用紀念館中的還原場景,以情景再現的方式動情講述雨花英烈的感人事跡,使受眾在參與和互動中感悟雨花英烈的崇高精神。
*本文系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專項項目“烈士事跡在構筑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思政工作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20SJB0117)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貢獻說明
趙楊娟:選題確定,框架設計,論文撰寫、修改與定稿;鄭凱利:選題討論,資料查閱;馬宏瑞:經費支持,論文修改。
注釋與參考文獻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 OL].[2022-10-26].http://cpc.people.com.cn/ n1/2022/1026/c64094-32551700.html.
[2]趙彥昌,吉日格勒.抗美援朝檔案資源敘事化開發研究——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70周年[J].檔案與建設,2023(12):8-11.
[3]劉丹心.紅色檔案敘事中的互文性解構與敘事重構優化策略研究[J].檔案管理,2023(5):80-83.
[4]龍家慶.敘事表達在檔案宣傳中的運用與優化策略[J].浙江檔案,2020(1):30-32.
[5]黃夏基,盧澤蓉.我國紅色檔案數字敘事研究——基于省級綜合檔案館門戶網站的調查分析[J].檔案與建設,2023(6):31-34.
[6]朱彤,王興廣,陳賀琪.數字人文視域下紅色檔案傳承紅色基因路徑探析[J].檔案學研究,2023(3):112-118.
[7]邊媛,舒麗莎.場景理論視域下紅色檔案資源開發利用優化路徑[J].中國檔案,2024(2):72-74.
[8]何玲,馬曉玥.跨媒體敘事理論觀照下的檔案敘事優化策略——以紅色檔案為例的分析[J].檔案學通訊,2021(5):14-21.
[9]申曉晶,丁丹.基于視聽傳達理論的紅色檔案敘事活化思政課程探索[J].檔案管理,2023(1):88-89.
[10]孫大東,白路浩.心流理論視域下紅色檔案傳承紅色基因的向度與路徑[J].檔案學通訊,2022(1):15-22.
[11]楊光,奕窕.記錄媒介演進與檔案歷史敘事的變遷[J].檔案學通訊,2019(4):19-27.
[12]聶晶.杰拉德·普林斯的敘事理論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4:24.
[13]習近平.用好紅色資源,傳承好紅色基因 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J].求是,2021(10):4-18.
[14]中辦國辦印發《“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EB/OL].[2022-08-16].https://www.gov.cn/ 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
[15]陸國強.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 奮力書寫檔案事業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新篇章——在全國檔案局長館長會議上的報告[EB/OL].[2023-02-27].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2302/edef53f 544bb4eea8bfacd87fd8a223e.shtml.
[16]中辦國辦印發《“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EB/OL].[2021-06-09].https://www.saac. gov.cn/daj/toutiao/202106/ecca2de5bce44a0eb5 5c890762868683.shtml.
[17]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3年)》[EB/OL].[2024-01-09].http://www. 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1/t20240109_469903.htm.
[18]米歇爾·福柯.圖像理論[M].陳永國,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48.
[19]埃米里奧·馬丁內斯·古鐵雷斯.無場所的記憶[J].馮黛梅,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12(3):26-37.
(責任編輯:邵澍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