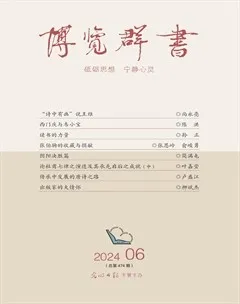《感遇》何以為《唐詩三百首》開篇之作
《唐詩三百首》是清代蘅塘退士孫洙編選的唐詩選集,此書影響深遠,問世不久就“風行海內(nèi),幾至家置一編”,被視為唐詩入門讀物的首選,也成為唐詩選本里流傳最廣遠的選本。該選本以張九齡的《感遇(十二首)》二首為《唐詩三百首》的開卷之作。我們以為,深究其原因,是很有意義的。
《感遇》其一:
蘭葉春葳蕤,桂花秋皎潔。
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jié)。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感遇》其七:
江南有丹橘,經(jīng)冬猶綠林。
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
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
運命推所遇,循環(huán)不可尋。
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孫洙選擇張九齡的《感遇二首》置之于開篇,大致基于以下三點考量。
于取詩宗旨考量
所謂感遇,孫洙引用《唐音注》注為“感遇云者,謂有感于心而寓于言,以抒其意者也”。以《感遇》名詩且成組出現(xiàn)始于陳子昂。被杜甫在《陳拾遺故宅》中稱為“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即就其《感遇》詩而言。張九齡《感遇》十二首作于其開元二十五年被貶謫荊州長史后,張九齡年近六十,其時張九齡如同被貶謫的屈原一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雖曰發(fā)憤抒情,然我們在通讀《感遇》十二首后的第一感受是其抒情與屈原、陳子昂之感遇抒憤大不同。
屈原兩次兩遭貶謫,然而“睠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而在“(《離騷》)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記·屈原列傳》),其借助于香草美人的書寫本欲表達忠心,而在班固等人看來是“露才揚己”顯君之過。陳子昂兩次入獄,一生一死,其《感遇》三十八首內(nèi)容豐富,有詠史、有言志、有游仙、有同情底層苦難,皆借此抒發(fā)自己壯志難酬,向往隱逸之情。
張九齡《感遇》十二首,雖有借鑒前人之意,然在內(nèi)容上比較單一,以抒發(fā)身世感慨,表現(xiàn)理想情操為主,在藝術(shù)上則是溫柔敦厚的含蓄表達。如《感遇·江南有丹橘》是詠物言志詩。“江南有丹橘,經(jīng)冬猶綠林”,開篇點題引出所詠對象“丹橘”是歷經(jīng)寒冬而持有綠意不會凋零的草木。一個“猶”字,是意外,是堅守,是詩人對丹橘的敬畏。“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古人講“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講的是地勢使之然,張九齡生于嶺南,自然明白此種道理,然而在這里他卻否定了“地氣暖”的因素,直接給出“自有歲寒心”的答案。丹橘能“經(jīng)冬猶綠林”是“自有歲寒心”決定的,非環(huán)境決定。此處張九齡以丹橘自喻,強調(diào)自己是有“歲寒心”是貞潔之士,是有“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君子之節(jié)。“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如丹橘這般有歲寒心之嘉木自可推薦給“嘉客”、朝廷、君王,奈何險阻重重不能上達天聽。“運命推所遇,循環(huán)不可尋”,這是在前面敘事的基礎(chǔ)上生發(fā)的命運感慨:人生的運命是可遇不可尋的,武略超群,太公釣于渭水;文章蓋世,孔子厄于陳蔡。“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全詩以反問結(jié)束。樹桃李自然能下自成蹊;樹丹橘也可以下自成蹊,問題在于丹橘沒有桃李的幸運。劉禹錫在《吊張曲江序》中說“寄詞草樹,郁郁然與騷人同風”,《感遇·江南有丹橘》與屈原《橘頌》同情共旨。張九齡與屈原命運又何嘗不相似呢。屈原作品有著強烈的情感抒發(fā),其詩托云龍,說迂怪,有忠有怨憤,其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皆與“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詩教相左。而張九齡則是借助于詠嘆丹橘、蘭、桂等草木之“高潔”和“歲寒心”來暗示了自己品格的高潔,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朝廷發(fā)現(xiàn)和重用的期待之情,此正是與“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相合之處。
張九齡“七歲知屬文”,年十三“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步入仕途后,張九齡以直道事君,在朝廷遭遇激烈的權(quán)利斗爭,自身也遭遇三黜,二次被貶外任,一次辭官歸養(yǎng)。這類似于《論語》中記載柳下惠的“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的經(jīng)歷。張九齡作《感遇》之時,正是被貶荊州長史的低沉期,縱觀十二首《感遇》我們看不到一絲“忿懟”。無論是詠物、抒懷、詠史,我們都能感受到他的情感與語言始終在“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邊界內(nèi)釋放和書寫。陳子昂《感遇》中還有“肉食謀何失,藜藿緬縱橫”“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的譴責,有“每憤胡兵入,常為漢國羞。何知七十戰(zhàn),白首未封侯”的詠史孤憤,而張九齡的《感遇》只有類似于《江南有丹橘》的詠物言志。他的詠物詩中,有著君子之志的朦朧表白,呈現(xiàn)出一種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苦而不言,笑而不語的含蓄之美。這是孔子論詩的思想、是《毛詩序》詩教觀的體現(xiàn)。《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張九齡的《感遇》所呈現(xiàn)的就是這種中和之美,這種溫柔敦厚之美。我們讀詩喜歡讀壯懷激烈之作,因為此類作品容易挑動我們的情緒;我們喜歡讀一針見血的深刻之作,因為這類作品能給人以酣暢淋漓之感;其實最難的是這種具有中庸之美,而以中和之狀態(tài)呈現(xiàn)出來的作品,這是心有驚雷,筆生春意的境界。孫洙身處文字獄盛行的乾隆之世,以溫柔敦厚的《感遇》開篇,以盛唐明相張九齡樹立標桿才更有利于《唐詩三百首》在當時的生存和流傳。
于風格即人考量
張九齡其人,以風度美著稱;其詩作古雅中庸,這種美也可稱之為“九齡風度”。
以“風度”來高評張九齡,始于唐玄宗。王讜撰《唐語林》載:
玄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眾,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舊唐書·張九齡傳》載:
林甫自無學術(shù),以(張)九齡文行為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悅。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知政事。后宰執(zhí)每薦引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
基于以上記載,“九齡風度”成為唐玄宗選拔公卿的標桿和審美標準。關(guān)于“九齡風度”學者,論者多矣。陳建森先生在《“九齡風度”與唐代文學的審美取向》一文中指出:
玄宗品評“九齡風度”,基于張九齡的“風儀”“品行”“文學精識”三個層面:一是張九齡“風儀秀整”令玄宗見之“精神頓生”;二是張九齡守正忠直,具有宰輔大臣應有的品行風范和預見性;三是張九齡以文學精識深得玄宗器重。
張九齡風儀秀整是其表,守正忠直是其品,論辯風生是其才,此三者是其風度的三個維度。文學即人學,風格見人格,如果以“九齡風度”的視角來關(guān)照《感遇》之詩,我們發(fā)現(xiàn)《感遇》諸作也正是“九齡風度”的文學性表達。
《感遇·蘭葉春葳蕤》《感遇·江南有丹橘》 兩首看似在詠物,一詠蘭、桂,一詠丹橘,只要我們稍加思考便可以發(fā)現(xiàn)這是張九齡運用傳統(tǒng)的比興寄托手法,表達自己謫居荊州時郁憤自省的情緒。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中指出:“陳正字起衰而詩品始正,張曲江繼續(xù)而詩品乃醇。”陳子昂的“詩品始正”,指的是他以“漢魏風骨”“風雅興寄”來拯救五百年來“彩麗競繁,興寄都絕”的文壇頹風。張九齡的“詩品乃醇”,指的是其詩歌創(chuàng)作中融入了屈原以來的興寄與儒家詩教的君子風骨。“蘭葉春葳蕤,桂花秋高潔”,春蘭多么茂盛,秋桂何其高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jié)”,春蘭、秋桂以自身的欣欣然生意,自成一種美好的節(jié)操風范。“江南有丹橘,經(jīng)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由歲寒心”,很多注家把這里直接對接屈原的《橘頌》。屈原的《橘頌》從橘樹的外貌描寫到精神的賦予,從而把“獨立不遷”“蘇世獨立”等精神融入橘樹之中予以贊頌。橘樹成為屈原自我精神物化的對象和精神的寄托,被劉辰翁稱為千古“詠物之祖”。
張九齡的《江南有丹橘》一詩,可題名《丹橘》或《橘頌》,其筆下之丹橘賦予的精神中注入了儒家君子風范和操守。“經(jīng)冬猶綠林”“自有歲寒心”兩句,讀來很容易映照《論語》中孔子那句“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后凋”是不凋,不凋是“經(jīng)冬猶綠林”,張九齡看似在詠丹橘經(jīng)冬不凋,其實是在表達儒家所倡導的“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的氣節(jié)。講“歲寒心”,張九齡沒有重復孔子的松柏,而是選擇謫居江南盛產(chǎn)的“丹橘”,一是此丹橘兼有孔子“歲寒后調(diào)”之品質(zhì)和屈原“獨立不遷”之精神。同時我們注意到“丹”,紅色。丹橘,是紅色的橘子映襯在綠林之中,是“可以薦嘉客”的果實,也是坦誠于君王朝廷的一片“丹心”。張九齡的《感遇》可以看作是政治表白,是借蘭、桂、丹橘來表達自己在政治上為君王貶謫下人格依舊保持高潔的品格。《唐詩三百首》在五言律詩一卷選了張九齡的一篇《望月懷遠》,就其主題而言,古來解讀者多以為是懷念遠方的親人或情人。王志清先生在《這〈望月懷遠〉之所懷》一文中強調(diào)了張九齡作為政治家的一面,提出“張九齡以情人相思而委婉表達君臣關(guān)系,乃古人所習用的香草美人的寄托諷喻,表現(xiàn)出一種怨婦心理與棄女形象,其所懷的那個‘遠’,乃皇城長安,乃皇帝玄宗也。”張九齡以直道事君而遭貶黜,在以上所選三首暗含政治抒懷的詠物懷遠詩中,我們看到委屈不甘為自我本心、佳節(jié)、高潔所沖淡,對君王剩下的是坦誠的表白和思念。《四庫全書總目》指出:
九齡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稱開元賢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許諸人下。……今觀其《感遇》諸作,神味超軼,可與陳子昂方駕。文筆宏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亦具見大雅之遺。
孫洙正是看到了張九齡作為、開元賢相,也看到了他文章高雅的一面,這才是“垂紳正笏氣象”,這才是不以仕喜,不以黜悲坦蕩襟懷的“九齡風度”,而這種從人格風度到作品風格的一致體現(xiàn)構(gòu)成了孫洙首選張九齡的重要原因。
于興寄作法考量
張九齡的《感遇》二首突破了文學對政治倫理的依附性書寫。文學具有獨立與文學的價值存在,然而隨著中央集權(quán)的加強和君臣倫理關(guān)系的凝固,站在政治的立場上則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屈原借助香草美人的意象來進行政治抒情以表忠貞赤誠,《毛詩序》要求詩具有“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的功能,曹丕《典論論文》高舉文章是“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的旗幟。阮籍《詠史》、陳子昂的《感遇》皆是政治不得志下的抑郁詠懷,這種借助詩歌來對政治倫理下不甘寂寞,希冀仕進情懷抒發(fā)都是一種政治依附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其目的是表達“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和“情人怨遙夜”的無奈。張九齡的可貴之處在于《感遇》中表達了一種“何求美人折”的對等狀態(tài)。春蘭、秋桂的生意盎然,欣欣向榮是自我形成的一種美好節(jié)操,非假外求,也不求認知。其“葳蕤”、其“高潔”,其“生意”、其“經(jīng)冬猶綠林”,均是自我生成,無關(guān)“地氣暖”的環(huán)境,不是“地勢使之然”的出身。雖是草木之屬,然持有“自爾為佳節(jié)”“自有歲寒心”的操守,“何求美人折”“何求薦嘉客”。春蘭、秋桂、丹橘的“自爾”“自有”,一個“自”字強調(diào)的是本身生成的品質(zhì),不是依附政治下的權(quán)力生成,是脫離了一切外在價值賦予下自我獨立價值的對等、多元性體現(xiàn)。“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霍松林《含蓄蘊藉,寄托遙深——說張九齡〈感遇〉(十二首選二)》一文中提出:
“誰知”并不等于“誰料”,而近似于“誰管”。蘭桂自為佳節(jié),自有本心,自行其素,自具欣欣生意,不求美人采擇;林棲者是否聞風,是否因聞風而相悅,誰知道呢?誰管它呢?
雖為草木,不求美人折、不求運命遇而自成風景。這是張九齡在宦海沉浮30余年后的深刻認知,這是他穿越官場現(xiàn)實后凝練的生命感悟。
而張九齡“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中給出了“草木——美人”的對等、多元的關(guān)系模式。沒有“美人折”,草木自有會“春葳蕤”“秋高潔”的欣欣生意,能有“聞風坐相悅”的價值體現(xiàn)。“何求美人折”中包含了“不求美人折”“不拒美人折”兩種情形;“誰知林棲者”中同樣也包含了“林棲者”是“聞風坐相悅”還是“聞風坐相厭”兩種情形。“何求”表達了草木對“美人”的無待態(tài)度,是求與不求我都在那里,是求與不求我都是我,求與不求我“本心”不改的獨立自由狀態(tài)。“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以一種含蓄的語言表達了一種堅定的立場,這是對自我人格的尊重,對自我生命的尊重,是詩人尊重現(xiàn)實又通過個體化的理解在對抗與逃避外給出了一個個體化的理解。
張九齡“草木有本心”的個體性自我人格、地位、價值的生成,是其通過《感遇》詩篇而給出的獨特思想性價值創(chuàng)造。這是孫洙選擇張九齡的《感遇》二首作為《唐詩三百首》開篇之作的最主要考量,也是《唐詩三百首》全書三百多首詩歌的精神奧義所在。在這種安置中,《感遇》暗中契合了孫洙自己的審美價值追求和人格精神的傾向。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是張九齡“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思想的淺層次激烈表達,孫洙放置于《唐詩三百首》的中間就在于以《感遇》的看似溫柔敦厚的表達中保護了《夢游天姥吟留別》的激烈、沖突、對抗。如果張九齡的《感遇》沒有上升到這種解讀,而停步于對丹橘不遇的詠嘆,這和陳子昂的《感遇》有何區(qū)別?只是同一不遇主題的重復書寫,主題相同下的個體書寫差異而已。唯有如此解讀,我們才能把此詩上升到一個全新的角度,才能明白孫洙對《感遇》不為人知的深刻思考與深邃洞見。
(作者系文學博士,長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