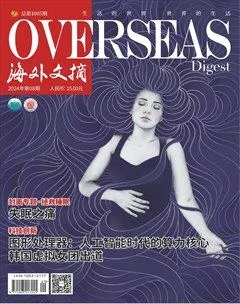南極帽帶企鵝:在碎片睡眠中生存
科學家們發現,處于“一次睡四秒,一天1萬次”睡眠模式的帽帶企鵝仍能維持機體正常運作。

會議上發言者的講話聲逐漸變為背景音,你感覺眼皮越來越重,昏昏欲睡。突然間,你變得非常清醒,趕緊環顧四周——有人看到我打瞌睡了嗎?你剛才進入了“微睡眠”,這是一種很短暫的意識喪失,幾乎一開始就結束了,持續不了幾秒鐘。
一次僅睡四秒鐘聽起來很像一種折磨,但這對帽帶企鵝不算什么,它們每天這樣小睡1萬多次。在南極洲喬治王島研究鳥類的科學家說,帽帶企鵝在繁殖季需要時刻關注自己的巢穴,保護蛋和雛鳥免遭襲擊。它們每天累計能睡大約11個小時,不會進入深度睡眠。
“人類無法維持這種狀態,但帽帶企鵝可以。”法國里昂神經科學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保羅–安東尼·利布雷爾說,“睡眠類型的復雜程度遠超大多數教科書上的描述。”
研究人員在20世紀80年代就研究過企鵝的睡眠。他們將捕來的非繁殖期帝企鵝安置在便于觀察的庇護所,記錄了它們短時間內零碎的睡眠,并稱這種表現為“睡意”。而近期的研究發現,帽帶企鵝整天的睡眠都是這樣斷斷續續的,表明它們沒有進入深度睡眠。它們不管是臥著還是站著,都能睡覺。
研究人員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報告指出,帽帶企鵝繁殖期的睡眠是極端碎片化的,但這種微睡眠能讓它們的體力得到恢復。企鵝群很健康,繁殖很順利。
幾乎所有動物都需要睡覺,但睡覺會讓動物因為失去對外界環境的快速反應能力而更容易被捕食。利布雷爾說:“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動物行為,也受到了自然選擇壓力的影響。”大多數睡眠方面的研究都是在實驗室等受控環境內進行的,研究對象一般是人類或老鼠,但技術發展讓在真實環境中研究其他物種成為了可能。
研究人員通過腦電圖監測和連續錄像來研究野外的帽帶企鵝,與睡眠相關的大腦活動和閉眼代表它們進入微睡眠。被監測的14只帽帶企鵝處于孵蛋階段,生活在一個擁有2700多對繁殖期企鵝的聚落。觀察發現,它們午間的睡眠深度略有增加,因為那時被捕食的風險最低。
對帽帶企鵝父母來說,一方外出覓食時,另一方就要獨自在巢中守上幾天,延長睡眠時間可能會讓它們的蛋和雛鳥面臨被褐賊鷗捕食或被其他企鵝攻擊的風險。
研究發現,有些物種睡得很少,而且這對它們清醒時的表現似乎沒有產生負面影響。比如,非洲叢林象平均每天睡兩個小時,而且大多是站著睡。它們有時會連續48小時不睡。
在有些物種中,睡眠時間存在性別差異。比如,雄性果蠅每天需要睡超過10個小時,而雌性果蠅只需要睡4個小時,甚至少于15分鐘的睡眠也不礙生存。

軍艦鳥需要飛行數月才能完成跨洋遷徙。在此期間,它們每天靠不到一個小時的睡眠來支撐前行和捕獵。不過,軍艦鳥回巢后就開始“囤覺”了——它們每天睡近13個小時。
研究人員發表在《睡眠進展》雜志上的文章指出,這些例子挑戰了“清醒時的表現取決于睡眠”這一流行觀點。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學者克里斯蒂安·哈丁和牛津大學生理學教授弗拉迪斯拉夫·維亞佐夫斯基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相關文章指出,睡眠益處是逐步累加的,而利布雷爾等人的數據可能是證明這一點的最極端的例子。
人們普遍認為,碎片化有損睡眠質量。哈丁和維亞佐夫斯基指出,證明帽帶企鵝的睡眠模式對自身無害剛好能挑戰這一觀點。
研究人員認為,帽帶企鵝采取這種睡眠策略可能是對南極嚴酷環境的適應。那么,當生存環境改變時,其他物種是否也可以靈活地調整睡眠結構呢?
“我們還不知道這種睡眠模式是否也能讓人類受益。”利布雷爾說。人類的生理機能與帽帶企鵝不同,貿然模仿不可取。
這或許不是什么壞消息。畢竟,每天睡1萬個四秒鐘怎么聽都像噩夢。
編輯: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