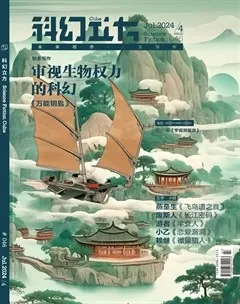審視生物權(quán)力的科幻
科幻小說的魅力不僅在于對(duì)未來科技及其應(yīng)用的奇思妙想,更在于它對(duì)人類自我的深刻審視。以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會(huì)夢(mèng)見電子羊嗎?》為例,這部經(jīng)典科幻之作通過描繪一個(gè)未來的反烏托邦世界,深刻探討了自我意識(shí)的問題。小說中的仿生人具備與人類相似的情感和記憶,這使得他們?cè)趥惱砗偷赖律吓c人類無異。然而,仿生人的身份卻始終受到質(zhì)疑,他們被視為“非人”的存在。這部小說被先后改編成了兩部電影,都是很多科幻迷的最愛,我們從銀幕上可以更直觀地感受仿生人的存在。
馬克思的“物化”理論認(rèn)為,技術(shù)進(jìn)步會(huì)導(dǎo)致人類自我認(rèn)知的異化。在這種異化過程中,人類逐漸失去對(duì)自身本質(zhì)的認(rèn)知,仿生人的存在進(jìn)一步挑戰(zhàn)了人類身份的邊界,促使我們反思“人類”這一概念的內(nèi)涵。但科技發(fā)展到今天,人類已經(jīng)不僅僅被異化,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包括腦機(jī)接口等新技術(shù)塑造出來的后人類,對(duì)于傳統(tǒng)人類來說,都是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了。“非人”即“異己”。從“異化”到“異己”,是我們今天不得不深入思索的人類處境。
在這里,我又一次驚訝于福柯的超前思想。在《性經(jīng)驗(yàn)史》當(dāng)中,福柯對(duì)“生物權(quán)力”(Bio-pouvoir)做出定義:“生物權(quán)力是一套涵蓋力量關(guān)系的矩陣,將生命與生命之間的機(jī)制納入明確的演算之中并以知識(shí)型權(quán)力作為改變?nèi)祟惿膭?dòng)力。”這句話比較燒腦,闡釋空間很大,在這里不展開。但給我們帶來的啟發(fā)是,科技對(duì)人體的改造和控制構(gòu)成了新的權(quán)力形態(tài)。在這種新的人類形態(tài)下,個(gè)體的自由和自我認(rèn)知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馬斯克的腦機(jī)接口公司Neuralink(神經(jīng)鏈接)最近所取得的實(shí)際進(jìn)展,給世人帶來了極大的震撼,讓這一技術(shù)從科幻走向現(xiàn)實(shí)。通過腦機(jī)接口,人類可以極大地提升認(rèn)知能力和身體機(jī)能,但也面臨身份和隱私的巨大挑戰(zhàn)。我相信,很多人都對(duì)此進(jìn)行了深入思考,但科幻小說對(duì)此進(jìn)行的反思則顯得更加生動(dòng)、具體,可以展開的話題也更加開闊。
本期劉十九的短篇小說《萬(wàn)能鑰匙》就是聚焦于這個(gè)話題,并且以芯片為敘事人,它既審視宿主,更審視宿主周圍的人,因此敘述獲得了一種絕佳的距離感———不遠(yuǎn)也不近——來審視人類的欲望及其權(quán)力的濫用。我們此前也說過,科幻與懸疑經(jīng)常如影隨形,這篇也不例外,層層反轉(zhuǎn),嵌套了許多科幻敘事。因此,這個(gè)短篇實(shí)際上有著中篇乃至長(zhǎng)篇的內(nèi)核。
小說的創(chuàng)意與小說的技巧是密不可分的。技巧原本只是小說的常識(shí),像人物、視角、情節(jié)等,這些都是小說的常識(shí),技巧當(dāng)然也包含在這些常識(shí)內(nèi)部,但更重要的是,好的創(chuàng)意才會(huì)帶來技巧的飛升。而好的創(chuàng)意來自思想,來自觀察,來自困惑。技巧不是為了花哨而生搬硬套,技巧是為這些創(chuàng)意的精神內(nèi)核服務(wù)的。
因此,我在這里再?gòu)?qiáng)調(diào)一次,科幻小說是一種人類對(duì)自我強(qiáng)烈審視的載體。通過各種“黑科技”的設(shè)定,讓我們得以觸碰人類形態(tài)的邊界,甚至躍出邊界以外。隨著科技不斷進(jìn)步,科幻小說將成為人類理解自我、審視自我、定義自我的一種極為重要的藝術(shù)裝置。
主持人:王威廉
作家,文學(xué)博士,中山大學(xué)中文系創(chuàng)意寫作教研室主任;著有小說集《野未來》《內(nèi)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zhǎng)的聲音》《倒立生活》,文論隨筆集《無法游牧的悲傷》等;曾獲“紫金·人民文學(xué)之星”文學(xué)獎(jiǎng)、十月文學(xué)獎(jiǎng)、花城文學(xué)獎(jiǎng)、茅盾文學(xué)新人獎(jiǎng)、華語(yǔ)青年文學(xué)獎(jiǎng)、華語(yǔ)科幻文學(xué)大賽金獎(jiǎng)、中華優(yōu)秀出版物獎(jiǎn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