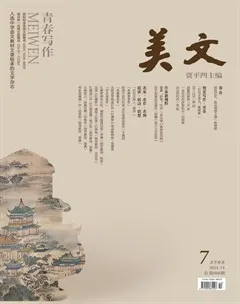豫·人
“一保官王恩師延齡丞相,二保官南清宮的八主賢王,三保官掃殿侯呼延上將……”《滿(mǎn)江紅》的上映,便帶火了別出心裁的“搖滾豫劇”配樂(lè),也讓豫劇火了一把。豫劇一尺水袖甩出嗔怒哀怨,一寸舞臺(tái)品味人間百態(tài)。
我的老家與河南搭界,素有戲劇之鄉(xiāng),當(dāng)?shù)匾灿袑?zhuān)業(yè)的豫劇團(tuán),在當(dāng)?shù)睾椭苓叺貐^(qū)進(jìn)行演出,每到過(guò)年過(guò)節(jié)都要搭戲臺(tái)唱大戲來(lái)慶祝節(jié)日。有一次跟著爸媽回老家,正趕上鎮(zhèn)上有豫劇演出,我跟著爸媽去鎮(zhèn)上看大戲,親身體驗(yàn)了看大戲的氣氛,在戲臺(tái)上,生旦凈末丑各種角色輪番上場(chǎng)表演,鑼鼓喧天,臺(tái)下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叫好聲,小販的吆喝聲接連不斷。有人在沒(méi)有開(kāi)戲之前就早早地占了好位置,把各種吃食擺在那里,邊吃邊看。有的人看戲看得入了迷,隨戲曲的情節(jié)時(shí)而大聲歡笑,時(shí)而又抹起了眼淚。
初春時(shí)節(jié)再次回到老家,正在田間漫步,忽然聽(tīng)到遠(yuǎn)處傳來(lái)了熟悉的豫劇:“過(guò)罷了正二月又到三月,桃杏梨花開(kāi)滿(mǎn)坡,滿(mǎn)地莊稼青啊綠呀,綠呀青啊,青青綠綠綠綠青青,綠油油綠油油,今年的糧食保證比往年多,嘿,保證比往年多。” 熟悉的豫劇唱腔,猶如一條清澈的小溪,流淌在我的心間,沐浴著早春的陽(yáng)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空氣中彌漫著泥土的芬芳和春小麥的清新,這是屬于家鄉(xiāng)的味道,看著田間綠油油的莊稼還有辛勤勞作的人們,他們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在這片土地上播種希望,收獲幸福。他們的笑容是那么樸實(shí)和真摯,讓人感到一種莫名的感動(dòng)和敬意。
我不知不覺(jué)地向那聲音傳來(lái)的方向走去,只見(jiàn)一位老伯一邊鋤著地,一邊唱著豫劇。他看到我驚喜而又崇拜的眼神:“妮兒,好聽(tīng)不?我就好這一口,干活的時(shí)候就想唱幾句,這樣才得勁。”我看到這位老伯臉上滿(mǎn)意而憨厚的笑容,我知道豫劇對(duì)于他而言是多么重要,豫劇已經(jīng)融入了他的生活,而豫劇也來(lái)源于他的生活。
就是在這一刻,我真正認(rèn)識(shí)到了離開(kāi)了這方淳樸的人民和土地,再好的戲也出不來(lái)。豫劇,憑借其喜聞樂(lè)見(jiàn)的表現(xiàn)形式,深深地根植于勞動(dòng)人民的生活之中,深深地根植于這方淳樸而肥沃的水土之中。我認(rèn)識(shí)到僅僅學(xué)習(xí)豫劇的基本知識(shí)和進(jìn)行豫劇賞析,還不能真正領(lǐng)會(huì)到豫劇這種藝術(shù)形式的真正魅力和靈魂,需要到豫劇這種藝術(shù)的發(fā)源成長(zhǎng)的地方去,深入到藝術(shù)的成長(zhǎng)土壤中去,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因?yàn)槿嗣袢罕姴攀撬囆g(shù)表達(dá)的最直接呈現(xiàn)者。
正是這種豫劇與生活和勞動(dòng)人民有機(jī)統(tǒng)一的共同體,才為多樣式的中華藝術(shù)長(zhǎng)廊塑造了生旦凈末丑的多彩人物形象。如《定軍山》的黃忠,雄勁威武;《梁山伯與祝英臺(tái)》的梁山伯,瀟灑斯文;《拾玉鐲》的孫玉姣,純潔天真;《穆桂英掛帥》的穆桂英,英姿颯爽;《連環(huán)套》的竇爾敦,粗豪俠義,等等。王實(shí)甫《西廂記》中的小紅娘成為俠義智慧的化身,融入大眾對(duì)美好生活的向往,體現(xiàn)對(duì)善良、熱情、勇敢美德的追求。 “其事多忠孝節(jié)義,足以動(dòng)人;其詞直質(zhì),雖婦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dú)鉃橹畡?dòng)蕩。”戲文唱詞中體現(xiàn)的善惡分明、懲惡揚(yáng)善、褒忠貶奸,戲中人身上具有的愛(ài)國(guó)情懷、優(yōu)秀品格、傳統(tǒng)美德,戲曲舞臺(tái)虛實(shí)相生、以形寫(xiě)神的大寫(xiě)意,無(wú)不體現(xiàn)著中華民族對(duì)和合共美的追求,詮釋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蘊(yùn)含的精氣神。
人是文化藝術(shù)的表現(xiàn)者,也是文化藝術(shù)的享受者和受益者。文化藝術(shù)可以讓人成為感性的人、理性的人、完整的人、自由的人。文化藝術(shù)豐富了人性,也深刻了人性。通過(guò)文化藝術(shù),我們獲得的不僅是美感,還有心靈和精神的自由,以及整體性的全面發(fā)展。文化藝術(shù),是人的藝術(shù)。藝術(shù)是人的本質(zhì)力量對(duì)象化的一種實(shí)踐活動(dòng)。沒(méi)有人,就沒(méi)有文化藝術(shù)。同時(shí),文化藝術(shù)的特性也對(duì)人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人之所以離不開(kāi)文化藝術(shù),就在于人的生命需要文化藝術(shù),人向往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使得人從生命深處召喚文化藝術(shù)滿(mǎn)足。
正如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所強(qiáng)調(diào)的:“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huì)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chǎng),也是社會(huì)主義文藝繁榮發(fā)展的動(dòng)力所在。”我將以學(xué)習(xí)豫劇等傳統(tǒng)藝術(shù)文化為契機(jī),賡續(xù)歷史文脈,以時(shí)代精神增強(qiá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藝術(shù)文化的生命力,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的傳承者和弘揚(yáng)者,這樣必將收獲豐盈的人生,成就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