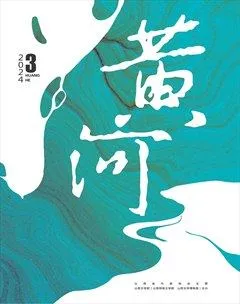離土進城的撕裂之痛
“每天早晨,父親陳先土的第一件事兒是穿戴好衣服坐在門枕上,點燃一根煙一邊抽一邊瞇著眼朝遠處看。他花十幾分鐘的工夫把一根煙抽完。每一口煙在他的肚子里轉一圈,再從鼻子甚至眼睛里冒出來,便不再是煙了,而成了淡淡的霧氣。”
這是陳倉《后土寺》的開篇,悠然恬淡,一幅鄉村水墨畫。
“透過霧氣,他似乎把整個村子都看空了,把幾畝莊稼看透了,把一座大山都看穿了,最后看到兒子陳元坐在一千公里之外的半空中。”
寧靜致遠,父親牽掛著千里之外的兒子。
如此美好,接下來的卻是讓作者、讀者都痛楚的撕裂。
《后土寺》有兩條脈絡,一條是兒子陳元在后媽去世后放心不下獨守空落落一座院子的孤寂的父親陳先土,想盡辦法帶父親進城;一條是父母離異的留守兒童麥子對爸爸陳元無盡思念,進城尋找父親陳元。牽扯兩條脈絡的是既是身為兒子,又是身為父親的陳元,到城市里打拼生活的辛酸與不堪,是這個時代千千萬萬從鄉村涌向城市的打工人的縮影,交織、牽拽著鄉音血脈,切割、撕裂著一代人離土進城的心路和根脈。
一、帶父親離土的根系撕裂
“土可生白玉,地內出黃金。”枝繁葉茂如一棵大樹的陳氏家族,傳到陳元這一輩,樹葉落光了,枝丫枯干了,已“不再像一棵樹了,而像顛倒過來的一根小草”(《后土寺》16)
枯去的枝丫倒過來是小草下面枝枝蔓蔓的根系,牢牢地吸附固守著剝離不掉的泥土。小草(陳元)不是蒲公英,隨風輕輕一吹,就飄到了千里之外的城里,他是被移栽到城市的一棵樹。
樓下邊的草坪沒有完全鋪好,有幾棵碗口那么粗的樹是不認識的,被東倒西歪地扔在旁邊,樹根用繩子包扎著———那些樹都是在外地培育好的,然后連根一起被拉到上海,準備移栽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它們的境遇與我一模一樣……(《后土寺》397—398)
陳元的父親陳先土是樹根,也是緊緊抱著樹根和泥土的繩子。
陳元早就進城了,是大上海的記者。然而,陳元并沒有真正進城。“自從到了上海,當陳元發現人家尤其在乎出身的時候,一般人問陳元是哪里人,他多數是不回答的。如果被逼急了,或者要填個簡歷什么的,陳元只說是陜西的。”(《后土寺》21)
詩人潞潞在《鄉村的悲劇》(讀李杜的詩隨感)里寫道,“我記起新疆朋友說的一段話。他說,他見過巴里坤草原上哈薩克人的牧羊犬,兇猛異常;但就是這些狗,它們偶爾經過烏魯木齊的街市時,一個個貼著墻根,即使在電線桿下撒一泡尿,也是東張西望一臉膽怯的神色;他曾經為那些狗驕傲,此時卻不得不悲哀了。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類比,是一種貶低,那就錯了……從某意義上說,我們的確像巴里坤草原上的那些狗……從鄉村文化轉入城市文化,實際上是把一個完整的人一分為二,使和諧變為不和諧,這種分裂的痛苦是相當大的,這種傷害也將是刻骨銘心的……是對過去生活的否定,是一次殘酷的分裂,是痛苦至極的再生。”
塔爾坪,是陳元進城的牽拽。埋葬了后媽,牽掛陳元的就只有七十多歲的老父親了。陳元的想法簡單,人死了,就沒有了牽腸掛肚,父親跟自己去上海是順理成章的事。
“你老太嗲老太奶,你嗲你奶,怎么辦?……死了就可以不管了?你媽你哥,他們也死了,難道不用上墳了?”(《后土寺》20)在塔爾坪生活了一輩子的老父親陳先土說道,塔爾坪的泥土、一草一木,以及過日子、打發時間的習慣和方式都是融入在父親的生活里,乃至血脈里的。還有一頭大肥豬,在兒子陳元軟磨硬泡,甚至冒著丟掉工作的風險又續了幾天假的猶豫中,父親說起了要喂到過年才能殺的一頭豬。這是眼前父親牽掛的唯一活物。陳元請來了表叔殺豬佬陳先株把豬殺了。殺豬的當口,父親突然回來了,啪的一聲,把一只碗摔在地上,十分生氣,“誰讓你們殺豬的?……你們曉得這頭豬是誰養的?是你后媽養的……你后媽死了,這頭豬更要繼續養著,起碼讓我養到過年吧?”
殺豬(《后土寺》18—26),硬生生斬斷了父親的又一支心蔓。
老戲(《后土寺》26—35),讓父親抬起頭,眼睛一亮的老戲,冬天不種莊稼,湊在一起唱幾天的老戲。會唱老戲的麻花子,兒子在山西煤礦招了上門女婿,女兒嫁去了河南,七八年沒回家了,整天一個人在家里,說話的人也沒有,孤單出病來,發不出聲,成了啞巴。說不了話的啞巴,一看到陳元心里就興奮亮堂起來,曉得老伙計想聽老戲了。把式、道具、戲服收拾好,扭著麻花步子拉著陳元就上路了。父親早早地在院子里掛上了大紅燈籠,扯了綢緞被面拉作幕帳,包谷稈子隔了登臺亮相的屏風,搭好戲臺。臺下端端正正坐了十幾個人,等著看戲。沒等陳元攔擋,麻花子跨上戲臺,揮舞著一根鞭子,在咚咚鏘的鑼鼓聲中,風塵仆仆轉了一圈又一圈,唱不出一絲聲音,想鯉魚打挺,躺在地上沒有彈起來,像半條在地上掙扎的蚯蚓。知道了實情的父親把麻花子扶到床上,對著麻花子字不正腔不圓地唱,前半夜唱,后半夜嘟嘟噥噥地說,不曉得唱了多少遍,嘟噥了多少話,麻花子哭了,父親也跟著哭了。又一根牽掛和念想也斷了。
陳元想著法子折騰幾天下來,還是沒能安頓好父親,十分不安又茫然不知所措。在陳元看來,老父親放不下的兩畝地,再好的年成,收一千多斤麥子、一千多斤苞谷、兩千斤洋芋,值多少錢?放在上海,一輛車子抵得上父親種兩三輩子的莊稼。
“賬能這么算嗎?如果都那樣算的話,世上還要我們農民干什么?沒有一個農民種地,世上的人吃什么?總不能直接啃鋼筋水泥和喝玻璃碴子吧?”父親的心思陳元不是不懂,這是城市與鄉土的割裂,父親與兒子情感的撕扯。
后媽去世了,養的豬殺了,唱老戲的老伙計啞巴了,父親還是不愿離開鄉土,把回上海的兒子送出村口,送到石門鎮,看著兒子坐上去縣城的班車,獨自立在初冬的寒風中,像一棵大樹上僅剩下的幾片葉子。車子爬到半山腰,父親仍然站立在橋頭,像一只小小的螞蟻被迅速卷入茫茫的霧氣寒煙之中。
送走兒子的父親,又坐回門枕上點燃一根煙,卻已亂了內心的安寧,幾口就抽完了,沒有從鼻子眼睛里冒出來化成霧氣,從嘴里直接吐出來,煙還是煙,濃濃的煙,父親什么也看不空了,看空的是自己,慌慌張張中,一個破舊的收音機,重又回到了父親的生活中。
收音機(《后土寺》35—40),是陳元親媽去世后父親買的。地里干活,山上放牛割草,父親把收音機都帶在身邊,收聽的內容只有一個,晚上短波,白天中波,清一色的老戲,后來又增加了一項,聽天氣預報,不是陜西天氣,不是河南天氣,是陳元所在城市的天氣。有一年聽預報上海有十幾級臺風的時候,老父親急急地跑到鎮上打電話提醒陳元,不要讓風給吹跑了。
后來,耳朵聾了的父親,還是不離不棄地把收音機帶著身邊,音量開得很大,吵了村子里的安寧,大家罵,你個聾子,聽什么收音機呀?父親笑著說,我是聾子,收音機又不是聾子。
父親醒著,收音機就醒著;父親睡了,收音機不見得睡得著。勞累過度的收音機壞掉了,父親花了好大的價錢請人修好了,修的價錢抵得上再買一臺收音機了。修好后的收音機父親沒舍得再開(自己是聾子,開不開沒啥差別了),卻天天搬進搬出,放在身邊,擦上一遍又一遍。有個古董販子想二百塊收走,父親多少錢都不賣。
賬不能那么算,父親給陳元打了個比方,“如果那不是一臺收音機,而是自己的一個媳婦,她無論唱歌還是罵人,你什么都是聽不見的,你是讓她坐在身邊嘮叨呢,還是把她趕走或者賣掉?”
放不下父親的陳元,在回上海的途中聽了偶遇的遠房嫂子點撥,在縣城下了車,直奔電器商場買了一臺二十五英寸的彩電返回到塔爾坪,有了電視,父親又能看老戲了。用嫂子的話說,“電視里有戲曲頻道,秦腔、豫劇、越劇、京劇,《鍘美案》《天仙配》《包青天》《屠夫狀元》,想看什么沒有呀?”
為了讓父親看上不帶雪花點子的電視,陳元又買回來衛星大鍋支在房頂上,河南臺、陜西臺、中央臺,好幾套電視節目收到了,從大白天等到天黑,從天黑守后半夜,又守到天亮,沒有收到一個戲曲節目。
“父親安慰陳元說,比收音機好多了,起碼能看到人影子了。”
聽馬鐵匠說,一臺電視機一個月要用上百度電,父親趕緊拔掉了插頭,還是拿出了收音機,不時地看看收音機,看看那一閃一閃的亮點。
上百度電能花多少錢?陳元說電費由自己付,父親還是那句話,“你的錢就不是錢嗎?”
父親用電,“天不黑透不開燈,而且還備用了兩個燈泡子,一個三十瓦,一個十五瓦。在陳元回家的時候,他會換上三十瓦的,陳元前腳一走,他后腳就換成十五瓦的。”
收音機的紅燈不閃了,啪的一聲,一道紅光,一股黑煙,父親的收音機也變成了啞巴。啞巴收音機仍然被父親擺在香案上,擺在他能看得見的地方,仍然不時地拿下來擦一擦。
寂寞是可以忍受的,而逝去了一個又一個親人的父親,沒有了豬,不能看老戲,不能聽收音機的父親,一下子就老了,爬上閣樓掛臘肉的時候,糊里糊涂地從梯子上摔了下來,臉色慘白得像一張白紙,神情恍恍惚惚的。他看見了自己給自己準備的老衣。
“如果這時候陳元離開塔爾坪,無異于置父親于死地。沒有父親,他陳元要上海干什么呢?他陳元要遠方有什么用呢?”(《后土寺》 42)
打麻將(《后土寺》41—52),打麻將,在塔爾坪被認為是敗家。唯一會打麻將的,陳元的大伯陳先木,在解放前打牌敗光了家里的銀元,敗掉了十幾畝的土地。幾十年后麻將風再次興起后,大伯手癢癢,想教幾個老人打麻將,被罵得狗血噴頭。打牌成癮的大伯沒得好死,在一個雪天的夜里從麻將桌上下來上廁所,掉進廁所活活淹死了。為了安頓好父親,陳元顧不了那么多了,想到了要教父親打麻將,想著父親學會打牌了,最好是上癮了,生活就有寄托。陳元費盡心思誘導父親對打牌有了興趣,松了口,以碼牌比作碼柴火,摸著麻將就像是摸著奶奶的骨頭,總算是讓父親學會了打麻將。父親卻反悔,說打麻將會上癮,不能學了他大伯,輸了銀元,輸了地,還輸掉了家里的三桿獵槍。陳元煞費苦心,在小賣部里買了幾包猴王煙,一人發了一包,把開小賣部的陳先水,殺豬的陳先株,馬鐵匠約到家里打牌,引誘著父親終于坐到了麻將桌上。幾個老人鬧了別扭,陳元背著父親分頭給三個老人打電話一頓勸說,無奈之下答應給每人發一百塊錢,求著三個老人陪父親打麻將。沒成想,兩個月前還一個人放倒陳元家一頭大肥豬的陳先株,中風了,上廁所連自己的褲子都解不開了。寄希望于打麻將消遣父親寂寞孤單的愿望也落空了。
長槍(《后土寺》52—58),離開塔爾坪回上海的陳元,“不停地回過頭看著父親,又看看只剩下父親一個人的院子,越來越像一只餓死的腹中空空的畜生,透著一絲絲的開始腐爛的氣息。”陳元揪心,父親不舍,順道去看二姨娘。陳元的親媽去世后,父親心里一直裝著二姨娘,也與舅娘、小嬸有解釋不清楚的風言風語。后媽死了,舅舅死了,陳元的舅舅,用比自己還長出一截子的長槍把自己打死了,死在他到死也不愿離開的刺溝,死在了他自己的家,刺溝最好的房子里。這是陳元小時候睡過的房子,是舅舅舅娘住了六七十年的家,成了舅舅的墳。
二姨夫也死了,父親自由了,不用瞻前顧后偷偷摸摸了。“但是,父親的某些欲望似乎被歲月禁錮住了,只剩下一個愿望了———找一個可以說話的老伴,或者暖暖腳撓癢癢的老伴。”
這么小的愿望,猶如在田隴間邁上土坎想抓拽的一把小草,小草枯萎了,看得見抓不得。二姨娘病得下不了地,不能自理,不想拖累人。
二姨娘讓陳元找舅娘,舅娘也一口回絕了。舅娘忌恨陳元父親的小氣和私心,“找你爹嗎?你曉得他怎么說的?說哪個女人去塔爾坪管吃管住可以,但是你們家的一粒米一根草都是你這個寶貝兒子的,想圖他的家當趁早死心。”父親給陳元存有五六萬的存款呢!陳元送給父親的煙呀酒呀,都被父親拿到小賣部換成錢,存在了信用社。
大火(《后土寺》58—64),執拗的父親拒絕進城。陳元心里墜著老了的父親只身回上海了,終日心神不寧,忐忑不安。父親還是不出所料地出事了,他去山上燒荒開地,一是為了打發日子,二是增加一點收成,引燃了一場山火,燒過了幾架山,差點兒把自己燒死在山上,面臨著要賠錢,被罰款,也有可能被抓起來。
受到驚嚇的父親,像做錯了事的孩子,接到兒子陳元的電話,沒開口就嚶嚶地哭了,哭聲凄慘,身子不停地哆嗦著。等兒子陳元回來前前后后打點,將父親失火燒山的大事化小之后,父親終于吐口,讓陳元帶上自己去上海。
這是《后土寺》第一回《時光》,塔爾坪曾經的“高山流水”“清風明月”“福壽滿門”“祖德流芳”四房院落的時光,守著“清風明月”的父親陳先土的時光。
父親站在初冬的寒風中,像一棵大樹上僅剩下的幾片葉子。
院子,越來越像一只餓死的腹中空空的畜生,透著一絲絲的開始腐爛的氣息。
在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中,農村,特別是大山深處的農村,被城市巨大的吸力掏空了:“這些寂寥落寞的空巢,是我們走進城市前的空巢,是我們無數人內心的歸宿,也是中國現代文明遺落的胎衣和襁褓。在那里,我看到美好的事物正在悄然消逝,人群漸疏,村莊老去,生動而溫情的兒時記憶,在現實的凜冽大風中行將湮滅……一種生活方式正在洶涌而來的都市文明面前迅速衰落、消逝,這些寂寞的村莊也許是中國數千年生活形態的最后一抹痕跡。(攝影師馬卓《空村》)
父:“都搬走了。”
子:“跟我到上海去。”
父:“我頭疼。”
這是作家陳倉分享的短片《父親》里,父與子的一段重復了多次的對話。看著空蕩蕩的村子,空蕩蕩落敗的院子,父親滿臉的委屈和難活:都搬走了……都瞎著(坪掉了)……
空,空有多深邃,疼痛就有多徹骨,多恐懼。把一雙腳如樹根般深深扎在塔爾坪的父親拽起來,帶離塔爾坪,帶往上海,對父親陳先土、兒子陳元是無以言說的痛楚和撕裂。
二、留守兒童的苦痛和對親人的無盡6a1996f7723813f05d7bf2e94c69ce51思念
“爸爸,你現在在哪里呢?……你為什么失蹤了呢?因為那兩個字被抓起來了(陳元告訴過麥子,把‘成立’寫成了‘獨立’,恐怕當不成記者了,要去建筑工地蓋大樓),還是因為忙著蓋那一百層大樓呢?你站在樓頂上能摘到星星了嗎?秋天過了,天已經冷了,你家大丫頭可以不要星星(說到去工地蓋大樓,陳元裝作很高興的樣子問麥子,一百層大樓蓋好后我最想干什么?麥子說爸爸是不是想在上邊住一晚上。陳元說太高了恐怕睡不著,就站在樓頂上摘一顆星星給女兒),但是爸爸,如果你在搬磚的時候,安玻璃的時候,一定要站穩啊。”(《后土寺》66-67)
讀著這樣的文字,淚水在眼眶里酸澀地打轉。
背井離鄉在城市里獨自打拼的陳元,隱忍著艱辛,隱忍著煎熬,隱忍著疲憊,在一次久別勝新婚的春節回家,把自己設計了一遍又一遍:野性大發的狼,瘋狂變態的魔鬼,風月場上的高手。然而,擠了火車,換乘汽車,再倒摩托車,風塵仆仆回到家的時候,他像被填入香料、桂皮和鋸末,泡在福爾馬林中的木乃伊。
隱忍著內心的苦楚,承受著陳世美的罵名,陳元離婚了。原有的夫妻之情化成了前妻的一腔仇恨,不僅不讓女兒見陳元,連接個電話都不允許。女兒稍稍長大了,懂事了,會偷偷想辦法打電話給陳元,而陳元則無法聯系女兒。
那種被動的關系,像生者與死者,死者可以看到生者,但是生者永遠看不到死者。也像脫線的風箏,當他想抓住風箏的時候,發現那根線并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后土寺》 168-169)
父母離婚后的麥子,無辜、無助地在親情裂扯中游離、漂浮著。母親再婚后,把原本帶在身邊的麥子獨自丟在了塔爾坪。一把年紀的父親沒有精力也沒有能力幫陳元照顧女兒,接到上海自己帶又沒有學校能接收。無奈的陳元只好把女兒送到了來往很少的河南盧氏的姐姐家。后來麥子的母親也許想開了,和女兒和好如初,又把麥子接回了丹鳳縣城,新找的男人還天天推著自行車接送麥子上下學。當表姐問陳元,女兒成了別人的,你不會生氣吧?
有人替我養著女兒,我為什么會生氣呢?
一句有些許調侃、自嘲的話語,隱忍的辛酸、苦楚,誰人能解?這是多少在城市里打拼的鄉下人陷入的困境!
《家書》,是陳元的女兒麥子寫給爸爸陳元的信,是留守在家鄉的,父母離異的孩子,對遠在千里之外的父親的無盡思念,想在電話里聽一聽父親聲音都難以觸及。父親陳元不是不掛念女兒,曾經的手機號碼里有女兒的生日1011。在剛剛把女兒托付給河南盧氏表姐的時候,女兒過生日,趕在1011這一天就剩幾分鐘的時間里,陳元把電話打到了學校的隔壁,央求著陌生女人把女兒喊來接電話,問女兒有沒有吃一頓好的,有沒有點蠟燭許愿,電話里還給女兒唱了一首生日歌。
然而,在城市打拼的陳元,境遇脆若薄冰,容不得現實生活的堅硬和牽掛女兒的柔軟。陳元前前后后找了幾個女朋友,給女兒打個電話都得躲起來,后來干脆狠狠心,每次約會時把手機關了。一旦女朋友發現陳元還有個女兒,就消失再也不見了。后來雖然遇到了心地善良的小青,陳元還是沒有底氣告訴小青自己有個女兒,選擇了關機,直至“心安理得”地換掉了包含有女兒生日1011的手機號碼。但是,陳元對女兒的牽掛從未減輕。
在這個世上,陳元真正的親人,除了住在塔爾坪的父親之外,還有一個住在河南盧氏縣鄉下的來往不多的姐姐,和一個寄養在姐姐家的女兒。陳元與這個女兒也聯系不多,時間長了自己都懷疑這是不是自己的血脈。但是他在心里還是十分牽掛著這個女兒,這個女兒也十分牽掛著他。有一年,由于各種各樣的苦衷,陳元突然之間就失蹤了,女兒在絕望的時候給陳元寫下了一封信。(《后土寺》66)
十三歲的女兒,傾訴了對爸爸的日思夜念。學校里,女兒遇到大伯陳元北家的孩子,表哥陳正方。陳正方的父親陳元北在北京離天安門不遠的一家公司當保安。同樣與父親遠隔千里的陳正方,堅持天天在操場上跑圈,一圈一圈地跑。丹鳳縣距離北京有一千三百公里,在操場上跑一圈是四百米,跑十圈是四千米,三百二十五天,就能跑夠一千三百公里,不到一年就能“跑到”北京了!
我們的教室里貼著一張中國地圖,我用尺子量了量,丹鳳縣城至上海接近八十厘米,直線距離是一千公里,曲線距離差不多一千三百公里。我多么想與陳正方一樣,每天圍著操場繞十圈,這樣每年就能見你一次了。但是一個丫頭,一個十三歲的丫頭,我無論怎么努力只能堅持八圈,八圈就八圈吧,每天八圈,三千二百米,這樣算下去的話,我需要四百零六天,才能跑完一千三百公里。(《后土寺》70)
這是兩個孩子想念父親的方式,似深埋在泥土里的一粒種子萌動的思念,是那樣的脆弱和被無視。已是高三學生的陳正方,年級第一名,很有希望考上北大清華。很快就能見到父親的孩子,在一次期中模擬考試,只排到了火箭班的中游,老師一句“跑步能跑進清華北大嗎?就憑這個分數,想上首都北京的大學那等于上天”擊碎了孩子的夢,陳正方爬到樓頂跳樓了。雖然是跳到了消防搭好的氣墊子上,身體無大礙,可孩子的內心有如種子萌發的嫩芽被踩折了。
待在塔爾坪真的不錯嗎?
塔爾坪的一座廟,后來的陳氏祠堂,如今由祠堂改作的小學又被拆掉了,不存在了。送走最后三個孩子的牛校長,在學校關門的最后一天,在教室里的黑板上寫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手里緊緊捏著半根粉筆,像一根木頭一樣被一場大火燒焦了。
故鄉,留給孩子們的是被抽空了的荒涼和絕望。
還有孤獨、無助、恐懼。
十三歲的女兒麥子,“生病了”,身上不停地流血,以為自己要死了,在信里給父親交代了后事:一是自己的遺物,一把木梳子,希望爸爸留下來,掛在胸前,讓它代替自己陪著爸爸。二是給螞蟻的道歉。自己在操場“跑步去上海”的時候,把幾只落單的螞蟻捉起來,帶到教室,想幫它們跑得更遠,卻害怕在教室里爬來爬去的螞蟻被人踩死,從窗戶里丟出去了,擔心丟出去的螞蟻再也回不了家。第三是希望自己生日的時候爸爸能燒幾張紙給自己。
沒有人告訴麥子她是“長大了”。她肚子痛,老師和同學們和她開玩笑說是不是唱歌太用力把腸子唱斷了。她去了一個學校外的小醫院,男大夫說要看她哪里流血時,突然意識到血是從某個秘密部位流出來的,怎么可以讓他看呢?只好撒謊說咳嗽流鼻涕頭暈,讓大夫開點兒感冒藥。大夫給她開了一盒小柴胡沖劑,麥子興奮地發現小柴胡的盒子上寫著“上海涵春堂制藥有限公司”,地址在浦東,麥子想象中的爸爸蓋的一百層的高樓就在浦東,而麥子和爸爸在塔爾坪的山上就挖過柴胡。她感覺自己一包一包喝下去的不是藥,是拌在一起的上海和塔爾坪。
有媽的孩子像個寶,沒媽的孩子像根草。哪個女兒不渴望有媽媽疼呢?在冬天的大風里,“那個人”吵啞著嗓子,壓低著聲音喊女兒,“麥子呀,你看看你褲子后邊,血都滲出來了,你是大姑娘了,你的大姨媽來了你明白嗎?大姨媽每月都會來一次你明白嗎?你這幾天不要喝涼水,不要洗衣服,不要洗頭,晚上一定要蓋好被子。”
麥子心里一熱,向爸爸說了句對不起,向著門縫中“那個人”的眼睛回頭了。
這封撕心裂肺的思念,猶如投入大海的漂流瓶。
麥子,不只是陳元的女兒,她是千千萬留守家鄉的孩子們的縮影,是在荒蕪中頑強、隱忍生長的小草,也可能是自生自滅的小草。
三、父親進城,無法帶離故土
費盡心思與周折,陳元終于帶著父親進城了。第一次進城的父親,可謂“人在礮途”,而陳元的心里是輕快的,“喜”感中流露著成就,帶著父親逛西安的十字大街,上大雁塔,觀博物館,登東方明珠塔……說話的調調都開始頑皮起來。
然而,第一次進城的父親,除了知道兒子在城里,對城里就是一張白紙。他內心里沉著一座山,坦然、實誠、平靜,全然沒有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滑稽和好笑,只有樸素,樸素到我們不知怎么承受。
陳元帶父親登上大雁塔,父親曉得里邊住著唐僧,給觀音菩薩念經,還有孫悟空,給孫悟空念緊箍咒。登上大雁塔,陳元問父親好看嗎?父親說不就是上山嗎?在父親眼里,大雁塔,只是住了虛幻的唐僧、孫悟空,它就是一座塔,遠不如一座山,藥材挖不完,樹木燒不盡的大山。
在陜西歷史博物館,陳元和女朋友小青眼里的展品,是如果賣掉的話,價格是多少?這不是陳元和小青的標準,是城里人的標準。一個中年男人,一臉絡腮胡子,一身唐裝,一副黑邊眼鏡,手上拿著放大鏡,聽到陳元和小青嘻嘻哈哈說一塊西漢皇后的玉印至少值一百萬時,透過鏡片看過來笑咪咪地說,至少八百萬!而一對唐鴛鴦蓮瓣紋金碗,在父親眼里,只是可以拿來盛飯吧?
父親進城,只是在春節期間游玩了幾天,便以頭暈為由,死活也不愿意出門了,只是坐在陽臺上抽煙,看一晃而過的火車。幾天流光溢彩、光怪陸離的時光,在父親看來,只是“給眼睛過生日!”———眼福是飽了,但是相當的虛幻。父親想家了,想塔爾坪了,只有回到塔爾坪,腳下才會有實實在在、踏踏實實的安寧。陳元只好買了火車票,把父親送回去了塔爾坪。
父親第二次進城,是陳元以讓父親來上海給自己提親為理由,把父親“誘騙”進城的。剛一進城,父親按照家鄉塔爾坪風俗做提親準備,平時舍不得吃的掛面、紅糖、西鳳酒、自家養的老母雞下的土雞蛋,只因一粒老鼠屎,被兒子的女朋友小青她媽視作垃圾提下樓扔了。被人嫌棄的父親心里憋屈、不自在。陳元忽悠女友小青,以養寵物的理由,給父親網購回來一頭“小香豬”。然而,上海的豬不是塔爾坪的豬,小青高高興興買回來的豬,不是父親心心念念要養的豬。這一頭與塔爾坪的豬,沒有啥不一樣的畜生,“進城”后弄出一出又一出啼笑皆非的事來。剛進家門,親家不認識豬,只知道是女兒買的寵物,肯定是狗了,肥頭大耳的,起名肥肥;小青眼里,管它是狗還是豬,就是一只寵物,自己姓范,在家里是老大,自己的寵物自然是老二了,起名范二;父親眼里,他就是一頭豬!小青她媽滿心歡喜給女兒的“寵物狗”準備精心熬煮的排骨,后來知道確實是一頭豬后,又把家里弄的亂七八糟、臭氣熏天的,就想一刀砍了它。父親把豬趕到小區花園里溜了溜,與一只發情的獅子狗拱來拱去,晚上獅子狗的主人就找上門了,說陳元家的丑八怪“范二”,非禮了她家的純種獅子狗,擔心她家寶寶懷孕了,要陳元和小青負責任。在學校里評職稱受了氣的小青,回到家把一肚子的怨氣和忿恨撒在了小豬身上,把煮熟的滾燙的囫圇雞蛋硬塞進豬的喉嚨里,看一只小豬如何在自己的擺布下掙扎、嚎叫。
一頭被人帶到城市里的豬,遭受的“禮遇”“折磨”,從鄉下進城的陳元和父親感同身受。城市里沒有豬的容身之地,家里不行,樓道里不行,小區的花園不行,小區保安看在陳元是記者的份上出主意默許陳元和父親在陽臺外面門面房的樓頂上搭了一個棚子,這只被人帶到城市里的豬終于有了臨時的安身之舍。父親也搬到了樓頂,圍著棚子種起了蔬菜,心身也終于些許安定下來,心里樂呵著,隨口還哼起了《天仙配》。
這頭小香豬,看起來與塔爾坪的小豬并無差別的豬,終究不是塔爾坪的豬,在一次眾人圍觀的跳樓事件中,被她的主人一撒手,從主人的懷里摔落了,砸暈了跑過來救人,也是救豬的父親。
小豬,在抱著它的主人的懷里流眼淚了。父親也流眼淚了。閉著眼睛躺在病床上的父親,有一顆淚水順著眼角流了下來。
四、女兒進城,托不住女兒的“夢”
和哄著、“騙”著父親進城不同,女兒想爸爸想“瘋”了,在鞋墊子里攢了不少錢,攢夠了路費,像做夢一樣一下子“飛”到了上海。陳元的心突突地跳著,“漫卷詩書喜若狂”:“見到門口的保安,他在心里對保安說,我女兒來上海了;見到公交車司機,他在心里對公交車司機說,我女兒來上海了;見到幾只麻雀,他在心里對麻雀說,我女兒來上海了。他真想把這個消息告訴每一個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女朋友小青———他不敢告訴的人就是小青,最想告訴的人也是小青。”(《后土寺》172)
然而,父女團聚的喜悅被陳元現實的境遇碰得稀碎。連一輛電動助力車都借不到的陳元,咬咬牙,討價還價后從樓下修車鋪,以50元一天的價格租了一輛別人放在鋪子里修理的雅馬哈,帶著女兒去看大上海。
同樣是父親,城市里的孩子是坐在寶馬車里嚼著牛肉干,而放過牛的女兒只能坐在自己租來的雅馬哈后坐上去豫園看燈會。更尷尬、屈辱的是因違章被警察攔下來,為50元的罰款在女兒面前與警察胡攪蠻纏,僵持中,還是女兒從鞋墊子下拿出僅有的45元,警察墊了5元才湊足罰款。只要能和爸爸在一起,別的都不是事兒的女兒,讓爸爸掉頭回家了,回到出租屋自己扎燈籠。天蒙蒙亮的時候,睡眼蒙朧中的女兒看到爸爸扎的五角星燈籠,興奮地說,多像五角形的太陽。此時的女兒,心中升起的是童年的美好與希望。而父親陳元,看著從地平線徐徐升起來的太陽,是一只一扎就破的紅色的圓形的氣球。如此的脆弱不堪。
帶著女兒去動物園,連一張門票也買不起,陳元讓個頭已過了一米二的女兒半蹲著身子蒙混過檢票口,自己以一張報社印制的臨時采訪證想混充記者證免票,被工作人員攔下后,求助報社主編又不好意思明說而無果。已進了動物園的女兒,看了看不遠處的動物,主動走了出來。近在咫尺的心愿,陳元給不了。只好等天黑了,動物園關門了,保安也下班了,陳元帶著女兒翻過鐵柵欄門,在黑漆漆的園子里,只看到了兩只斑馬和一些動物雕塑。
愧疚無比的父親路過一個超市,給女兒買了一瓶可樂,講了自己也是孩子的時候,因為“餓”,為了能吃上堂弟吃剩下用來喂螞蟻的剩飯,喊了一冬天堂弟爹的屈辱經歷。“偷可樂”硬生生揭開了陳元童年的創傷。他想呵護女兒,不想女兒再經歷自己的過往,看到女兒撿回來的一件布娃娃,盡管女兒洗過了,也讓女兒扔掉。
因為餓!我們是一樣的!這是情感缺失的留守兒童的吶喊。
在《后土寺》第七回《白夜》這一章節里,陳倉描寫了一眾從鄉村來城市討生活的底層打工人的生存場景。賣菜的叫王北瓜,裝修工喚周螺絲,賣豬肉的是張排骨,在小揚州按摩房里做按摩女的是小渭南,房產銷售公司賣房子的小老鄉余發水……在春節一天天挨近的臘月里,正是心急著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的時月,王北瓜、周螺絲、張排骨、小渭南、余發水們卻依舊在城市里的角落里漂泊著、孤獨著。在冷清的月夜里,擠在出租屋里的王北瓜、周螺絲、張排骨,靠幾瓶啤酒調侃著家里、家外的女人,消遣著自己的寂寞;在燈紅酒綠,人來人往中倍感孤單的小渭南,有家回不去,也不想回家,尋到出租屋來找陳元……這是他們在大城市里如馬路邊石頭縫里的小草般艱難生存,白天被漠視,夜晚被遺忘后的取暖方式。
經歷了外甥余發水在網上看了幾張美女照片后的夜里稀里糊涂錯進了厚嘴唇女人的房間的新聞事件;女兒只在小渭南的按摩房暫住了一晚,僅僅隔了一天一夜,麥子已不是原來的麥子了,涂上了紫色的口紅,裝上了長長的假睫毛,畫上了濃濃的眼影,涂上了銀色的指甲油,馬尾辮也不見了,頭發松松散散地披在肩頭;幼兒園的一個五十多歲的保安,以騎木馬的誘惑猥褻了賣菜攤主的女兒。
沖動、氣憤、絕望,五味雜陳的父親陳元,拉著女兒回家了。臘月二十二女兒離家出走,二十三才到上海找到父親的女兒,在上海僅僅住了兩個晚上。原本還在猶猶豫豫回不回家的陳元,臘月二十五一大早,帶著女兒坐上了回家的班車。
五、父親生命的終點———兒子向上生長的起點
陳元終于又把父親帶到了上海。在父親患了肝癌,半昏迷中,悄悄把父親拉到上海住進了光明醫院。這一章節里(《后土寺》第八回《家書—回光》),是父親第三次進城,也是最后一次進城,彌留之際的父親第一次沒有吵著回家,主動提出要看看東方明珠,看看兒子工作的報社。陳元背著行將遠去的父親,自己也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進城。
帶父親進城,盡管當時的陳元工作不順,手頭緊巴巴的,但是在女朋友小青的資助下,內心還是很有優越感的,想著法子讓一輩子沒出過大山的父親進城見大世面,享受大城市的文明,過幸福的晚年生活。然而,對父親而言,有如“小豬進城”般難活。
女兒進城,則是對身為父親的陳元自信和尊嚴的重擊,飽受了城市文明的堅硬、冷漠,獨自吞咽著底層生活的辛酸、屈辱、無助。
三代人的“進城”,是扭曲的一幕悲喜劇。
在父親走向生命的盡頭,冥冥之中將生活的態度,做人的自信、尊嚴、善良注入到兒子陳元的心地。父親與這座城市的關系,似乎一下子正常多了。陳元與這座城市的關系,也正常多了。
去東方明珠,陳元沒有再找蔡經理走特殊通道,而是讓女朋友小青買了三張票,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正式走過了檢票口。父親在走進檢票口的時候嘟噥著說,“這樣挺好的!”
“無論有多少次登上東方明珠的理由,卻是第一次花錢給自己買票,給小青和你爹買票,這種感覺是十分奇妙的,起碼發現自己是有尊嚴的。(《后土寺》369)
帶第一次來上海的女兒去動物園,憑一張報社的臨時采訪證想蒙混過關被揭穿后,遭來了眾人尖酸、刻薄的嘲諷。
這一次帶著父親在東方明珠,看著顫顫巍巍的老人正常排隊,排在前面的、后面的紛紛謙讓起來,工作人員也上來表達關切。
幾年前的一個晚上,帶女兒看自己工作單位,因沒帶身份證,被“肥嘟嘟”“瘦溜溜”兩個上海本地保安“為難”。千說百說也沒能讓陳元和女兒上樓的兩個保安,這次不再冷臉、生硬,看父親身體不好,讓陳元和父親趕緊上樓,還主動沖在前面,幫著按好了電梯。
冷漠的報社主編賈懷章給予了陳元意想不到的熱情,打電話叫來攝影記者給父親和陳元咔嚓咔嚓拍了好多照片,還把自己的車子借給了陳元。
路上車子爆胎了,又遇到了曾經當著女兒的面“刁難”自己的交警“浦東”。這次“浦東”沒有再“刁難”陳元,義務為陳元換好了備胎,婉拒了陳元200元的感謝費。
陳元要背父親去自己的辦公室,父親說,從下邊看看就行了,上去人家會笑話的,笑話陳元有個土農民的爹。
放在原來的話,雖然我以自己有一個農民父親感到欣慰,如果真要把父親帶到同事面前那是需要勇氣的,我不僅僅害怕人家笑話白紙一樣無知的父親,還擔心人家發現我一直隱瞞著的出身。但是現在,我生氣地蹲了下來。(《后土寺》375)
帶著父親參觀自己將要入住的小區,看到樓下的草坪里,有幾棵碗口粗的樹,樹根用繩子包扎著。這些是在外地培育好的樹,然后連根一起被拉到上海,準備移栽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陳元說它們的境遇與自己一模一樣。
父親陳先土生命的終點,是兒子陳元向上生長的起點。父親是樹根,也是緊抱著樹根的草繩,終將化作泥土,與新的泥土融為一體,托舉著兒子向上生長。
陳元真正意義上進城了,“我原來與一道疤(出租車司機)一樣,總覺得這個社會是不可理喻的,但是不明白為什么自己的看法突然改變了。我不是用寬容的方法安慰你嗲,更不是想給他一個美好的假象,而是把人世的一切放在他這個走向終點的坐標系中,發現了原本一直存在的美,有的是無奈的美,有的是反差的美,有的是冷靜的美,有的是火熱的美,有的是高貴的美,有的是樸素的美,只不過因為自卑的原因,被我一再地曲解了。”(《后土寺》374)
陳先土,在大山里種了一輩子地的農民父親,彌留之際伸出手在地上抓了抓,在空中抓了抓,在兒子陳元的腿上敲了敲。兒子問他,你在干什么呢?他說,我在拔草呀,地里的草都長上來了;我在摘扁豆,晚上煮扁豆吃怎么樣?我在破柴火,馬上要過冬了,得準備一些柴火放在那里。
父親,樸素的生活執念,是托起陳元的精神支柱。
回到塔爾坪,在小學的廢墟上新修的寺廟里,陳元從肩膀上放下包著父親陳先土骨灰的包袱,端端正正地放在香堂里的香案上,在自家門板做成的牌匾上嚴肅認真地寫下三個大字———后土寺。
這一天,二O一七年,農歷五月初二,公歷五月二十七日,是作家陳倉父親八十歲生日。陳倉寫好了《后土寺》最后一句話———看了看那個擺在香案上的黑色的包袱,又抬頭看了看被夕陽鍍成了金色的那塊牌匾。陳元朝著地面全身心地伏了下去。
陳倉淚流滿面。
【作者簡介】張學明,曾用筆名寒軒,有詩歌、小說、評論、散文等作品發表于《詩刊》《山花》《山西文學》《都市》等文學期刊。
責任編輯:曹桐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