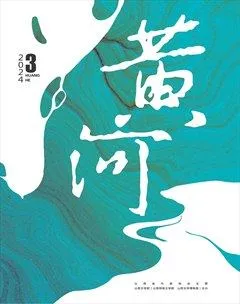重逢,即是永別
你拗,我更“皮”
《東坡志林》常常拿王安石來開玩笑。書里引述,王安石某次和劉原父一起痛飲,忽然停箸,問劉原父:“孔子‘不撤姜食’是什么意思?”原父一本正經答道:“根據《本草》,生姜多吃會損智。因此老子說,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是老子的學生,是以道教人的,所以提倡‘不撤姜食’,讓天下人都當笨蛋。”
王安石得到悟解,十分高興,后來才知道,劉原父的話原來竟是跟他開玩笑的。蘇東坡因而論王安石“多思而喜(穿)鑿。”劉原父是按照他的思想方法來作解說的。《東坡志林》記這一個故事之后,接著說:“庚辰三月十一日,食姜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姜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以為后世君子一笑。”由此可見,“姜粥”也是“堅硬的稀粥”。
王安石為人正直而刻板,有時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他的學問水平堪稱一代大家。對于學識,他是頗為自負的。當時朝廷中人,都暗中稱他是“拗相公”。
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三月開始,他在兒子等人幫助下動筆撰寫《三經新義》(王安石撰《周官新義》,王蚞、呂惠卿撰《毛詩義》《尚書義》的合稱,是熙寧變法的重要理論依據),經過兩年左右才告完成,他自認為是古代經書的權威評論家,基本否定了鄭玄、馬融等大儒的相關研究。他還利用行政管理的權力立下標準,國內讀書人都必須研讀他的“新義”,連科舉生答卷也要以“新義”為準。一些大學問家歐陽修、司馬光、蘇軾兄弟等對此頗有看法。蘇軾出京之后,有一次監考鄉試,曾寫詩表達了他對考生試卷表現出來思想呆板、學識貧乏的深切擔憂。
學者們不僅對拗相公的《三經新義》報以反對態度,對于他研究文字的著述《字說》也頗有看法,認為他研究中國文字的構造和起源,不做探究,不用比較,頗多主觀臆造。有人曾諷刺它是“幻想語言學”,一個人半天就可造出許多篇章。
備受人指責的《字說》,現在已散失了大半,唯有殘留下來的只言片語,可以推想原書情況,這成為歷代文人茶余飯后的趣談。而蘇東坡和王安石的許多交際,都與《字說》有關。
蘇軾是名列全國第二的高中進士。早在16年前,王安石是第四名,蘇軾風頭比王安石更勁。兩人的第一份工作均是簽判;彼此的詩歌、文章都出彩,可謂勢均力敵。
明朝王昀貞編纂的《調謔編》就記載了幾個故事:
東坡聞荊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意思是說,王安石把“篤”“笑”等當作“會意字”,荒唐地加以發揮。這怎能不被人譏笑呢?
文字中有“鳩”字,由“九”和“鳥”兩部分構成,讀音是“糾”。這本來是形聲字,左為聲,右為形。拗相公卻一心想由字義找到出乎預料的新意,他一意孤行,竟然發展到推翻字音的程度。
有一天,蘇軾與王安石閑聊。蘇軾故意請教王安石:“說說看,‘鳩’字為什么由‘九’和‘鳥’兩字所構成?”
因為不明東坡的就里,王安石一時語塞。
東坡笑起來,揭開了謎底:“我認為這一證據是《詩經》里說的:‘鸕鳩在桑,其子七兮。’意思是七只小鳥兒,再加上它們的父母,不就是九只了嗎?”
王安石恍然大悟,蘇東坡不是在討論學問,而是在借此諷刺自己。
不料,沒過幾天蘇軾又來“發難”了,這一次是涉及“波”字。
“波”也是形聲字,是由“水”和象聲的“皮”字所構成。王安石解釋時,想象力太過豐富,在《字說》中竟解釋為“波為水之皮”,這明顯是詩人的思維。但如果牽強附會地理解,也還說得過去。
如果這一解釋合理,蘇東坡的“坡”,是不是“土地之皮”呢?蘇軾一想到此就大笑不止。千年之后的當代作家賈平凹順勢道出了蘇東坡這一重要品質:“蘇東坡,太‘皮’了!”因為“人可以無知,但不可以無趣”。
蘇軾遇到剛剛退朝的王安石,“波”字讓他忍俊不禁,詼諧地說:“照先生書里的解釋,既然‘波’為水的皮膚,那么‘滑’字一定是說水有骨頭!”
王安石表情尷尬,一時僵在了路上。
可見,王安石的《字說》違反文字的造字規律,不少地方出于主觀臆斷,遭到人們的質疑和非議實屬難免。何況,他遇到的是蘇東坡這樣的才思敏捷之人!
蘇東坡在為反對新法所作的詩歌中,往往或明或暗地攻擊王安石本人,他不但反感王安石的“新政”,而且對王安石的學識也看不上眼,說“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又說王氏之學為“俗學”,而王安石的“經說”和“字說”,問題的確太多。
公允地說,王安石對蘇東坡當然也不無成見,但他年長一些,在為人處世上表現了長者的沉穩與大度。不僅如此,王安石后來還逐漸改變了對于蘇軾的看法,他特別欽佩東坡的文學天才,特別是在讀了東坡獨抒性靈的詩作后,他發自內心稱贊:“子瞻,人中龍也!”
才智機敏的東坡,也并不可能永遠正確。一天蘇東坡登門拜訪王安石。王安石不在,管家便把他引到主人的書房里用茶。蘇軾在書房里一邊品茶,一邊欣賞主人書房懸掛的字畫。
目光一轉,他注意到王安石書案上有一首尚未寫完的《詠菊》詩。其中二句是:“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蘇軾看罷,諧謔的天性發作,哈哈大笑。他認為:春蘭秋菊,菊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素有傲雪之骨,不管風吹雨打菊花只會枯干,不會飄落。眉山蘇家庭院里的菊花就是如此,沒想到當朝宰相王安石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
他略加沉吟,提筆在王安石的詩句下加了二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續完詩句之后,回過神來的蘇軾,知道自己又禍從口出,這樣豈不是冒犯了“拗相公”的臉面?白紙黑字,已經不能再在紙上涂抹或銷毀證據了。于是,他向管家匆匆告辭而去。
王安石回家,管家說:“蘇軾來過,等了您一會兒,就走了。”
王安石見到書房的書案上的續詩,知道定是蘇軾所為。他不禁暗笑起來:“蘇軾呀,枉你過目成誦、出口成章,《離騷》你不是背得很熟嗎?那里邊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詩句,難道你這名震京師、帝王視為棟梁之材的大學者,連這都不曉得嗎?”
東坡來到黃州后,公務之余,經常與友人一起吟詩消遣。一天正值九九重陽節,他約請已是隱士的陳季常來家里飲酒賞菊。當他與陳季常來到花園時,一向見花就喜形于色的東坡,突然沉默了。原來,昨天還是怒放的菊花,經過一夜風雨之后,現在只剩下一些光禿禿的枝干在風中微微搖曳,枯菊稈下鋪滿了金黃色的菊瓣……真是秋風秋雨愁煞人,寒宵獨坐心如搗。
陳季常很少見到東坡這副沉默木然之樣,忙問緣由。東坡禁不住深深嘆了一口氣,便把給王安石詠菊續詩等往事細說了一遍。
陳季常也是飽讀詩書,提出了自己的觀察:“橘子生長在淮河以南就稱為橘,生長于淮河以北就稱為枳。菊花一般不落瓣,但黃州這里的季候有些特別,菊花是落瓣的。可見凡事都有它的特殊性。你曾經提到,蜀地眉州還有香海棠,但是黃州這里的海棠就沒有任何氣味啊……”
東坡霍然大悟,他有些不好意思了,羞慚滿面地對陳季常說:“看來拗相公所寫的‘吹落黃花滿地金’一句沒錯啊,倒是我寫的‘秋花不比春花落’錯了!這才是地地道道的狗尾續貂……”
幾年之后,東坡被重新起用應召回京時,他曾專門為續詩一事,登門向王安石認錯。
對于“新法”,東坡不止一次向神宗上奏:先是上《議學校貢舉狀》,反對王安石的科舉改革;后來王安石準備低價購買浙江出產的四千盞燈供宮中使用,東坡又上《諫買浙燈狀》予以阻止。神宗皇帝認為蘇軾說得對,沒有采納王安石的意見。熙寧四年(1071年)東坡挺身而出,為民請命,又上三千多字的《上神宗皇帝書》,直言上諫,到了“非吐不可”的時候了,質疑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可行性。
變法派惱羞成怒,將蘇東坡視為保守派的干將,想方設法排擠打壓。御史謝景溫把妹妹嫁給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他自然要收拾一下蘇東坡。他上奏說,蘇軾回蜀“丁憂”時,用官船販賣貨物,并且大售私鹽;“丁憂”期滿回京時,又私下調用兵士。官員參與販賣私鹽,這還了得!
東坡認為:謝景溫為改革派成員,又與王安石弟弟王安禮是姻親,謝景溫如此誣告自己,自然是出于他們的授意了。事實上,在王安石得到這一稟報后,“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十三,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5175頁。)
需要注意,喜怒從來不形于色的王安石,“大喜”二字的分量。
面對朝廷的嚴厲質詢,東坡回復:“蘇某奉公守法,絕無販賣私鹽之事,也絕沒有私下調度兵士。”
朝廷為此逮捕了當年船上的船工、水師等人,嚴加審訊,東坡中途曾經與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相遇,新黨中人希望李師中出面做偽證,遭到李師中嚴詞拒絕。朝廷才知道,東坡販賣私鹽之事純屬無中生有:那是蘇軾返京之際,恰逢眉州兵士去汴京迎接新任的知州大人,于是順道將東坡一行送還京城,其實東坡還為公家節約了一筆路費,顯然不屬于私下調兵。
案情已查清,但東坡徹底心灰意冷了。誰人不知這是陷害啊,他不想在汴京這個漩渦里弄得昏天黑地。
前途陰晴無主,風雪難料。天地之間擁塞著不可名狀的痛苦。春季的靜默中,唯有細雪斜斜飄成一種牽掛。但也許是了無牽掛。
風雪是不會收起成命的。遼闊的路途上,枝丫間的春意,把遠方拉到了眼底。
那就走吧。《詩·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東坡啊,你真走得了嗎?
兩個“古之君子”
蘇東坡與王安石兩人在從政方面雖處于對立面,而且自始至終誰也沒有說服對方,從未“一笑泯恩仇”。但從文學創作上講,尤其是變法初期的情況已成為往事之后,他們又是真正的同路人,畢竟都是歐陽修古文復興運動中的杰出人物。在歐陽修逝世后,蘇東坡、王安石在當時文壇上威望最高,時代賦予了他們很多期望。在文學上的這種關系,促使他們更加重視和珍惜彼此的友誼,甚至是面子。因為擁有友誼,并不一定要出于知音。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的愛子王蚞離世,才33歲啊!這轟然一擊,讓王安石陷入了無邊的悲痛。他的病也加劇了,神情恍惚,多次托病請求離職。
元豐七年(1084年)春,王安石舊病復發,某天突然昏迷,兩天滴水未進。也許暴病就是一場啟示錄,待病情好轉,他思前顧后,認為自己佛禪修行遠不到家,應該在有生之年廣結善緣。就在這年冬天,妻子吳氏也撒手人寰,這又是一次沉重打擊。吳夫人20歲與王安石成親,42年倏忽而過,她一直以賢妻良母的形象出現在家族眾人面前,廣受贊美與敬重。于是,王安石散財超度,捐給太平興國寺大量熟田、旱地之后,懇請朝廷將江寧府上元縣的“半山園”改為寺院。神宗皇帝立即降旨照準,并御筆題寫了“報寧禪寺”。王安石在江寧秦淮河畔租賃了一所普通宅院,于四月從鐘山搬家,在這所小院里度過了他的最后時光。
此時的王安石,已經悟入禪宗甚深。他不再是政治家,不再是大哲,甚至不單單是一個文士。他“以物觀物”,臻于物象與心靈的整合成一、融為一體,全然是自然天成的審美之境,他的詩歌創作,也全然由古體詩轉向了絕句。北宋詩人張舜民在《賓退錄》卷二里,稱贊王安石晚年詩作:“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評價極高。連黃庭堅也由衷承認:“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足見王安石晚年之作,已然抵達唐詩那種直接用形象呈現意象的詩歌勝境!
王安石坦承:“未能達本且歸根,真照無知豈待言。枯木巖前猶失路,那堪春入武陵原。”
神宗還賜給王安石一匹御馬。不料御馬很快病死了,他就買了一頭毛驢代步。那是王安石從“半山園”遷回江寧幾月之后,炎炎七月的一天,他騎毛驢到鄉野漫游,借此散心,不知不覺來到長江碼頭,江邊密密麻麻停泊著大大小小的商貨船只,舟帆林立,好不熱鬧。他把驢子交給雞毛小店拴好,在岸邊踱步。
忽然一個熟人走上前來,指著江中的一艘商船稟告:“荊公,那是蘇軾乘坐的船。”
王安石又喜又驚,立即讓仆人帶他上船。
王安石來得太過突然,蘇東坡連帽子也來不及戴好,就急忙出艙相迎。
“子瞻,此次來金陵有何公干?”王安石的語氣不徐不疾。
“學生奉圣諭從黃州‘量移’常州,路過金陵,正欲造府拜訪您,不期在此相遇。倉卒之間穿著便服參見先生,請恕失禮之罪。”蘇東坡向王安石深深一揖。
“量移”是唐、宋公文用語。官員被貶謫遠方后,遇恩赦遷距京城較近的地區。泛指遷職。
王安石笑著說:“子瞻何必客氣!禮,難道是為我輩而設嗎?哈哈哈!”
王安石的坦然之態,讓蘇東坡又恢復了活潑的常態。他們在船艙簡單交談了一陣,約定次日在王安石寓所品茶敘舊。
翌日一早,蘇東坡就來到王安石的便宅,王安石早在客廳等候。他們品啜香茗,話題自然要回到那些人生世事里難以解開的“結”。
看到白發蕭然、舉止遲緩的王安石,蘇東坡滿懷深情回憶往事:“荊公還記得否?熙寧三年朝廷拜先生為相的圣諭下達當日,百官登門道賀不已,而先生因為來不及向朝廷進獻謝表,所以都讓下人婉言拒絕了百官,沒有出來接見。當時我和你恰好坐在西面的小閣里,耳聞外面的陣陣喧鬧,你皺著眉頭,許久未說話。忽然間你起身提筆,書寫了‘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兩行詩。想不到先生15年前的愿望,今日終于實現了……”
王安石笑道:“真的有這回事嗎?往事如白駒過隙,加之我身弱多病,已經忘記了。我病愈之后,倒是有些工夫來琢磨這些往事了。”他看著東坡,接著說:“子瞻,過去的種種經歷,真有如經歷一場大夢。‘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當年你在朝中,毫不隱諱地指出皇上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大銳,那時我在旁聽了也很不舒服啊。現在回想起來,你的話還真有一定道理!”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說多年來東坡一直就在等待這個解釋的機會,他道:“以前我對新法的確有較大的抵觸情緒。貶謫黃州這幾年來,接觸很多普通百姓,了解到不少下面的真實情況,知道‘免役’‘農田水利’等措施,對于減輕農民負擔,保證農作物豐收,確實起到了作用。”
王安石本來不欲多談政事,但受到感染,頗有感觸地說:“子瞻,你這次‘量移’,只不過改換了地方。其實啊,你是做翰林學士的人才,眼下真有些屈才了……”
東坡生性詼諧,他對王安石說:“荊公,讓我講一個您家鄉臨川的故事吧。誰都知道臨川的牛皮鼓名聲在外,揚州一富商子弟表示愿出高價購買。有一位臨川人得到這一訊息,千里迢迢將牛皮鼓運到揚州。那位富商子弟當場敲鼓,誰知半點響聲也沒有。富商大失所望,買鼓的事情自然就告吹了。臨川人帶著皮鼓垂頭喪氣回鄉,越想越氣,在過河時,一揮手就把鼓扔進了水中,想不到鼓卻在水面發出撲通、撲通的響聲。臨川人站在岸上,望著河水,深深嘆氣:你(指鼓)早出聲,我也不會落到這個地步啊……”
王安石閱人無數,自然聽得出,蘇東坡借這個“鼓”,裝進了他的很多心事。東坡的用意是,暗怪王安石當政時沒有替他說話,也沒有予以重用。可見,東坡還有不平之氣,壅塞于心。
王安石寬厚地微笑,沒有辯解。再說什么,均顯得多余了。
事實上,王安石不但幫過蘇東坡,而且是強有力地扭轉了頹勢。元豐二年(1079年),御史臺長官舒、李定彈劾蘇軾利用詩歌諷刺“新法”、反對皇帝,造成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頃刻之間,蘇軾就由堂堂湖州太守變為御史臺監獄的重囚。當時朝廷內外,上自曹太皇太后,下至張方平、范鎮、王安禮等重臣要員,都紛紛伸手搭救,甚至連變法派中的章也在神宗面前為蘇軾說好話。王安石在鐘山聽到這一消息,非常焦急,連夜給皇帝上書,用驛馬快遞送到京城。書中誠懇地規勸神宗說:蘇軾是位舉世聞名的才子,哪里有圣明之世卻發生妄殺才士的行為呢?神宗看到,連“對頭”王安石都出來為蘇軾說情了,加上自己本來就愛惜蘇軾之才,也不忍心把他置之死地,于是順水推舟,從輕發落。
王安石上書營救蘇軾這一義舉,當時不為人所知,所以蘇東坡一直不知道事情的原委。
他們在書房內談論了不少老朋友的近況,見王安石有些疲倦,東坡建議一塊出去透透氣。王安石站起身來,扶著拐杖,來到后院的小花園。時當夏季,園內竹木茂盛,枝葉繁茂,兩人受到感染,平息下來,話題又回到了彼此心儀的詩歌。
幾天之后,東坡在江寧知府王益柔(勝之)陪同下,游歷了鐘山。他們在已經改為報寧禪寺的王安石舊居“半山園”里細細探尋。那里還有王安石居住過的“昭文齋”,酴骾金沙二花雖然花期已過,但綠葉婆娑,綠意盎然。還有老友米芾題寫的匾額,還懸掛著大畫家李公麟為王安石繪制的肖像……揣摩此時蘇東坡的心際變化,想來大有一番況味。
蘇東坡倚馬可待完成了一批近作,立即送王安石指教。
接到蘇東坡詩稿,王安石詳讀《次荊公韻四絕》,其中第三首是這樣的:
騎驢渺渺入荒坡,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王安石知道,蘇東坡這首詩,是步其《北山》一詩之韻而作。蘇詩中所描述的他們相聚的情景與種種感受,使他徹底認識到東坡心胸坦蕩與真誠,已不易動情的他,也是頗為感慨。蘇東坡還有一首題為《同勝之游蔣山》的五古詩,以細致的筆觸描寫自己暢游鐘山(又名蔣山、北山)的經過。當王安石讀到“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時,不禁拍案感嘆道:“像蘇子瞻這樣的人,今后幾百年內還會再出現嗎?”
“和詩”,表達的是文人間的敬重。他立即和詩一首,并在詩前用小序說明作詩的動機:“余愛其‘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之句,因次其韻。”詩的結尾以“墨客真能賦,留詩野竹娟”的評語,再一次表示對東坡才華的贊賞。從一開始的道不同不相為謀,實緣于君子和而不同,大概是這次歷史性相會的最佳注解。
在一來一回的詩章里,“從公已覺十年遲”,展示了東坡金陵之行重新了解王安石后得出的結論;而“似子瞻之才,日后能否再有”,無疑是王安石與東坡接觸以及詩文唱酬后得出的新發現,一改他氣盛的當年,對當初寂寂無聞的“三蘇”的不屑。
兩位政見不同、棱角分明的才子,在以往波詭云譎的權力爭斗中所產生的系列齟齬與嫌怨,可謂是“渡盡劫波兄弟在”,雖然未必“相逢一笑泯恩仇”。
兩人以為,就此別過了,人生還會相逢。
蘇東坡離開江寧抵達儀真(今江蘇省儀征市),接連給王安石送去兩封短信。第一封信說:“某游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這是繼他“從公已覺十年遲”體認之后,又一真情實感的流露。第二封信里談到,他本來要遵從王安石的勸告,在金陵買田置宅,侍陪荊公養老鐘山,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如愿以償。現在只好在宜興、常州一帶物色田園。如果買地成功了,將來扁舟往來甚是便利,兩人見面也就不是什么難事了。
信里,蘇東坡還向王安石推薦秦觀,說他不僅“行義修傷,才敏過人,有志于忠義”,而且“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并附上秦觀數十篇詩文,請王安石審閱評議。王安石接到信后,不久就給蘇軾作了回復,信中對秦觀詩文大加稱贊,說“得秦君詩,手不能舍”,認為其作“清新嫵媚”,足可以與鮑照、謝靈運的詩作相頡頏。這足以說明,對于他們那樣的品行高潔之人來說,他們之間從未有過私人的恩怨情仇,只有從政和民生方面的分歧。而且在獎掖后學、愛惜人才方面,他們的觀點又完全一致。
聯想起蘇東坡在《上韓太尉書》里描述了他對古代君子的懷念和崇敬,他還將君子分為“古之君子”“后之君子”與“后世君子”三種類型,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君子是“古之君子”,他們是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典型代表:“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如此看來,他認可王安石,乃是“古之君子”。
重逢,就是永別
一塊出自靈念的毛坯,一當置身鐵錘之下,鍛造與純化是一個高手必經的工序。
一種情況是將其鍛打成了利器;另外一種情況是被錘為了一堆爛渣;還有一種人,則妙手將自己吹打成了一張薄片,就像民間傳說的那樣,一兩黃金打出的金箔能蓋一畝三分地。可惜他們鍛打的不是黃金,而是延展性不好的鐵,于是,就干脆把自己卷成了喇叭———這基本上就是封建知識分子的本職工作。他們都不是這樣的人。
“恨別鳥驚心”的余緒是,東坡從芙蓉花大面積跌落的風雨空隙里,看見亂飛的鳥兒,再一次,像菊花那樣飛起,站在了芙蓉的枝頭。
凝露為霜,霜如銀。在晨光下變成了一滴一滴的時光殘液,從容自瓦楞落下。夜露滴落的聲音,將鳥鳴濺濕,鳥鳴翠綠而蓬松,如山野的萬竿修篁,如西王母的發飾。我們方知道,夜露流過的方式與姿勢,與雨完全不同。
他們也沒有意識到,他們的重逢,就是永別。
在長江熱氣升騰的浩大水面,白蠟蠟的天光從烏篷船頂擠進來江風,就像劍穗一樣飄拂,就像毛筆的枯筆一樣在紙上澀滯,它們在用一種回光返照的方式暗示:不是再見,而是永訣。
誰也不知道,兩年后的公元1086年,王安石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六歲。
誰也不知道,還有舉在頭頂的驚濤駭浪,在等著蘇東坡。
【作者簡介】蔣藍,詩人,思想隨筆作家,田野考察者。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委員,四川省作協副主席,四川大學文新學院特聘導師,四川文理學院客座教授,已出版《蘇東坡辭典》《成都傳》《蜀人記》等。
責任編輯: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