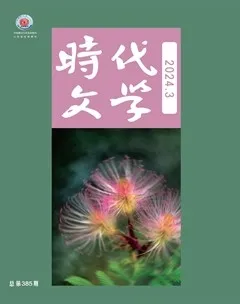如果故事有另一個結尾
小說寫完,我拿給我爸看,他和我媽永遠是我的第一讀者,他看后說一切都很好,這個故事獨特,如果不是親身經歷過,是編造不出來的。然而大概隔了兩年的時間,他又問起來這篇小說,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他說有點接受不了后半部分,最好改了。
在做菜的間隙,他在抽油煙機的混雜噪音下,突然問起來,我說怎么了,他遲疑了半天,顯然在做著最后的斟酌,然后關了抽油煙機,廚房瞬間安靜,頓一頓,他問我:“能不能不殺那只羊?”
海馬體是人大腦里神秘而古老的區域,海馬在神話里是波塞冬的坐騎,鼻息能吹動大海,金黃色的雙蹄能跨越黑暗之淵。《山頂上的雪》就是這樣一個藏在海馬體里的故事。
我沒有見過我爺爺,每次提起他,我爸都加上這樣一句:如果你爺爺還活著,他一定最疼你,因為你是他第一個孫女,是家里第一個女孩。因此,我自小就有一份額外的憑空虛設的愛,那是我假想出來的爺爺對我的寵愛,因為是假想出來的,是一種代償之愛,所以不著邊際也用之不竭。小時候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和老年男性對話,因為我從他們身上看見的不是或蒼老或矍鑠,而是一份我假象出的親緣,故而不知道在他們面前我應有的姿態,在疏離中總有意無意帶著一點討要關愛的本能。
我明白事理之后,我爸才告訴我,爺爺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年輕時死于一場事故。他是鄉村醫生,給人看病也給動物看病,中年時調到外村上班,十天半個月才回趟家,平時都住在單位宿舍,有天夜里一氧化碳中毒去世。那天和他一起的還有另一個人,那人是縣里的,去他們單位下通知,因為地方偏,人又少,和我爺爺又是舊識,便歇在他們單位,兩個人都沒了。肉體之死背后又多了許多其他的疑問:那家人住在哪兒?那家人后來有沒有來過?兩家人有沒有見過面?如果那家的人找來,會說些什么?如果他們找來,我們又會說些什么?都沒有,沒有下文,沒有人找過。我對這個事實感到失望,因為二十多年來每次想到爺爺,那個我甚至不知道姓名的人也會隱隱浮現,于是便有了這篇小說。
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從卡拉拉山開采出一塊大理石,請匠人雕琢一座大衛像作為城市的象征,后來請來了米開朗琪羅。在被問到要如何用這塊大理石雕刻出大衛時,米開朗琪羅說出了那句打動人的話:大衛其實已經在里面,我只要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就好了。這篇小說的寫作不同于以往其他的寫作,這篇小說的故事是現成的,它已經在那里了,我只要講明白、講好就行。也正因此,我格外珍視這篇小說。
小說里,昆寶娘倆來了,昆寶是第一次來,母親打算燉一鍋羊肉招待他們,也算是一種逞能,一種孤兒寡母應付生活游刃有余的示威,一種對于沉默拷問的孤膽對抗,甚或是一個血淋淋的逐客令,于是祭奠了一只羊出來。我覺得應該以死亡對抗死亡,羊被殺了,但肉難以下咽,幾個人圍坐著開始自然而然地談論起兩個父親。對于這樣的情節安排,我自認為是羅曼·羅蘭所謂的英雄主義,不憚于與丑陋為伍,所以沒有做大的改動,更沒有聽從爸爸的意思,因為我本能地抗拒溫情的結尾,覺得那是一種美化,模糊且平庸,我甚至會認為那是一種高調的謊言,一種卑微的逃避。
然而人歸根結底是趨善的,這是進化留下來的一種本能,“不忍”這個詞可以被解讀為“軟弱”,也可以被解讀為“慈悲”,我逐漸理解為什么爸爸要改掉結尾,因為他對于那樣的結尾是不忍的。
雖然沒有付諸行動,但我的大腦自動校正了這個家族故事,它或許還可以有另一個結局。顯然爸爸想了很久,兩年的時間,我懷疑他多次欲言又止,所以在說出口的時候,這個故事被接續了一個已然成熟的結尾,他語調緩慢,克制,憂傷,像是說起歷史本來的面目:
我跟昆寶講這只羊的來歷,講它小時候的孱弱與潔白;講它甚至有個名字,叫白河;講它愛吃咸味的草,鐘愛山坡;講它耳朵上的豁口,眼睛是淡紅色……我如泄露天機一般吐露出關于這只羊的一切秘密,然后把它領到昆寶面前,把拴它的繩子塞到昆寶汗津津的手掌里,一個儀式結束了,一場回溯開始了。而回溯,遠比一場殺戮更回腸蕩氣。
昆寶母子牽著羊走了,從此再也沒有來過。
一只活著的羊比一只死去的羊更有人情味,它是歉意,是陪伴,是一種呈現退讓姿態的擁抱,良善溫和含蓄,不含咄咄逼人的殺氣,它由爸爸手中到了我手中又到了昆寶母子手中,被帶走,被好好圈養,何嘗不是另一種代償之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