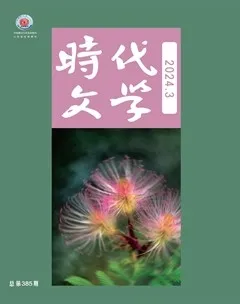我的年
我總以為,過年是因為一生太長了,長到看不見盡頭,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于是就用年把日子截斷。就像用鐮刀割麥子,毒日頭底下,彎腰埋頭割了半晌,抬頭看看還不見邊際,渾身的勁立馬就泄了,鐮刀揮起來有千斤重。要是地塊小,一彎腰一抬頭,就要割完了,渾身的勁像風吹過來,立馬膨脹了,輕快歡悅地割完一塊又一塊地。
過年又是因為人生太短了,從呱呱墜地到垂垂暮年,短到一眼就看見頭,直白得沒有一點風景。人們就用年把日子截斷,像園林里的隔斷,“有墻壁隔著,有廊子界著,層次多了,景致就見得深了”。一年一年摞起來,人生仿佛就豐富了。
依了生命的長度,切割出數量不等的年。年年歲歲有相似,歲歲年年又不同,成其為每個人的一生。
我回望自己大半生被年切割過的日子。
小時候跟著父母在農村過的年,大都是物資匱乏的年代。
我父母的意思是孩子跟著他們一年到頭沒享什么福,苦倒是吃了不少,過年了,就竭盡所能讓孩子們高興。年三十上午,不論買幾斤肉,母親總是用十三印的大鍋燒火煮肉,騰騰熱氣和肉香從做飯的小棚子里鉆出來,氤氳著,彌漫著,把家里家外的空氣熏成年三十才有的味道。父親拿個大盆盛肉和肉骨頭,把大盆裝得滿滿當當,快步往屋里走去。早等得心急火燎的姊妹仨像雞雛跟了老母雞,顛顛地跟在后面跑了去。這頓肉不能放開吃,父親看見哪個孩子還眼巴巴的,就又撕了肉往他嘴里塞去。
除了吃到肉,過年這兩天,孩子都可以不用干活。吃罷肉的下午,無限滿足地跑出去瘋玩了。母親和父親就一直在忙年。父親在天井里,把一年來攢下的木頭用洋鎬劈了,晚上熬五更,在屋里點起火盆取暖。燃燒完的木柴華麗轉身,變成紅紅的木炭,父親就把兩根長鐵筷子擔在火盆上,烤出酥脆焦黃的饅頭片,每個孩子都得吃,說是五更里吃了一年不生病。
我的父母,用他們的慈愛和溫暖遮蓋了貧窮,在我的年里留下濃濃的肉香,我的年里跳動著紅彤彤的木炭火,溫暖我一生。
有了女兒,漸漸習慣在婆家過年。在婆家過的年,更是熱鬧,盛騰。
年三十這天, 兄弟三個帶了妻兒從城里的小家趕往山村的老家。婆婆特意用大鍋燒柴火煮腿骨。這種伴著煙熏火燎之氣煮的腿骨格外香。婆婆帶著滿身的柴草屑剛走出低矮的灶間,二哥就帶了家什進去,一會兒,被熱騰騰的肉香包繞著端了一大盆肉骨頭出來。天井里早放好了桌子,二哥剛放下盆,好幾只手已經伸了過去。站著的,蹲著的,嘴里咝咝哈著氣,互相看看彼此不雅的吃相,笑聲溢出天井。
只要不是冷得厲害,吃罷午飯,我們就在天井里擺開陣勢。大哥帶了孩子們打掃衛生,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孩子們干著干著就圍著電視機邊看邊鬧。二哥是主廚,邊算計晚上的菜品,邊做準備。三哥,我的愛人,自相識以來,我總是稱呼他為“三哥”,這么多年一直都沒有改變。三哥在家是老小,不論爹娘還是哥嫂眼里,他都是比孩子們大一點的孩子,他沒有自己專職干的活。誰喊他他也應聲,他就像個陀螺似的店小二,哪里需要就轉到哪里。我們妯娌仨洗刷十一口人同時用的鍋碗瓢盆,剁肉餡剁素餡,炸春芽炸帶魚,各有其職,忙而不亂。公公婆婆坐一會兒,站一會兒,看看這個笑笑,看看那個笑笑。
晚上吃年夜飯,觥籌交錯猜拳行令,春晚往往成了下酒菜肴。
吃完團圓飯,我們六個齊下手,包完新年早晨的第一頓素餡餃子,點響炮仗,“爆竹聲中一歲除”,仿佛生活的不如意真的連同舊歲一塊去了。人們用這種形式表達著生命中一個個美好的愿望。
在婆家過年,祖孫三代,十一口子人,從年三十直鬧騰到大年初二,每人都像卸完了車又加滿了油,帶著這股熱鬧勁兒各自回小家,奔向又一年的新生活。
可騰騰熱火,說滅就滅了。公婆再也不長年輪,沒有了爹娘的家,只是一所宅院,在空蕩蕩的年里破敗下來。我曾渴望在一場盛大的煙花中過年,也曾向往在年里走向千里江山。那是我想要的不同凡響的年。年過半百,咀嚼起爹娘健在時家里那些令我厭煩的不變年事,卻像父親點在五更里的火盆。或許,正是這些看似一成不變的規矩里,延續著生命的律動。
老人變成了桌子上的牌位,讓我看到自己的去處,也讓我看到自己的來處。在鄉村,因農事,據農時,創年立節,蘊蓄希望和祝福。也許我們的祖先明白,日子不是無限延長的,它隨時隨地會斷掉。凡生命皆如此。三哥就突然和我毀約,把我的年變成了年關。
今晚又是年。
我在城里沿襲了鄉村的年俗,我的家堂桌上擺了三哥的牌位。他剛過半百,我不能讓他和公婆平坐在一起。我說服了所有的親人,讓我改一改規矩,我請三哥一個人回家過年。
我把三哥的遺像拿出來,立在桌上。我揣著三哥的照片去趕年集,看見往年我們在年集里拉著小車子擠來擠去,邊說邊笑。現在年集還是紅火熱鬧。火紅的熱鬧中,我感受著自己一點點被凍成一坨冰,寒冷向四周輻射開來,我咬緊牙,堅定地走向熱鬧的深處。
年三十中午,我也煮骨頭。不忘給三哥放一小碟蒜泥。我想也許他能聞到我終于又把我們的家炸出了濃濃的年味。
我一點點擦拭他的遺像,像過年給他穿起我精心做的新衣。我對著三哥舉杯,和三哥過他走后的第二個年。
吃罷年夜飯,我不看春晚,把琴對著三哥放下,低眉信手輕輕彈奏,我想讓三哥從我的琴聲里,看見我活著的樣子。
我熬五更。我攬三哥照片在懷,坐在母親給我縫制的蒲墩上,靠在暖氣片上,細細碎碎地和他訴說我這一年瑣瑣屑屑的日子。
這是我和三哥的年。俗套的年事里,我要讓三哥看著我一點點站起來。
我和三哥的年,已無關迎新除舊,已無關日月流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