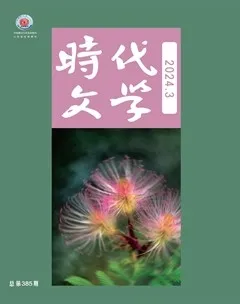新生
待產病房里,陪護家屬們你一言我一語,低聲閑聊著,一位眉眼俊秀的小護士急匆匆推開門說:“14床,去檢查;16床,準備一下。”16床正是我。
我確實需要準備一下,因為這時的我像一只大熊貓,需要愛人扶起來才能下床,自己連只鞋子都穿不上。又一次慢慢挪進產檢室,吃力地爬上冰冷的產床,醫生檢查的結果是:沒開骨縫。這是我第三次上產床,第三次原樣下來。見我又回來了,婆婆嘆了口氣,又用哄孩子似的口吻說:“快再吃點東西吧,生的時候有力氣啊!”我接過姐姐買來的油餅,吃了兩口,全部吐了出來。我大哭起來,不想生了,要回家。愛人不敢吱聲,婆婆悄悄嘀咕著:“女人都要過這一關,哪有不生的道理!”眼看著病房里越來越暗,太陽照進病房的影子扁成了一條線,一天又要過去了。我的主治醫生一陣風般地來到病房,嗓門提高了八度:“這么說吧,門小人大,能出去嗎?”這是位身材高大的女醫生,走路虎虎生風,說話的聲音能瞬時填滿整個病房。她快速走近我,從鏡片后瞥了一眼我的肚子,做了一個往外擠的動作,說:“考慮考慮剖腹產吧!”說完,打開門,又一陣風般去別的病房了。
我妥協了,決定做剖宮手術。
天哪,在醫生的“威逼”下,我脫下病號服,突然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原來是位男麻醉醫生正端坐在手術床前,我腦子里轟的一聲,慌慌張張抓衣服遮身體,但所有衣服已遞到室外。我一絲不掛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周遭白晃晃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撕咬我的身子,皮肉像被刀片旋一樣疼,我感到了巨大的羞辱,我痛徹地體會到人的弱小和無助。那一刻我好像暈過去了,等我稍稍清醒一點,本能地去捂自己赤裸的身體,唉,有用嗎?掩耳盜鈴。闖過了這次鬼門關,后來談論起產房里有男醫生這事時,朋友們的說法是,正常得很。醫生眼里不分男病號女病號,他們只關心打針、動刀的具體部位。
無影燈的銀粉紛紛飄落,無聲無息,我安靜下來,平躺到手術臺上。“這位準媽媽,剛才還號啕大哭呢。”小護士悄悄地說,然后是偷笑聲。幾位年輕的醫生指著我的肚子,問東問西,比比畫畫,主刀的正是剛才那位走路如風的王醫生,在跟他們講解著什么,都是我聽不太懂的專業術語。我閉上眼,任滿腦子白光流曳。
上半身和下半身被白圍簾隔開,麻藥注入了腰椎,很快,下半身似乎不存在了。我的神經一直緊繃著,一會兒,聽見主刀醫生跟旁邊的實習醫生說:“你看她這個肚子特別大,肚皮也有些厚,切開的時候……”她一邊解釋著,一邊動了手術刀,肚皮割開了,我沒有感覺出一絲疼痛;緊接著是“嘩啦嘩啦”的水聲,不知道是羊水還是血水。一陣“叮叮當當”手術刀、手術剪碰撞的聲音過后,一名小護士喊:“出來了,出來了,怎么長這樣啊!”我一聽,心涼了半截,孩子什么樣?不一會兒,只聽“哇”一聲,響亮的啼哭聲傳進了耳朵,那位麻醉醫生笑道:“聽這聲,這孩子勁兒不小!”
醫生一邊給我縫合傷口,一邊還給實習醫生講解著如何下針。孩子呱呱落地,可我的心還懸著。
我動也動不了,被裹起來抬上擔架車。終于回到病房,大家又一陣手忙腳亂,把我安置到病床上。愛人安頓好我,兩只大手摸向襁褓:“兒子,睜開眼,叫爸爸!”他笑得樂開了花,婆婆的目光也不離嬰兒左右,咯咯地笑個不住:“剛生下來咋會叫爸爸嘛!俺又添孫子嘍!”
我在醫院的兩天一夜中,母親沒吃一口飯,坐立不安。孩子生了,父母也坐車到了。母親心疼地念叨:“你說說,生個孩子差點要了閨女的命啊,好好的,挨了一刀!”父親心疼地到床邊給我掖被角,不小心碰著了輸液的管線,我“哎喲”一聲,母親嗔怪道:“你快離遠點兒,笨手笨腳的,別碰疼了閨女!”我的父母,他們只擔心我的身體。
麻藥的效力還在,我翻不了身,一直牽掛孩子是否健全,想看看孩子什么樣。婆婆連忙抱過孩子,說:“好著呢,好著呢!剛才睜開眼了,看著隨你,就是個小小紅啊!”愛人幫我戴上眼鏡,我吃力地側頭瞅了瞅,襁褓中是小小的他:腦袋身子很協調,肉嘟嘟的小臉,小嘴巴咕嘟著,小拳頭攥得緊緊的,投降似的靠緊耳邊,似乎睡著了。“怪不得小護士笑,原來這么難看啊……”我還沒說完,母親搶過話兒:“你們年輕人啥也不懂啊!老話說,月窩里的孩子丑過驢。這小家伙可不丑,眉眼這么清秀,這就是好看的孩子了!”
我和愛人結婚后,受下海風潮影響,他一展翅膀,從山東飛去深圳打拼。半年后,我也辦好停薪留職手續,追趕他的腳步。本來我們打算在深圳闖一闖,創下一番事業,沒承想,久別重逢的甜蜜過后,我就懷了寶寶。到底是創業還是要孩子呢?這是個大問題。在此之前,我曾經懷過一次孕,那時新婚晏爾,不懂如何避孕,我卻不想那么早要小孩,沒經愛人和家人同意,自己去醫院把孩子拿掉了。過后婆婆埋怨,愛人不高興,母親怪我不懂事,我也懊悔不已,但為時已晚。這次我不敢再私自決定了,我們去問在深圳一家醫院當兒科醫生的舅媽,她說我這種情況必須得要孩子,否則容易滑胎。她舉出表嫂的例子,表嫂就是因為流產傷了身體,遲遲未能再懷孕。
帶著深深的遺憾,我由深圳飛回山東。腹中的寶寶,乖巧溫和,妊娠反應也不劇烈,我胃口大開,能吃能喝,孕肚日漸明顯。我孕前不足100斤,到孕后期猛增至140多斤,同事笑稱我光有橫,沒有豎,越來越像個圓球。原來的衣服壓進箱底,我穿上姐姐懷孕時穿的外套,要多夸張有多夸張,臉也越來越臃腫,真是丑極了。我不敢照鏡子,不敢看自己一塌糊涂的樣子。我曾是學校年輕女教師穿著的時尚標桿呀:春天粉色及腰夾克、藏青色闊腿裙褲,夏天一身紫色碎花連衣裙,秋天大八片收腰方格風衣,同事們都叫我時裝模特兒。學生、同事羨慕的目光時時令我驕傲。
丑就丑吧,平安就好,可妊娠期到五個多月時,一件突發的事又讓我處在了擔驚受怕中:當時我住在單位分的婚房里——一種筒子式的平房,電線線路很老了。一次,在用電熱器燒水時,不知哪里漏電,我的手猛地被電流震開,身子趔趄到一邊,差點摔倒,頭似乎要炸裂,回過神來,我想的是,壞了,會不會影響到胎兒?會不會生一個不健全的孩子?我從此有了心病,查閱了一些書籍資料,看到導致畸形的種種實例,雖沒有關于這事的任何資料,可仍默默憂心。我沒有跟父母及婆家人說這件事,怕他們大驚小怪,更怕他們也跟著擔憂。我時時關注自己的肚子,時時與胎兒對話:寶貝,要好好的,老天保佑你。第六個月,我去做了彩超,雖然醫生診斷胎兒發育正常,我心頭壓著的石頭卻還放不下,夜里常被噩夢嚇醒。懷孕第七個月時,我自己照顧不了自己了,愛人只好辭掉了深圳的工作,飛回我身邊。深圳到山東,幾千里的距離,阻斷了他創業的夢想。他是落寞的,因為外出的闖蕩失敗了。看到我逐漸笨重的身子,看到胎兒的胎動,他才逐漸快樂起來,常常趴在一邊與它對話,給它聽優美的胎教音樂。可我心底的秘密卻不敢告訴他,我如履薄冰,害怕胎兒會有一點點、一絲絲不好的癥狀。現在終于確定孩子是個健全健康的嬰兒,我一歪身子酣然睡去。
我醒來時已是下午。時值五月初,雨后的天空如一塊藍寶石,晶瑩璀璨,陽光溫柔地斜射進了病房,對面的院墻邊,挺拔的梧桐樹新綠盎然,薔薇枝葉扶疏,正在開啟一場盛大的花事。多么美的春光啊。我尋找著孩子的笑臉,忽然想到傅天琳的詩《我的孩子》中的詩句:我的盛開的花朵/我的蓓蕾/我的剛剛露臉的小葉子/你聽見媽媽的呼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