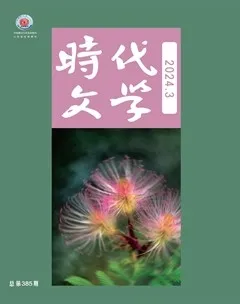詩心顯現(xiàn)與詩性寓言
海洋在古希臘神話中意為統(tǒng)治萬水之神,是萬水之源的擬人化,代表了世間日月星辰的起點和終點。作為地球科學的概念,“海洋”之稱則來自于千百年間人們關于其自然形成過程的逐步理解:邊緣為“海”,中心為“洋”,二者彼此交融互通,共同構(gòu)成一方統(tǒng)一的自然物象世界。
在中國古代漢語中,“海”與“洋”在水陸距離的遠近所指層面代表著不同的內(nèi)涵,因此被鮮明地區(qū)分開來而存在,并單獨使用。其中,前者靠近大陸,意為百川匯聚之處,如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將其解釋為:“天池也。以納川者。”中華書局出版的《漢魏古注十三經(jīng)》中的“四瀆者,發(fā)源注海者也”則強調(diào)了其河流匯聚的特征。后者最初僅指水名,后又具有了比海大的水域,即海洋中心部分的引申意義。可見,與背靠大陸的地理環(huán)境特征以及進而形成的農(nóng)業(yè)文明高度繁榮的客觀物質(zhì)條件緊密關聯(lián),地沃水足、氣候適宜穩(wěn)定,中國古代先民僅靠陸地農(nóng)耕就可豐衣足食,對海洋的認識便自然顯出基于“大陸視角”之上的單純和感性,中國古代僅將“海”視為盡頭或邊緣,這與西方,特別是地處半島的古希臘諸國由于陸地資源匱乏而產(chǎn)生的海洋觀念完全不同。
然而,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對海洋實用價值的忽視并不意味著古代中國人海洋經(jīng)驗的缺失,山頂洞人遺址中曾出土的貝殼、余姚河姆渡遺址中曾出土的木制船槳等,都充分證明先民們的海洋活動自新石器時期便已開始。進入文明時代,尤其是先秦兩漢以來,更為頻繁的海上實踐、更為豐富的海洋認識和想象不僅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海洋特質(zhì)愈發(fā)凸顯,還使中國古代海洋文學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因此,那些有關中國沒有海洋意識和海洋文化的觀點實屬片面。
但不可否認,古代中國人對海洋的態(tài)度確實不似西方人那般,在不斷探索與開拓的行為中,形成自由、冒險甚至帶有侵略性的海洋觀念。在中國人看來,位于大陸邊緣的海洋意味著陌生和危險,劉熙的《釋名》中甚至有以“晦”釋“海”的記載:“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以此來形容海洋的神秘和昏暗。
此種認知特點自然會鮮明地體現(xiàn)在中國傳統(tǒng)文藝作品的創(chuàng)作中,特別是海洋意象的構(gòu)建中。出于對海洋的天然恐懼,人們常常將之與困境、兇險、苦難聯(lián)系在一起。但與此同時,海洋又在一定程度上為人們留下了廣闊的想象空間,一方面,遙遠未知的海洋被人們寄予純凈、自由的向往;另一方面,深海的變幻莫測所激起的敬畏和崇拜心理又迫切呼喚著精神的寄托,《山海經(jīng)》中的“海上仙山”,《莊子》中的山中神人,“不餐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于四海之外。”作為圖騰意象,充滿安撫人心的力量,也使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海洋書寫飽含奇異玄幻的色彩。
兒童文學作家劉耀輝的小說《野云船》以詩意生動的語言展示了海島少年的生活,其中對海洋的書寫便體現(xiàn)出了上述美學觀念,不僅僅單純將其作為故事發(fā)生的地點,而是以多樣化的敘事策略賦予其更為豐厚且深刻的內(nèi)涵,從而鮮明地呈現(xiàn)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古典文學的特點。
溫柔之鄉(xiāng):
詩意生長與情懷共筑之場
與傳統(tǒng)文學中對“海洋”意象的詩意化建構(gòu)傳統(tǒng)相適應,《野云船》中的海洋及其環(huán)繞的黑瀾島首先被作者賦予了明顯的如世外桃源一般的詩意色彩。這是一片極具海島風情和鄉(xiāng)土情調(diào)的原生態(tài)場域,居民不多,生活簡單,大多靠打魚為生,物質(zhì)條件不佳,但他們樂觀知足,且彼此之間融洽相處。可以說,這片海承載了海島居民最真摯的情懷,也成就了自古以來人們最向往的生存狀態(tài)。
不同于遠古西方人四海為家的生活方式由農(nóng)耕文明主導的古代中國人向來崇尚平穩(wěn)與安定,骨子里刻入了濃厚的故鄉(xiāng)情結(jié)。“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世世代代生長于此、受其哺育的黑瀾島人自然在心底對眼前的海洋和身處的小島懷有一種獨特的感情,正如楚天舒曾對天闊所說:“等你們長大了,草原、雪山都看過了,就會發(fā)現(xiàn)還是家鄉(xiāng)好。無論你走到哪里,這大海、這小島都會永遠占據(jù)你心里最溫柔的地方,因為你就是在這里生、在這里長的。”這是海洋之于黑瀾島人最表層的意義,也是楚天舒在畢業(yè)前夕回鄉(xiāng)助教時最根本的心理動機。
作者筆下的海洋為漁家少年們的精神撫慰和心靈成長提供了自然開闊的土壤。與陸隔斷、如孤島懸空一般,海洋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黑瀾島的經(jīng)濟發(fā)展,但也由此保護了小島不受外界的侵擾,民風淳樸、風景秀麗,島民與萬物保留有超越世俗功利的最原始、最純凈的關系。
農(nóng)歷三月二十三的盛大祭祀典禮是黑瀾島人海洋情感的首次集中展現(xiàn),“這一天是天后媽祖的誕辰,黑瀾島上的全體島民要聚到一起賽會,為媽祖慶壽”,“在這黑瀾島上,媽祖誕辰是一年里僅次于春節(jié)過大年的隆重節(jié)日……”作者大量著墨于此,將“媽祖”這個已匯入百姓集體記憶的信仰符號作為黑瀾島人世代依賴海洋又敬畏海洋的復雜心態(tài)的承載,在對祭祀禮儀的平鋪直敘間,將這種心態(tài)表露得完整又直白。
除了最直接的海洋情懷,黑瀾島人還對島中的百種生靈保持著最純粹的熱愛。從黃眉姬到招潮蟹,從老黑彈樹到耐冬花,他們積極且珍惜與自然的每一次互動,而被迫承受死亡的傷痛又使他們格外敬畏并珍視生命,于是,他們在試金灣的金色海灘上小心翼翼地注視山瓜蔞,又在去往雪浪嶼的小船上嚴肅莊重地仰望信天翁。在孩子們眼中,它們不僅僅是鄉(xiāng)土情感、往昔記憶的載體,它們本身也是朋友,是伙伴。也正因為此,答應張琴子為其尋找山瓜蔞的楚天闊,最后終于在崖下大荒嶂的半腰處找到一棵時,卻也僅僅摘下了六個果兒,給大自然留下了三個。
至此,海洋與黑瀾島終于超越了物質(zhì)故鄉(xiāng)的意義范疇,而具備了精神家園的特質(zhì)。靈魂與萬象互通、自我與外在交融,從而成就了一方“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靈境。這是人與自然最和諧的存在方式,也是古往今來人們最向往的生存狀態(tài)。而在此意義上,這一孩子們的精神故鄉(xiāng)、靈魂可以自由棲居的地方,便可在天舒的返鄉(xiāng)行為及最終的死亡結(jié)局中解讀出另一種意義指涉,即在對于回歸心靈居所的向往中,實現(xiàn)了靈魂的永久安寧。
“斜陽入海,一線青山遠;月上云舟,千里向黑瀾。”“海天之間,春水初生,春云初展;黑瀾島上,春林初盛,春山初醒。”作者以充滿詩意的語言滿懷熱忱地悉心書寫海島少年們每一次奇妙的生命體驗,又以極富創(chuàng)造性的意象構(gòu)建將這種詩意盎然推向頂點。靈動輕盈的飛來鶴、威武壯觀的龍兵過、火紅燦爛的野云船……在詩心構(gòu)造的詩性空間里,自然造化之景似是裹上了一層朦朧柔和的光暈,而這片既象征靈魂居所,又代表精神寄托的“溫柔之鄉(xiāng)”,也似是由此透出了一種空靈脫塵的韻味。
苦難之所:
人世無常與悲憫復現(xiàn)之地
中華民族是典型的農(nóng)耕民族,因而,在圍繞陸地農(nóng)耕文化構(gòu)建起來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對待海洋的態(tài)度和觀念便不像西方那樣開放和自然。
由海洋民族或游牧民族的祖先實踐經(jīng)驗所決定,在西方人的潛意識里,廣闊無垠、渺渺無限的海洋就是自由和開拓的代名詞,時時呼喚著人類的冒險和進取,由此形成的以自我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激進特征甚至攻擊色彩的海洋觀念,于文藝作品中的突出表現(xiàn),便往往是以航海為敘事背景,以尋寶、探索、冒險為敘事主線,講述追求自由、征服困難、克服艱險的故事,突出個人存在及對命運的控制,從而表達實現(xiàn)個人夢想、證明個人價值的主題內(nèi)涵。
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中關于海洋的書寫以及海洋意象的構(gòu)建,則常常基于其神秘莫測、陰晴不定的特點,講述它帶給人們的困苦和災難。隨著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特別是在近代外族跨海入侵、民族屈辱護國的時代大背景下,古往今來秉承大國統(tǒng)一觀念的中國人,又在創(chuàng)作中將海洋作為敘事空間展開故事,從而使文學作品中的海洋書寫超越了原先的單一所指,表現(xiàn)已根植于人們集體記憶之中的災難情節(jié)。
《野云船》的故事圍繞海洋、孤島及島上的漁家少年展開,傳統(tǒng)文化觀念的深刻影響以及海島生活面臨的真實狀況,都使作者的復雜情感及其所要表達的主題內(nèi)涵不僅滲透在對于精神故鄉(xiāng)的詩意想象中,還蘊藏在對于海洋苦難的書寫中。
與廣闊、純凈、詩意并存的,是因海而生的惡劣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一方面,特殊的地理位置讓島上的冬天漫長而寒冷,“剛剛拐過五戟崖,海風就直直地迎面撲了過來,硬得像宰魚的刀子一樣”,“海島上的天氣就像娃娃的臉,說變就變。剛才還是一片響晴,轉(zhuǎn)眼就變成了寒風呼嘯,陰云密布”,“孤懸于大海中的黑瀾島,氣溫比內(nèi)陸低得多,還停留在初春時節(jié)”……凜冽的寒風、刺骨的寒氣使冬天的黑瀾島猶如一個大冰箱,叫人避無可避。另一方面,因海隔斷,與城市遙遙相望的小島像是一個被遺棄的孩子,孤立無援,更難言進步和發(fā)展,“整個黑瀾島上大多數(shù)人家的生活條件都很不好……買得起削筆刀的也不過梁雁飛、吳連魯、張琴子、楚夢瀾等三五個同學而已”,“所謂的午飯,不過是清一色的咸魚餅子,卜老師也不例外。雁飛多帶了個煮雞蛋,就引來了一片暗暗的艷羨”,“黑瀾所小學師資奇缺,平均每個班只能分到一位老師。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是這一位老師教全科”……風里來浪里去的討海人家,生活貧苦、資源貧乏已是常態(tài),但心靈自由、精神富足的他們似已不將物質(zhì)條件的束縛視為悲哀。
真正讓他們苦不堪言的,是海難時有發(fā)生。憑一葉扁舟“出沒風波里”,世代靠海吃海的黑瀾島人,既要面對在海上討生活的艱難,又要面臨同風浪搏斗的風險。董船波的爺爺、楚天闊和張琴子的爸爸的遭遇,給初經(jīng)世事的海島少年留下了關于死亡的記憶和經(jīng)驗。
受觀念差異影響,中西方多數(shù)文藝作品在海難情節(jié)的書寫中呈現(xiàn)出了明顯的不同。西方的海難故事往往伴隨有“荒島生存”的敘事模式,如《魯濱孫漂流記》《孤島歷險記》等,主人公遭遇海難后被丟至一處無人荒島,被迫展開自給自足的荒野求生挑戰(zhàn),與孤獨為伍,與自然相伴,與野性共存,并總會以主人公的求生成功而告終,以此凸顯人類強大的主觀能動性,更在此基礎上重申個人存在的無窮力量和巨大價值。
對比而言,中國式的海難書寫則更多的是在對媽祖信仰的基礎上,著重刻畫渲染人類于無情災難面前的渺小和不幸,從而在對世事無常的書寫中抒發(fā)悲憫情懷。
《野云船》中對于天舒意外死亡的情節(jié)安排便明顯體現(xiàn)了這一點。以天舒學習哲學專業(yè)及顧曉航對哲學產(chǎn)生了興趣為引,在去往雪浪嶼的小船上,借孩子之口詢問的那個關于生死的哲學問題,看似突兀,實則為后續(xù)情節(jié)埋下了伏筆。“埃斯庫羅斯本來是在悠閑散步,根本不會想到死,卻突然就這么死了;小烏龜被老鷹叼到了天上,肯定會以為自己必死無疑了,誰知道卻奇跡般地活了下來。”這宿命般地影射了天舒的結(jié)局:幸運地從風暴正中的巨浪狂風中逃脫,卻不幸喪命在過路風引起的意外插曲中。令人難以置信的滑稽劇在現(xiàn)實中復現(xiàn),以情理之中與意料之外的強烈對比,凸顯出生命于命運面前的脆弱無力,而這無疑亦加深了所謂“生死無常”的諷刺性,更從現(xiàn)實層面印證并闡明了天舒感嘆的那句“且行且珍惜”的全部意義。
小說對天舒祭日的描寫也可謂凄美而富有詩意,龍兵過和野云船同時出現(xiàn),共同組成“世代生活在海島上的漁人們見過的最神秘也最壯美的景兒”,來護送天舒的靈魂升天。在這里,作者向被苦難席卷的一家人傾注的厚重悲憫情感,借助頗具奇觀化的意象想象方式得表現(xiàn)出來。
詩和遠方:
基于海洋意象的情感想象
詩意與感傷交織,美好與苦難共存,由此可見,在《野云船》的故事里,“海洋”已不僅作為環(huán)境背景存在,而是超越了物理空間與敘事原點這一單純意義,成為具有“意象”性質(zhì)的載體。
作為抽象的主題思想與個人情感的具象表達媒介,“海洋”及其環(huán)繞的島嶼首先被塑造成一個潔凈無瑕、充滿詩意的場地。它是黑瀾島上漁家少年們的溫柔故鄉(xiāng),孩子們得其哺育、受其滋養(yǎng),隔絕于塵世喧囂之外,品性純良,雖然物質(zhì)生活匱乏貧苦,但是精神生活充裕富足。作者以滿含贊許的目光溫柔凝望著孩子們與這片土地和諧共存的生活狀態(tài),以極其生動的語言悉心描繪著他們的每一次游戲、每一場遠航。事實上,這正是作者內(nèi)心最真實的渴望鏡像,他將這份渴望寄托于這片海洋與這座海島上,字里行間無不盡顯最深切的期盼和最真摯的向往。
黑瀾島的形象基礎原是作者的家鄉(xiāng)青島,他依照自己熟悉的海濱環(huán)境,又著意褪去其現(xiàn)代性,保留獨屬于海島的淳樸風情,竭力將之構(gòu)筑成為一個洗滌心靈的詩意天堂,并在此基礎上,以一系列極富浪漫色彩的想象來深化這種詩意。飛來鶴、龍兵過、野云船……既與作者意圖表達的少年“詩意遠航與心靈成長”的主題思想暗暗契合,又抒發(fā)著他對于這片詩意之地的深厚情感。
文中亦存在對于遠離海洋的外部世界的描述,北京大學和天安門作為現(xiàn)代化的進步發(fā)達的物質(zhì)世界的縮影,滿載著全島孩子們的希望與憧憬,卻僅在作者筆下,借天舒來信中的寥寥數(shù)語一筆帶過,“夕陽映照下的這個園子名叫燕園,有一個大大的未名湖”,“湖畔矗立著一座靈動的博雅塔”,“校園也實在太大了,比我以前上過的所有學校加起來還要大許多。當然,沒有咱家的黑瀾島大,可是要比黑瀾島酷多了”,“當我真的站在天安門前的廣場上時,那種感覺、那種震撼是完全不一樣的!”這些描寫插入在孩子們因目睹野云船而興奮異常的情節(jié)中,頗具對照意味,隱晦地展現(xiàn)了二者及其背后的空間指涉之于作者內(nèi)心的不同意義。
故事以天舒留在筆記本上的寥寥數(shù)語作結(jié),是他正要創(chuàng)作的小說開頭,關于那片海,關于海島上的少年,也關于那艘人人向往的野云船。語句唯美如詩,放置于此卻似別有深意。從此以后,孩子們將展開新的生活,滿懷憧憬與希望。而處于文字之外的作者,也將在痛定思痛后,直面自己、直面人生。
朱光潛在《談美》說:“藝術家在寫切身的情感時,都不能同時在這種情感中過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觀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嘗受者退為站在客位的觀賞者。”誠然,當作者撿起那塊象征心結(jié)鑰匙的小石碑時,就說明他已做出了決定。當一切塵埃落定,回頭再看《野云船》的故事,便能從中品讀出幾分告別意味來,特別是七月十五那晚,孩子們?yōu)樘焓娣抛叩暮舸芍^最后的正式告別。當那艘最大的海燈船燃著明亮的嘎斯離岸,并隨潮水越漂越遠,帶走了孩子們的祝福和遺憾,也帶走了縈繞作者心間多年不曾散去的執(zhí)念。
歷盡千帆后,他終于在此時打開了心里的那個結(jié),選擇與自己和解。往后余生,他終于能直面過往,笑看未來……
用小說結(jié)尾處卓瑪看完天舒留下的文字后所說的那句“我覺得不像是小說,倒像是一首詩”來形容《野云船》本身似是最合適不過。作者劉耀輝深受中國傳統(tǒng)美學影響,因而總賦予作品以濃郁深厚的詩意,顯示著其純凈質(zhì)樸的詩心。縱覽全書,從空間建構(gòu)到故事情節(jié),從整體結(jié)構(gòu)布局到敘述語言,無不散發(fā)著一種動人心弦的詩性之美。意象構(gòu)建是使作品具有詩意的重要原因,也是作者表情達意的重要途徑,其中關于“海洋”的書寫便極具代表性。作者以個人親身經(jīng)歷為藍本,又將最真實的心境和最深沉的感情編織其中,使“海洋”這一意象顯示出了浪漫與現(xiàn)實并存的雙面特性,在詩意中抵達了真實,更直擊人心靈。可以說,“海洋”是作者復雜情懷抒發(fā)的關鍵媒介,因此,將之作為立足點,深刻解讀、剖析其背后深層的寓意所指,對正確理解作品主旨、把握作者心路歷程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