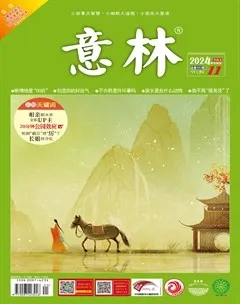我的背包

施瓦辛格經(jīng)常在網(wǎng)上和人互動(dòng),有一回他在勸那些沒(méi)精力健身的網(wǎng)友時(shí)說(shuō),“人生有時(shí)就是一場(chǎng)運(yùn)動(dòng)”。最近風(fēng)靡的運(yùn)動(dòng)方式“負(fù)重健走”應(yīng)該就是融運(yùn)動(dòng)于日常的典范,它讓我意識(shí)到,我不是每天運(yùn)動(dòng)量不足,反而可稱作“運(yùn)動(dòng)狂魔”。我那個(gè)擠地鐵時(shí)給身后乘客帶來(lái)壓迫感的巨量背包,過(guò)安檢一卸一提略顯費(fèi)事的背包,奔跑時(shí)所有物品都在攪動(dòng)雀躍的背包,居然是增強(qiáng)心血管和肌肉力量的利器。
若感覺(jué)負(fù)重不夠,專家的小貼士是可以在背包里裝磚頭或啞鈴,而我的建議是既然有力氣沒(méi)處使,能否開(kāi)發(fā)一個(gè)“順風(fēng)負(fù)重健走”的App,分擔(dān)一下同伴的負(fù)重,或者到中小學(xué)門口當(dāng)背書包的志愿者。不過(guò),有了“負(fù)重健走”這道心理暗示,通勤和出差的路上便沒(méi)有“馱著重重的殼,一步一步向上爬”的苦楚,反而有一種徒步鄉(xiāng)野、騎行山間的強(qiáng)身健體感。
背包這么沉重,全因它裝載了身家性命。我也想為背包減負(fù),無(wú)奈各種應(yīng)用場(chǎng)景疊加了需求,使用習(xí)慣的固化又讓背包更像無(wú)所不能的瑞士軍刀。戶外攝影背的包分艙如迷宮,裝了器材,舍棄干糧,行之不遠(yuǎn);特能裝的徒步包,連袋鼠倉(cāng)也能塞下一個(gè)籃球,掛板還能吊一堆物件,背負(fù)系統(tǒng)又極其舒適,但找個(gè)小零碎實(shí)在費(fèi)勁;造型好看的通勤包,拉鏈和暗層間建起了一座分類宮殿,鎖扣能讓我在咖啡館放心地短暫離開(kāi),但反手從彈力袋拿水喝的習(xí)慣不能被滿足。沒(méi)有一個(gè)背包是完美的,所以我需要好幾個(gè)。
有時(shí)忍不住想換背包,肆意犯一個(gè)裝備黨的矯情,我就會(huì)想想玄奘和《倩女幽魂》里的寧采臣,一副經(jīng)篋或行笈走天下,包羅萬(wàn)象;或是母親小時(shí)候背我的背簍,晃悠悠,自重大,不存在背負(fù)系統(tǒng),照樣載著二三十斤的娃行走如飛。何況,如陳奕迅《你的背包》所唱,那個(gè)背包“載滿紀(jì)念品和患難……成為我身體另一半,千金不換,它已熟悉我的汗”。我不得不換掉上一個(gè)通勤包,是因?yàn)榘l(fā)現(xiàn)夏天它不僅在T恤衫上會(huì)留下背包形的汗?jié)n,而且會(huì)染藍(lán)我的白衣。經(jīng)年風(fēng)吹日曬,它涂抹油彩的臉也化掉了。
有了背包,就有了說(shuō)走就走的底氣,有了把家背身上往外掏寶貝的硬氣,被解放的雙手也能攬山河入懷。有一種頂級(jí)背包客的“流放生活方式”就令人神往,“極簡(jiǎn)主義者”的全部家當(dāng)可以只有七十二件東西,全部收進(jìn)一只雙肩包里,周游世界時(shí)將負(fù)擔(dān)拋在腦后。日本作家松浦彌太郎也提倡過(guò)一種放下包袱的“輕生活”,“把所有必需品都塞進(jìn)背包,就會(huì)在不知不覺(jué)中,同時(shí)裝進(jìn)很多垃圾”。
關(guān)于如何整理和利用背包,角色扮演類(RPG)電子游戲也給了我不少啟示。游戲不會(huì)給你一個(gè)無(wú)限背包,去犧牲難度和舒張感,玩家必須不斷分配背包里的資源,找補(bǔ)給,做物品交易或斷舍離,適時(shí)調(diào)整戰(zhàn)術(shù),戰(zhàn)勝?gòu)?qiáng)敵。現(xiàn)實(shí)生活如同打怪升級(jí),負(fù)重行軍能發(fā)達(dá)肌肉,背得越多,力量越大;輕裝前行卻能讓人更快,更靈活,也走得更遠(yuǎn)。定期更新背包,撿出過(guò)期的能量棒、不用的U形枕、發(fā)酸的汗衫,為水袋續(xù)上水,把充電寶充滿電,隨時(shí)為下一次出發(fā)做好準(zhǔn)備。